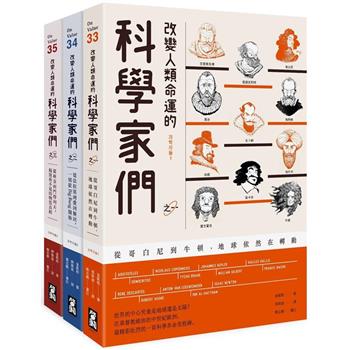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中國文學史.下的圖書 |
| |
中國文學史(下)-臺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紀念選輯 出版日期:2021-01-1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74 |
Literature & Fiction |
$ 474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474 |
小說/文學 |
$ 510 |
文學作品 |
$ 528 |
中文書 |
$ 528 |
中國古典文學 |
$ 528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文學史.下
文學史之作,不外乎以歷史為經,以作家作品為緯,
故文學史的方法應注意研究作家、分析作品。
至於如何研究與分析,則非單純方法能詳辨。
臺靜農先生撰寫《中國文學史》,不僅表達其個人性情學養所及,對歷代文學精神之深切體悟,與其間顯現之文化歷史流變,作真知灼見之詮釋,可謂:「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撰述期間幾近二十餘年,且不斷增補修訂,已完成先秦以至金元部分。其稿本與抄本長期在弟子間傳閱未得出版,一直至身後因遺稿由家屬捐贈臺大圖書館,臺大出版中心乃敦請中文系何寄澎教授主持整編加以出版,一代學人平生所蓄的心血結晶終能公諸於世。本書依時代分篇,上册包含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篇,下册包含唐代、宋代、金元篇,並附〈中國文學史方法論〉一文,乃先生以文學史家的眼光分析作文學史的方法,願有識者共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