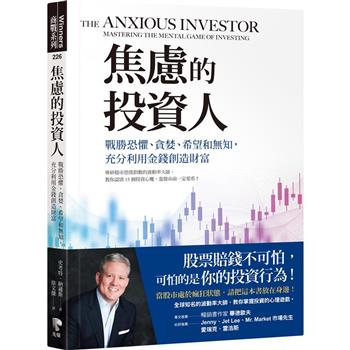明儒中的主動派與主靜派(摘錄)
一、前言
主張事功與實學的顏元(習齋,1635-1704)對宋明理學的批評最為嚴格,他認為從北宋以來的理學運動,其實是一種禪學運動,程朱表面上張揚儒學,而暗地裡卻是在毀滅儒學,孔孟程朱,他認為是對立的,所以他提出「必廢一分程朱,始復一分孔孟」的口號。在他看來宋明以來的儒學,基本上是無用的,而這個無用之學之所以接近禪學或者根本即是禪學的原因,在於宋明儒大多提倡靜坐,朱子即有「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主張,顏元則視作「無異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譏評極為急切。又曰: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平生,為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今玩鏡裡花水裡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
顏元反對靜坐,在於靜坐使人精神萎惰,筋骨疲軟,主靜空談之學久,勢必厭事廢事,以至誤己誤人甚至敗國敗天下。顏元對靜坐排擊之重,當然有其過當之處,然而他拈出靜坐這個論點來評論宋明儒,確實也掌握了相當的重點。宋明儒主張靜坐者極夥,而且其對動靜的觀念,也往往與其哲學觀念相互切合,譬如贊成靜坐的主靜派,往往重視主觀的冥想,重視抽象的知識推理,而反對靜坐的主動派,則比較重視即知即行,強調立身行事的具體成果。在道德上,主靜派多主張探索道德的形上理論,而主動派則強調道德在力行上的實際功能,主靜派重視天理人欲的差異,強調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不可相混,學者必須在「存天理、去人欲」的矩矱下修養磨鍊,而主動派往往將天理人欲視作一端,簡言之,主靜派多屬性二元論者,而主動派則多是性一元論者。
這個趨勢在明儒中看得更為清楚。本文主旨,即在由明儒的動靜觀來探索其哲學主張,從而辨析明代思想史上的諸問題。
在展開本文之前,須說明本文只針對明儒的「動靜觀」以作分析,所討論的是明儒贊成「主靜」或反對主靜的意見,反對主靜的,往往強調具體行動的重要,即視主靜者為枯寂,故又稱作「主動派」。由於主靜派多數主張靜坐,主動派則多數不主張靜坐或者反對靜坐,所以靜坐也是討論的主題。宋儒多有將「主敬」與主靜混說,有的甚至直接以主敬作主靜,這是分析不清所造成的,嚴格說來,主敬不同於主靜,主敬是指嚴肅面對及處理哲學與人生問題,這一點,即使是主動派也並不反對,所以本文並不處理主敬這一命題之下的問題。
二、陳獻章與湛若水
討論明代儒學,應該從陳獻章(白沙,1428-1500)開始談起,這幾乎已是公論,原因是明初諸儒,大多死守南宋朱學的矩矱,並沒有太多的創獲與突破,明學到陳獻章、王守仁(陽明,1472-1529)之後才算真正的展開。陳獻章是極為贊成靜坐的,他曾自述求學的經過云:
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與弼)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陳獻章自述求學的經歷,先是求師問道,後是遍覽群書,但終未有所得,後來乾脆「舍彼之繁,求吾之約」,一切放下之後,在靜坐中突然體悟出許多以前無法體會的道理來,原來在靜坐之中「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外在的知識和內在的心靈結合,而形成近乎朱子在〈格物補傳〉中所說的「豁然貫通」的現象。我們如拿來和陽明格竹子的故事相比較,也會發現其中有頗為相同的部分,陳獻章「舍彼之繁,求吾之約」,陽明「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其意義是有相通之處的。
陳獻章之學有強烈的「求之吾心」的傾向。他說:「夫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苟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道存焉,則求之書籍可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反而求之吾心而道存焉,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這一點與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1139-1193)的主張十分接近,與陽明也可說是同調。難怪《明儒學案》說白沙與陽明「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既主張求之吾心,因此他比較反對在書籍中找學問,他在〈道學傳序〉中說:
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
這個論調,幾乎與反對讀書的顏元完全相同,陳獻章曰:「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顏元則謂:「讀書著書,能損人神智氣力,不能益人才德。」又曰:「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然而顏元認為讀書無用,在鼓勵學者實事實行,而陳獻章之認為讀書為無用,在強調自我,因為外在或客觀的知識,對人的修養是全然無用的,兩人結論是完全不同的。他在〈道學傳序〉的結論部分寫著:
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書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陳獻章的理論是:一切真知應「求之於我」而非求之於書籍,要求真知於自我,則人須將自己置於「虛明靜一」的狀況之下,要將自我置於虛明靜一的狀況下,則捨靜坐,就沒有更為好的方法了,如此推論,自遠出顏元之意料,陳獻章說:
學勞擾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
又說:
為學須從靜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陳獻章是吳與弼(康齋,1391-1463)的弟子,吳氏門人如胡居仁(敬齋,1434-1484)、魏校(莊渠,1483-1543,胡居仁的弟子)都有主靜的主張,如胡居仁在他的〈居業錄〉中說:「靜中有物,只是常有個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又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黃宗羲論魏校之學曰:「其宗旨為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可見白沙之主靜,也受同門友朋影響。他如此的「主靜」,強調靜坐工夫,是不是會被視為「近禪」呢?這一點,陳獻章並非沒有自覺,他曾說:
老拙每日飽食後,輒瞑目坐竟日。
又說:
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
他在此處,似乎並不避諱自己的學問是「流於禪學者」,然而他在其他地方,也會設法來解說靜坐不見得是禪學,他似乎還是在乎別人批評他「近禪」的,他說: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援,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
足見他還是耽心他的主靜被視為近禪,因此偶爾不惜引「敬」入「靜」,做了點調和之說,但說的是朱子,不是自己。這一點,他的學生湛若水為之辨解,他說:
夫先生(指白沙)主靜,而此篇(指白沙〈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詩)言敬者,蓋先生之學,原於敬而得力於靜,隨動靜施功,此主靜之全功,無非心之敬處。此不察其源流,以禪相詆,且以朱陸異同聚訟,過矣。先生嘗曰: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按此,則靜與敬無二道,無二道,豈同寂滅哉!
湛若水認為陳獻章的靜,「原於敬而得力於靜,隨動靜施功,此主靜之全功,無非心之敬處」。是黃宗羲也在〈白沙學案(上).序〉中為之辨解說:
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為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
這兩段話十分有趣。湛若水為老師辨解,說白沙的主靜即是主敬,原本來自儒家正統,而黃宗羲則認為聖學有動靜二派,動者易於發現,靜者則否,因為不易被人發現,故靜者經常被視為鄰於外氏,言下陳獻章的主靜,並不等同於佛家。兩家的辨解言之成理,但都忽視了主體,白沙主靜如真的同於主敬,則為何不直接說主敬呢?白沙主靜不主動,也許不易被人發現而令人誤會其近禪,但問題不是別人發現或不發現的問題,而是白沙的主靜、靜坐是不是根本近禪呢?顏元對這個問題有過精到的分析,他說: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即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
如果以顏元判別的標準,陳獻章的主靜朝「靜坐收攝」這一方向發展是不能否認的,則他的主靜絕不可看成是儒門正統的主敬一派,敬,謹也,主敬是凡事謹慎,絕非講靜坐的守靜一派的主張。這一點,陳獻章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前引〈復趙提學僉憲〉文中說自己是「流於禪學者」,可見湛若水的說法不能成立,而黃宗羲的說法也大有問題。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極力推崇陳獻章,說他「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又說他「不假人力,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而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22黃宗羲對陳獻章的判斷是白沙之學雖由博而約,由粗而細,這「約」和「細」還是有的,並非虛無的,這一點和佛門的虛無、虛寂是純然不同的,這只說明陳獻章之學究竟與佛教有出入,並沒有說明陳獻章的靜坐到底有沒有禪門的成分。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因嘗評論陳獻章說:
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般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劉宗周這一點的意見明顯不同於黃宗羲,劉宗周對陳獻章的成就不是那麼推崇,他認為白沙之學「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至於陳獻章是否近禪,劉宗周認為無須辯論,原因是劉宗周根本否認靜坐的作用,他說:
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個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
靜坐在劉宗周而言是個含混的遁詞,他批評陳獻章「靜中養出個端倪」說:「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其實是個容易閃躲的藉口,又說「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可見劉宗周認為陳獻章的靜坐並不是從正統儒門中得來,是不是近禪,則因為靜坐無甚價值可言,所以也無須再辨明了。
湛若水(甘泉,1466-1560)受業於陳獻章,並對陳氏的靜坐提出其異於禪家的看法,表面上是維護他老師的主張,但他對陳獻章教人放下書本靜坐,卻表現了不同的意見。他曾說:
諸生讀書時,須調鍊此心,正其心,平其氣,如以鏡照物而鏡不動,常炯炯地,是謂以我觀書,方能心與書合一。孔子所謂「執事敬」,《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程子所謂「即此是學」,如此,方望有進。若以讀書主敬為兩事,彼此相妨,別求置書冊而靜坐以為學,便是支離,終難湊泊。
他這段話很有意思,表面上他不反對靜坐,他只不贊成「置書冊而靜坐」,他認為讀書與靜坐並不相妨,靜坐在求正其心,當心正之後讀書,就可以達到與書冊合一的境界。然而他卻十分嚴峻的提出了他不同於陳獻章的看法,他完全了解,陳獻章的靜坐之學是要放下書本的;其次,湛若水所提出的靜坐,總是將它與「主敬」這個觀念聯綴在一起,也就是他贊成主靜乃至靜坐是有條件的,主靜和靜坐不能脫離敬的意義範疇,這一點,他與他的老師根本不同。宋明儒在論及主敬與主靜的時候,有時候是意義含糊的,但陳獻章卻很少把這兩個詞用混,陳獻章的主靜就是主靜,並不是主敬,而湛若水的意思很明白,假如靜坐是指放下書本,靜只是追求自身的寧靜,而不與敬的意義有涉的話,他是反對主靜的,當然也是反對靜坐的,他說:
古人論學,未有以靜坐為言者,而程氏言之,非其定論,乃欲補小學之缺,急時弊也。後之儒者,遂以靜坐求之,過矣。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為言者,以靜為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時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即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而不可入堯舜之道矣。
在這段話中,湛若水提出兩個十分清楚的看法:一、古之論學,未有以靜言者,以靜言者皆禪也;二、正統的儒家應在事上求仁,在動時著力。這兩個意見說得十分明白,一點都不閃躲,可見其堅決。
湛若水對陳獻章「此為以自然為宗」的本旨是贊成的,《學案》稱湛若水之學是「隨處體認天理。」這個「隨處體認天理」的主張,有相當自由的成分,基本上是合乎陳氏主自然的宗旨。然而在動靜觀止,他的主張卻與陳氏相距頗遠,甚至唱起反調來了,譬如他批評「靜以養動」論者說:「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強制之病。故古來聖聖相授,無此法門。」這明顯是批評陳獻章的理論的。他極力的提倡「動」的觀念,認為學者應該由「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隨體認天理。」與陳獻章主張放下書本,一意靜坐當然不同,反而十分接近顏元的力行觀了。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的圖書 |
 |
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 作者:周志文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1-12-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0 |
二手中文書 |
$ 284 |
Books |
$ 284 |
Books |
$ 317 |
中文書 |
$ 317 |
中國哲學 |
$ 324 |
社會人文 |
$ 324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360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
黃宗羲曾說晩明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思想領域繽紛離奇,變化極大。王陽明良知學對晩明思想家影響甚廣,不僅思想界,對文學與藝術創造也有作用,而且爭議不斷,其中包括良知的性質,致良知的方法,以及判斷是非,應以歷史的格套或個人自覺為基準等,晩明學術,於此討論甚多。
本書收錄相關論文十一篇,著眼於晩明學術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以及思想的傳承演化上,除王學影響之外,也涉及其他學術議題,內容廣泛,議論精闢。
作者簡介:
周志文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學術史、明清文學、現代文學。曾至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講學,荷蘭萊頓大學訪問。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專著有《汲泉室論學稿》、《論語講析》、《孟子講析》、《陽明學十講》等。
章節試閱
明儒中的主動派與主靜派(摘錄)
一、前言
主張事功與實學的顏元(習齋,1635-1704)對宋明理學的批評最為嚴格,他認為從北宋以來的理學運動,其實是一種禪學運動,程朱表面上張揚儒學,而暗地裡卻是在毀滅儒學,孔孟程朱,他認為是對立的,所以他提出「必廢一分程朱,始復一分孔孟」的口號。在他看來宋明以來的儒學,基本上是無用的,而這個無用之學之所以接近禪學或者根本即是禪學的原因,在於宋明儒大多提倡靜坐,朱子即有「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主張,顏元則視作「無異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譏評極為急切。又曰:
洞照...
一、前言
主張事功與實學的顏元(習齋,1635-1704)對宋明理學的批評最為嚴格,他認為從北宋以來的理學運動,其實是一種禪學運動,程朱表面上張揚儒學,而暗地裡卻是在毀滅儒學,孔孟程朱,他認為是對立的,所以他提出「必廢一分程朱,始復一分孔孟」的口號。在他看來宋明以來的儒學,基本上是無用的,而這個無用之學之所以接近禪學或者根本即是禪學的原因,在於宋明儒大多提倡靜坐,朱子即有「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主張,顏元則視作「無異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譏評極為急切。又曰:
洞照...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2021年版序
臺大出版中心要再次出版《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這本書。新書做了些修正。
面對這本舊著,我的心情很複雜,其中包括有些羞愧。要說書中所談的問題,都不算沒價值,但我之前談時,沒把題目抓得太準,談得也不夠細,有些地方,總覺表面化了一點,宋明儒談這現象叫搬弄光景,光景就是光影,是事務的影子,與事務有關,卻不是事務的本身。
我在原序中,說這本小書所涉及的大多是「爭議」兩字,我想趁此機會稍微再談一下。
有心尋找的話,爭議是無所不在的,對晚明的知識分子更是。晚明知識分子煩憂的事很多,大的與...
臺大出版中心要再次出版《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這本書。新書做了些修正。
面對這本舊著,我的心情很複雜,其中包括有些羞愧。要說書中所談的問題,都不算沒價值,但我之前談時,沒把題目抓得太準,談得也不夠細,有些地方,總覺表面化了一點,宋明儒談這現象叫搬弄光景,光景就是光影,是事務的影子,與事務有關,卻不是事務的本身。
我在原序中,說這本小書所涉及的大多是「爭議」兩字,我想趁此機會稍微再談一下。
有心尋找的話,爭議是無所不在的,對晚明的知識分子更是。晚明知識分子煩憂的事很多,大的與...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學術研究叢刊」出版緣起
2021年版序
自序:迴音壁旁的爭議
明儒中的主動派與主靜派
仕進與講學:以王畿、錢德洪的選擇為例
羅汝芳論《大學》
論「道理不行,聞見不立」
何心隱與李贄的人倫觀
論黃宗羲的四篇「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論陳確的《葬書》
明末清初有關封建、郡縣的爭議:以黃、顧、王為例
明代笑話書中的士子
散文的解放與生活的解脫:論晚明小品的自由精神
張岱與《西湖夢尋》
2021年版序
自序:迴音壁旁的爭議
明儒中的主動派與主靜派
仕進與講學:以王畿、錢德洪的選擇為例
羅汝芳論《大學》
論「道理不行,聞見不立」
何心隱與李贄的人倫觀
論黃宗羲的四篇「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論陳確的《葬書》
明末清初有關封建、郡縣的爭議:以黃、顧、王為例
明代笑話書中的士子
散文的解放與生活的解脫:論晚明小品的自由精神
張岱與《西湖夢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