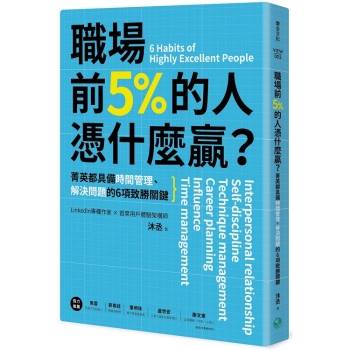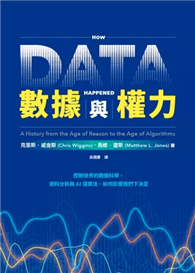導論(摘錄)
四、理論思考:文本行旅、異國形象與翻譯改寫
本書在翻譯理論的思考下,試圖將「非洲探勘/冒險記」,置入「跨文化行旅」的架構,觀察相關文本的接受與衍變。「行旅」並非指向普遍定義的休閒旅行,而是強調文本從此點到彼點的空間傳播。於此行旅路線,譯本從原著的既定認知框架,發展到另一有著不同價值認知的文化脈絡時,必然與他方文化語境碰撞、排斥、分歧與交流等,造成語言文字、概念表述與情節片段的變調。
(一)跨文化行旅與異國形象
湯普森(John Thompson,1951-)早已指出「全球化」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期,通訊網絡與訊息交流的規模開始越來越全球化。新式印刷技術確實促進彼時出版市場的發展與跨國交流。在工業技術的帶動下,各地出版品得以在全球化的國際市場中流通與傳播,出現各種跨國流動的路線。文本的傳播路線並非只是從西方到中國的一種模式,中間可能經歷其他地區,折射更複雜的「跨文化行旅」,如本書第四章討論法國凡爾納《氣球上的五星期》從法文原著發展到Chapman英譯本Five Weeks in a Balloon、井上勤日譯本《亞非利加內地三十五日間空中旅行》,再到中譯本〈空中旅行記〉(1903)與《飛行記》(1907)。從源語到目的語的過程中,相關著作經歷不同的文化脈絡,蘊藏各種饒具趣味的變調。文本的「跨文化/語際」路線,必然在不同的文化與語系脈絡下,展現新姿。若以劉禾提出「跨語際實踐」觀察,可見文本的移動與流變,經歷「詞語、意義、話語以及表述的模式」的轉變,以及文本在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接觸/衝突下,在主方語言中興起、流通並獲得合法性的過程。翻譯不只是與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衝突著的利益無關的中立的事件。實際上,它恰恰成為這種鬥爭的場所,在那裡,客方語言被迫遭遇主方語言,而且二者之間無法化約的差異將一決雌雄,權威被需求或是遭到挑戰,歧義得以解決或是被創造出來,直到新的詞語和意義在主方語言內部浮出地表。循此觀點,當文本輾轉傳播於不同的文化脈絡,與其他力量碰撞,開拓多重的向度。這些開拓,不僅僅表現於觀念與詞彙移植所產生的變調,更進一步延伸到文類形式、文學技法、觀念視野與價值內涵的轉變,開啟紛然雜陳的視野、價值與文化的對話。
在跨文化行旅中,譯本從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的脈絡時,尚內蘊著「自我」與「他者」的對應關係。德國學者狄澤林克(Hugo Dyserink,1927-2020)提及「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追求目標:「首要追求是,認識不同形象的各種表現形式以及它們的生成和影響。另外,它還要為揭示這些文學形象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觸時所起的作用做出貢獻。」從其視角,可見形象學的研究重點並不是探討「形象」的正確與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發展和影響;或者說,重點在於研究文學或者非文學層面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發展過程及其緣由。「比較文學形象學」主要研究文學作品、文學史及文學評論中有關民族亦即國家的「他形象」(heteroimage)和「自我形象」(autoimage)。形象學的出發點是每個「自我群體」(we-group)不僅知道自我認同的話語,亦了解認知「他者」(the other)的話語,並以自我區別於他者。他者與自我「群體標記」是一種兩極結構或曰正反結構,在形象的形成過程中,自我形象與他形象相互照應和相互作用。
「異國」形象成為對他者的描述(representation),牽涉到作者所處的社會整體對異國的「總體認識」,反射「自我」的文化需要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空間。在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視野下拓展的「異國形象學」,乃是以「跨」(學科、語言、文化)為特色,倡導者如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1939-)與馬克.莫哈(Jean Marc Moura,1956-)等法國學者提出建立起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與視野等。由巴柔所提出,對學界影響重大的〈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形象〉等文章,便指出「形象學」不只是對異國現實的單純複製式的描述:
形象是描述,是對一個作家、一個集體思想中的在場成分的描述。這些在場成分置換了一個缺席的原型(異國),替代了它,也置換了一種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對這種混合物,必須了解其在感情和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反映,了解其內在邏輯,也就是說想像所產生的偏離。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並非現實的複製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於形象。
巴柔指出面對「異國」形象時,得關注描繪者或是某一集體思想的「在場成分」,亦即這些描述者如何描述?描述者如何按照固有的文化模式、程序,導致重組與重寫?
形象研究無法脫離社會歷史時空而存在,馬克.莫哈在〈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及方法論〉一文中,關注「描述者」所勾勒的「形象」背後隱藏的「社會集體想像物」,強調形象模式有其意識形態的支撐,任何身分和形象都是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空間中逐漸形成與傳播。馬克.莫哈論及「形象」源自一個寬泛且複雜的總體:「社會整體想像物」(imaginaire social)是「全社會對一個集體、一個社會文化整體所做的闡釋,是雙極性(同一性/相異性)的闡釋」。從巴柔到莫哈的論述,皆將文本的異國形象置於更龐大的社會集體的網絡觀察,凸顯形象的生產與製作過程,反映從「個體—群體—整體」中的「自我」與「他者」形象的形塑。
(二)翻譯改寫
在文本跨文化行旅的過程裡,翻譯乃是形象呈現的途徑和媒介。在當代的文化研究論述中,翻譯學研究早已脫離語言層面上的指導原則,反而是在文化研究的脈絡下,關注出發語與目的語之間的轉換以及箇中所蘊藏的文化訊息,探討跨語際傳遞中既成的文學現象或文化現象。翻譯學如同形象學,關注目標語的社會民族文化自我身分和自我形象構建的功能。
翻譯有助於創造集體身分,構建民族文化,反映他者形象形塑,重塑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下的形象生產與傳播,如勒弗菲爾(Andren Lefevere,1945-1996)考察各時期的聖經譯本如何改變歐洲大陸的自我形象,如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德譯本,不僅對德國語言和文學產生影響,甚至改變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因此,翻譯研究有助於反映不同社會文化語境的譯者如何透過翻譯實踐的模式,塑造、改變、傳播和強化異域民族及其各種族群的文化形象與文化隱喻。對於「他者」與「自我」關係的探索,實也是探向譯者主體自身身分構建的另一視角。
若就翻譯理論而言,操縱派強調「翻譯」受到各因素的開拓/制約,是對原文的一種改寫(rewriting)」,如西奧.赫曼斯(Theo Hermans,1948-)指出為某種目的「對原文實施一定程度的操控(manipulate)」,譯者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語境,必然牽動譯本的面貌,形塑一更能適合該文化語境的主導意識形態和詩學。勒菲弗爾提及翻譯受到意識形態(ideology)、詩學形態(poetology)、贊助機構(patron)與論域(universe of discourse)等影響,對於原著進行調整,使其更符合改寫者所處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進而達到被接受的目的。相關論者提及翻譯學研究涉及意識形態、贊助機構、文化策略、國際環境、國家之間的關係等包含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因素。其中,尤為本書關注的是譯者詩學的注入,如何對於譯本產生變化?譯者如何在其所處的文化體系中使其譯文符合其所處時期的詩學形態,以達到原著被接受的目的?
譯者對原著的理解及其翻譯是一次「再創造」,而閱讀譯著的他國讀者的閱讀過程,同樣是一次「再創造」。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2000)將翻譯轉調視為「創造性的叛逆」(creative treason):「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可以說,全部古代及中世紀的文學在今天還有生命力,實際上都經過創造性的背叛。」從「翻譯操縱」、「翻譯創造」論等,都反映翻譯學的研究重點從「原文為中心」轉到以「譯本為中心」。
「譯介學」更進一步推進如此的研究模式,從跨文化、跨語言、跨民族的角度來考察、研究翻譯,關注跨文化交流的實踐。謝天振《譯介學》指出「譯介學」並非語言研究,而是文學研究或文化研究,「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出發 語與目的語之間如何轉換的問題,它關心的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伸等問題,它關心的是翻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從「譯本的作用」,側重文化層面對翻譯進行整體性的思考,擴大譯介學的理論視野和研究範圍。
上述各種關於形象與翻譯理論的思考,未必壁壘分明,卻相互呼應,投射殊途同歸的關懷視野,共同指出譯本在跨文化行旅中的翻譯創造/想像。在主、客方語言與內容的協商與調整過程中,譯本又如何受到意識形態、文化規範、民族心理與美學成規的形塑,使得來源語進入目的語的過程,為適應特定的文化語境而出現翻譯改寫的情形。
(三)晚清的翻譯實踐
本書固然以理論作為思考的起點,可是並非理論導向,更重視晚清譯者的文化脈絡、文獻材料與文本細讀,具體而微地觀察非洲文本翻譯傳播到晚清中國的途徑、接受方式以及譯本的轉向。
從十九世紀七、八○年代立溫斯敦與施登萊探勘非洲的人物傳記,發展至二十世紀初凡爾納與哈葛德的冒險小說譯本,有逐漸成熟化的趨勢。早期譯者較難同時掌控外語與中文文采,因而常出現口譯與筆述者合作的翻譯模式,擴大譯著與原著的差距,遂使得《黑蠻風土記》與《三洲遊記》都出現路線錯亂與迷失方向的問題,甚至改變原著的主旨。隨著翻譯風潮與翻譯理論的崛起,翻譯模式趨向嚴謹,二十世紀初的翻譯模式擺脫改頭換面的譯法,即或屢為人「詬病」的林紓譯著,已然大幅度躍進,趨向嚴謹。雖然,林紓仍然無法擺脫口譯者與筆述者的合作模式,可是其一系列非洲譯著,大致可以呈現原著的架構與面貌。謝炘更是克服口述者與筆述者的距離,獨自翻譯《飛行記》,緊貼其所依據的日譯本,一一呈現原著專業性較高的內容,已然告別早期方向迷失的問題,對於晚清小說界而言,無疑是「地理小說」範本。
針對晚清人士的翻譯實踐,學界陸續出現各種研究。早於明清的宗教文本翻譯,便有翻譯改寫的現象,如李奭學(1956-)研究明末耶穌會的印刷文本,歸納各種譯作行為的「動詞」,如「授」、「述」、「口授」、「口譯」、「口說」、「譯述」、「演」、「譯義」、「達辭」及「撰述」等,都凸顯翻譯改寫的現象。發展到晚清譯本,名目更多,如陳大康(1948-)提及晚清各種譯著標為「譯述」、「編譯」、「譯演」、「譯意」、「譯編」、「意譯」、「譯著」、「輯譯」與「演譯」等。這些翻譯改寫的名目諸多,卻殊途同歸,透過改寫模式,重塑一更能符合自身語境的譯本內容。王宏志指出譯者不容易為傳統讀者所接受的部分刪改,盡量配合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口味,「這時期的翻譯風尚,仍是一種所謂『豪傑譯作』式的意譯或甚至『譯述』」。陳平原(1954-)提及域外小說乃是以「意譯為主的時代風尚」,指出梁啟超等人所述的英人語「譯意不譯詞」,頗為時人信奉。
針對晚清的「譯述」模式,關詩珮指出「意譯」一詞無法全面概括晚清的翻譯規範,因為它把一切重譯、重述、撰述、譯述、節述、偽譯、豪傑譯都包括在內,有些「譯作」往往經過兩三次重譯或重述而成。陳宏淑指出西方著作進入日本脈絡時,先經歷日本明治時期盛行的「飜案」譯法。所謂「翻案小說」,乃是翻譯加上改寫,與許多中國學者所稱的「豪傑譯」異曲同工,經由各種刪減、增添與改寫的過程後,進入中國,又再次經歷大幅改寫、增刪情節等。
上述「譯述」、「編譯」、「譯演」、「譯意」與「譯編」等,慣常以「意譯」為代表的概念,確實反映晚清「不忠實」的翻譯模式。可是,此一不忠實的翻譯手法,從當今的翻譯研究而言,卻又潛藏著各種跟意識形態、文學美學與社會準則等相關的大有可為的研究視野。李歐梵(1942-)透過跨文化研究視角,提出一具有啟發性的研究構想─「接枝學」:研究一棵外國的樹如何在移植到中土後產生變化,其枝葉之間的分歧和接合(也就是莫萊悌〔Franco Moretti,1950-〕所謂的「diversity」和「convergence」)。他援引莫萊悌理論,指出支柱雖然是類型,但方法絕對是從技巧的細節,也就是「device」作起,二者之間的互動和弔詭才是他的方法的原動力。晚清的翻譯固然逸出原著甚多,可是卻可能透過枝節的改變,推動文學類型的進展。如王德威(1954-)曾指出晚清翻譯或許一無所獲,但亦能學得嶄新的東西,從而改變思維方法和敘事形式:「譯文拮据的文筆、怪誕的修辭、陌生的用語、不連貫的辯證,也許只是譯者能力限制的表徵,也許更指證與外來及本地語言、知識、符號系統間的差異及斷裂。」
若就十九世紀七、八○年代的探勘非洲的文學譯本而言,因正處於文學翻譯的起始階段,比起上述各種晚清譯本的改寫幅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譯著對於原著進行大規模的變動,甚至連根拔起,抽離原著主幹,面目全非,恐怕非一般「意譯」模式所能詮釋。本書拓展可能的詮釋模式,如提出「抽離主幹」與「拼湊片段」等。「主幹」乃是原著最核心的要素與形式,涉及作者所欲投射的主旨、價值、準則與訴求,一旦遭受根本性的抽離,必然會產生徹底性的變化。譯者抽離原著的主幹,使之變為更能符合自身視域的文本。
相對於「抽離主幹」對於原著主旨中心的根本變動,「拼湊片段」則是從周圍加入譯者關懷的片段,如翻譯的過程中,嵌入滬地文人的情誼、科學原理與詩詞文采等。譯者調動/剪接/並置各種其關注的片段,從渲染情感的詩詞片段到傳播新知的新聞內容,恰能反映八○年代譯者共存的多層旨趣。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穿梭黑暗大陸:晚清文人對於非洲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的圖書 |
 |
穿梭黑暗大陸:晚清文人對於非洲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 作者:顏健富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2-01-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穿梭黑暗大陸:晚清文人對於非洲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
在世界觀轉變的浪潮中,晚清文藝論者透過虛實交錯的想像,推開世界的窗戶,發現「非洲」。本書系統性與結構性觀察此一仍有待建構的學術議題:十九世紀中國人如何/為何接受、看待與想像非洲異域?「非洲」是在怎樣的知識結構與傳播模式下進入晚清文化界?當文人譯者面向自身不熟悉的新天地時,要如何呈現或傳達異域形象?肩負不同身分背景與任務的人士,必然因自身的屬性與位置,而牽動看待域外的特定視野,承載著豐富的文化與學術訊息。觀察十九、二十世紀翻譯傳播於中國文化界的非洲文本,大多圍繞著「探勘非洲」與「冒險非洲」的主題,投射「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中國」與「世界」的思辨,隱藏著作為翻譯者與創作者的「主體」與被描寫的「他者」的對應關係,並潛伏了一個群體的命運、遭遇、認同與應變。在「跨文化行旅」的架構下,本書觀察立溫斯敦、施登萊、凡爾納與哈葛德等人探勘/冒險非洲的文本翻譯與傳播到晚清中國的途徑,進而辨析各文人譯者投射的「非洲」形象與想像,替晚清文學與文化研究,開啟更豐富的詮釋面向。
作者簡介:
顏健富
馬來西亞華人,臺大中文系學士與碩士、政大中文所博士,現任清大中文系副教授。一邊旅行,一邊寫論文,遊遍五洲多異想。著有《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多篇論文發表於一級期刊。曾獲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學術旅行化,旅行學術化,界線模糊。研究近現代文學中的世界想像、烏托邦視野、冒險文類、新地理觀、概念旅行、異國形象等議題,乃至探索十九世紀「非洲探險文本」傳入晚清文化界的軌跡,回應的是旅人根深蒂固且又蠢蠢欲動的出走欲望。
章節試閱
導論(摘錄)
四、理論思考:文本行旅、異國形象與翻譯改寫
本書在翻譯理論的思考下,試圖將「非洲探勘/冒險記」,置入「跨文化行旅」的架構,觀察相關文本的接受與衍變。「行旅」並非指向普遍定義的休閒旅行,而是強調文本從此點到彼點的空間傳播。於此行旅路線,譯本從原著的既定認知框架,發展到另一有著不同價值認知的文化脈絡時,必然與他方文化語境碰撞、排斥、分歧與交流等,造成語言文字、概念表述與情節片段的變調。
(一)跨文化行旅與異國形象
湯普森(John Thompson,1951-)早已指出「全球化」可追溯至十九世紀...
四、理論思考:文本行旅、異國形象與翻譯改寫
本書在翻譯理論的思考下,試圖將「非洲探勘/冒險記」,置入「跨文化行旅」的架構,觀察相關文本的接受與衍變。「行旅」並非指向普遍定義的休閒旅行,而是強調文本從此點到彼點的空間傳播。於此行旅路線,譯本從原著的既定認知框架,發展到另一有著不同價值認知的文化脈絡時,必然與他方文化語境碰撞、排斥、分歧與交流等,造成語言文字、概念表述與情節片段的變調。
(一)跨文化行旅與異國形象
湯普森(John Thompson,1951-)早已指出「全球化」可追溯至十九世紀...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導論
一、前言
二、研究主題:非洲探勘/冒險記
三、非洲形象:「黑暗大陸」的演繹與變調
四、理論思考:文本行旅、異國形象與翻譯改寫
五、本書架構與論文出處
第一章 傳教、旅行與研究:立溫斯敦非洲傳記的翻譯與傳播
一、前言
二、譯本的發生:從留美學生計畫到世界地理學的傳播
三、非洲人體標籤:中國禮教與西方殖民話語的交疊
四、文人化的非洲視野:「研究」與「傳教旅行」的選擇
五、接受視野:晚清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的凸顯
六、結語
第二章 從上海天主教會、文藝圈到域外遊記:論《三洲遊記》對於施登萊Thro...
一、前言
二、研究主題:非洲探勘/冒險記
三、非洲形象:「黑暗大陸」的演繹與變調
四、理論思考:文本行旅、異國形象與翻譯改寫
五、本書架構與論文出處
第一章 傳教、旅行與研究:立溫斯敦非洲傳記的翻譯與傳播
一、前言
二、譯本的發生:從留美學生計畫到世界地理學的傳播
三、非洲人體標籤:中國禮教與西方殖民話語的交疊
四、文人化的非洲視野:「研究」與「傳教旅行」的選擇
五、接受視野:晚清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的凸顯
六、結語
第二章 從上海天主教會、文藝圈到域外遊記:論《三洲遊記》對於施登萊Thro...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