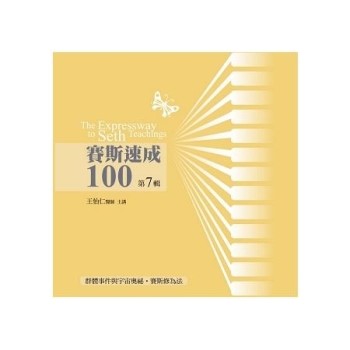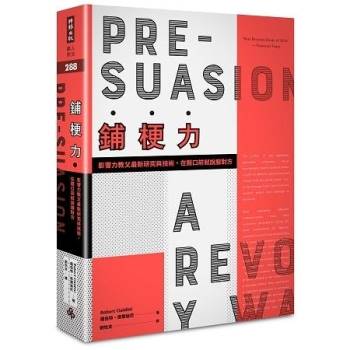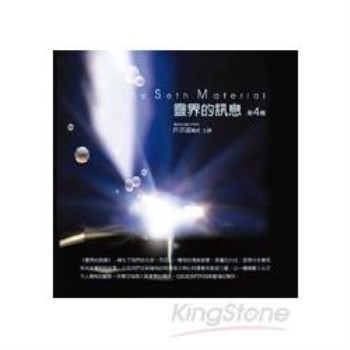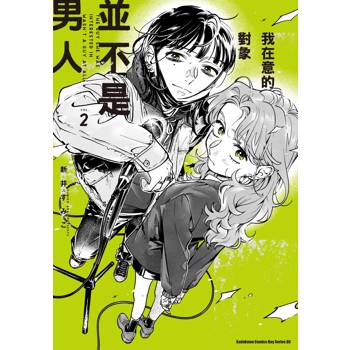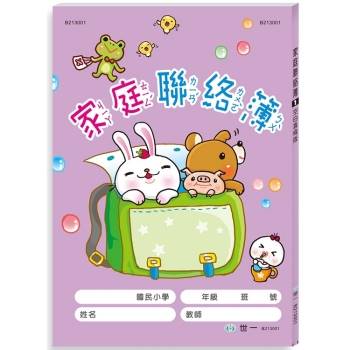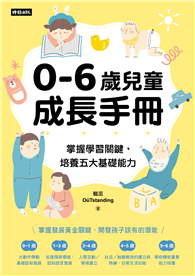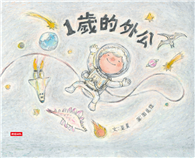序言
這本書選錄1991年筆者進臺大碩士班以來近30年間發表的8篇論文(參見附錄二),主題均環繞在清代臺灣的農墾、地權和契約。最晚發表的一篇是第八章〈從番屯到隘墾〉,其實也是最早寫成的。這篇文章原本是1996年完成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以桃園大溪地區為中心〉中的一章,當時因指導教授吳密察的推薦而得以獲邀在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的「臺灣開發史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並收入會後出版的論文集中。但當我著手要將相關論文改寫成專書,重讀這篇早年的文章時,唯一還算好的就只有字裡行間散發著的年輕熱情,至於其史料解讀、章節架構、論證分析等,雖還不至於不忍卒睹,卻難免臉紅心悸。相信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原本只想動手微調,最後變成徹底打掉重建,完全是一篇新的文章。整本專書的修改過程心情類皆如此複雜,既是困窘卻又感覺良好,最重要的不是自己在學術能力上的精進成長,而是清楚感受到了30年來臺灣史研究的深化、累積和擴展。因此,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本專書雖可說是「舊作」,卻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調整,目的是希望這不會只是本論文集,而是有著內在架構、有機連結,可以反映學術累積並展望未來的專書。
最早寫成的第八章〈從番屯到隘墾〉,卻列在大致依年代先後編排的專書之末,其實也反映了自己30年來的研究發展歷程。由於大學以來先後受到林瑞明教授、吳密察教授以及曹永和教授的影響,我最早有興趣的研究領域很自然就落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關注近山地區林野地權的爭奪與控制。不過,就在寫作碩論的最後階段,施添福教授的臺灣歷史地理學吸引了我的高度注意,因此也選擇今桃園市大溪區舊稱三層埔的地方,進行小區域的個案研究。但當時從事三層埔的早期歷史研究,目的在於理解日治時期林野整理的歷史背景,其主要關懷是19世紀的晚清時期。當時完全沒有預期,我後來就由此踏入清代歷史研究,而且年代越做越早,眼光則漸趨下層,從國家統治政策下到地方社會。最近幾年已經上溯到了17世紀末明鄭到清的政權轉換期間,也就是本書在第一章〈緒論〉之後最一開始的兩章。
這本書的主題是清代臺灣的墾荒與地權。墾荒作為一種制度,首先展現的就是國家的土地政策和稅收管理,凡是無主荒地依法須向基層縣官請准之後,才得以招佃墾殖,且在墾成之後陞科納稅、登載帳冊,成為民可自世其業的民田。研究墾荒制度的目的並不在於強調清朝統治臺灣的制度性規範,而是試圖理解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發展。這是因為墾荒制度是在清初地方官員爭奪土地與稅收的環境下擴大發展,而移民社會則是在拓墾定居的過程中形成;清朝統治兩百餘年期間無疑是臺灣最重要的移墾階段,特別是適於農墾、人口聚集的西部平原,而這同時表示官府的行政管理成為重建與理解臺灣社會的關鍵。
墾荒與定居就涉及了土地的權利主張及其長期控制。國家制度及法規成為合法地權主張的源頭,契約書寫及租佃關係則是各關係人安排權利義務最為簡便可行的介面,能彈性有效地因應隨著國家政策而來的各種變動。本書在方法上將契約當成是一個清代臺灣史的課題來提問,視為一個整體的文獻類別與現象,來理解清代臺灣出現大量土地契約文書的歷史與社會意義。現存為數頗為龐大的契約,不僅曾是歷史時期作為產權證明的重要文件,也是人們重建與理解地方歷史的關鍵史料。我個人因此期待,經由研究的進行可以了解現在人們普遍熟知的地方歷史,是在怎樣的結構與意識形態下產生,最終則是希望為臺灣地方歷史的全面改寫,提供新的可能視角與方法。
我之所以在此重講一次專書的課題,不是要說這本書已經順利達成原本設定的目標,其實目前的成果大概只能勉強算是開了個頭。因為若要理解契約與地方歷史建構,至少還得將研究延伸到晚清的開山撫番、清賦事業,日治初期的地籍整理、舊慣調查、鄉土研究、新式土地臺帳、登記制度等等,講述國家建構一套新的地權概念、地籍系統,以及社會接受新系統的同時卻更相信舊式契約所建構的地方歷史。然後還要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思考重新改寫地方歷史的方法,做出具體的替代性說法。但與其期待自己還有另一個可以全心投入研究的30年,倒不如寄望有人願意探索這個研究領域。
雖然一本書橫跨30年,這幾年改寫的過程中,腦海裡縈繞的卻總是年輕時從事研究的過往。研究生時期儘管經濟困頓,缺少資助,研究卻做得十分開心,跑了很多地方埋首查閱資料,每天都非常興奮。臺大無疑是最值得「發掘」的寶庫,因為校方當年未珍惜帝大遺產,珍貴的日文史料總是散亂在各級圖書館的陰暗角落,舊總圖、文圖、研圖、法圖,以及農經系、昆蟲系、森林系、植物系等,常會有令人驚喜的發現。相較於臺大,當時還位於新生南路、繼承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而來的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其日文舊籍則有比較完善的整理,館藏的宣傳手冊、期刊及政府公報等,相當完備。還有幾次去了分館位在新店檳榔路的書庫、摩門教金華街教堂、桃園土地改革訓練館、黎明新村省地政處、大溪地政事務所等等。最深刻的印象是1995年開始去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查閱總督府檔案。當時為了來得及一開門就調閱資料,往往從臺北搭乘最早一班的國光號。午餐時若不願花時間跟著員工一起搭交通車去餐廳,還得麻煩警衛先生幫忙訂便當。偶爾因為要看的檔案較多,也會投宿一晚300元的中興旅社。那時候,總督府檔案已翻拍成16厘米膠捲,雖然效果不是很好,時常斷片,實際上是非常方便。只是利用的人一直不多,兩臺微捲機就放在三樓整理組的辦公室裡,等於是跟大家一起上班。整理組、圖書室以及警衛室的員工們都很親切,總會特別招呼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現在回頭想想,我那時候皮夾一打開只有各式各樣的影印卡,認識最多的應是第一線的館員們。雖然彼此當年都沒沒無聞,沒能記下姓名,還是應該趁此機會感謝他們。
就跟長期以來一直受惠於圖書文獻館員一樣,兩次在臺大出版專書的過程,受到了湯世鑄總編輯、蔡旻峻編輯、洪麗崴編輯等人的鼎力協助,他們的編輯專業常令我欽佩不已。臺大能有今天的學術成就,不應忽視他們的巨大貢獻。
最後,我想將此書獻給先父李德裕(1940-2017)在天之靈。當我自己也有了家庭,才多少能夠體會,他何能如此認命日以繼夜的辛勤勞動。小時候,父親為了多掙些錢,除了佃耕4分多的水田外,河裡捕魚抓蝦、農場放陷阱捉鼠、建築工地做土水、跟團赴遠地插秧割稻、山裡抽藤等,樣樣都做,從無片刻休息。印象深刻的還有,政府鼓勵農村機械化後,家裡也向農會貸款買了久保田牌的小型耕耘機。常常,當我們起床準備吃早餐,他已經去幫耕了一些田回來。假日沒上學時會被吩咐中午去送便當,母親總是指著大概的方向說去田洋、溪埔(西)、湖底(南)、鐵枝路(東)或農場邊(更遠的東邊),就會看到。確實沒必要說精確的地點,因為村外一望無際的田地裡,常只有他一個人捨不得中午短暫休息,還戴著斗笠開著耕耘機在耕田,不管溽暑寒冬或颳風下雨。父親有著極為悲苦的童年,卻從不怨天尤人;從沒上過一天學的他,剛毅正直,通情達理,敬天尊神。他跟我的母親以及村裡的居民,無疑是最接近土地的人,卻也常被歷史切離得最遠。我也期待自己未來能有機會為眾多無名的鄉村及農民們寫些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