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台灣蘭科植物圖譜的圖書 |
 |
台灣蘭科植物圖譜:探索野生蘭的演化、歷史與種類鑑定 作者:林讚標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2-04-2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810 |
二手中文書 |
$ 1264 |
中文書 |
$ 1264 |
Books |
$ 1440 |
休閒生活 |
$ 1440 |
科學科普 |
$ 1520 |
大學出版品 |
電子書 |
$ 1600 |
動\植物 |
$ 1600 |
自然科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台灣蘭科植物圖譜
台灣野生蘭的數目已邁入新的高峰,累積四大亞科97屬超過470種。本書正是一本最新、最完整的台灣蘭科植物誌,帶你深入台灣野生蘭170餘年來國際與本土學者努力之下的採集研究歷史、最新的演化觀念,同時教導你學習分辨野生蘭的不同種類。
本書依照蘭花五大亞科的系統編排,作者娓娓道來台灣野生蘭的發現過程,描述花器構造,繪製蘭花線描圖,拍攝原花解析照片,並提供花期、分布與生育環境資訊,裡裡外外透徹呈現蘭花分類的關鍵特徵。更重要的是,本書幫助你了解並建立110百萬年來蘭科的演化觀念。
無論你是專業分類學者、有志學習蘭科植物分類學的入門學子,或者是業餘野生蘭花愛好者,本書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重要參考書。
本書特色
◆ 五大亞科下各類群依屬名與學名之A至Z排列,易於查閱。
◆ 500張手繪圖,近550張稀有物種與原花解析彩色照片,清晰呈現台灣野生蘭的內外特徵。
◆ 「蘭亞科、族與亞族演化關係卡通圖」彩色拉頁,讓你按圖索驥,透過相似外型,查詢到野生蘭的屬與種。
◆ 各級檢索表協助你鑑定任何一種野生蘭植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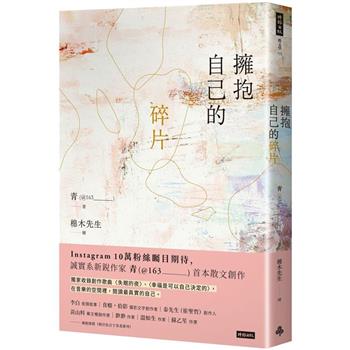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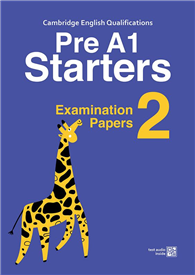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