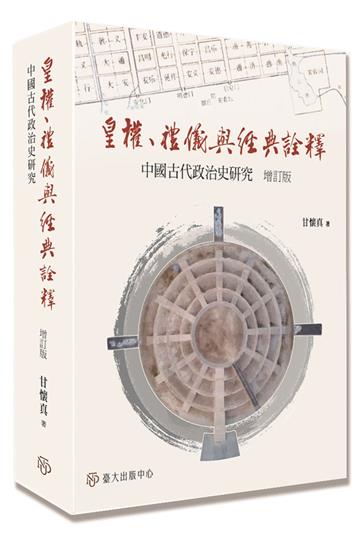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632 |
中國歷史 |
$ 704 |
中文書 |
$ 720 |
社會人文 |
$ 720 |
歷史 |
$ 720 |
社會人文 |
$ 760 |
大學出版品 |
電子書 |
$ 80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
二十一世紀以來,如何從中國歷史自身的脈絡探討中國歷史上的諸現象,成為新的中國史研究的使命。本書立基於此構想,希望能有新立場與視野,以經典詮釋(hermeneutics)為方法,從禮儀的角度,探究中國古代(約十世紀以前)皇帝制度與皇權的方方面面。對郊祀禮、喪服禮、「國家」制度、君臣關係等史學課題的探討,允為尖端研究。
本書收錄十四篇論文,分作三大主題:一是禮制的演變與儒教國家成立;二是「國家」與君臣制度;三是東亞世界中的皇帝制度。第十四篇論文為附錄,討論「皇帝制度是否為專制」。此外,作者另撰導讀一篇,題為「再論儒教國家」。本書的研究角度與方法,不但可去除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政治的若干刻板印象,亦可帶領讀者探索過去政治史研究較忽略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