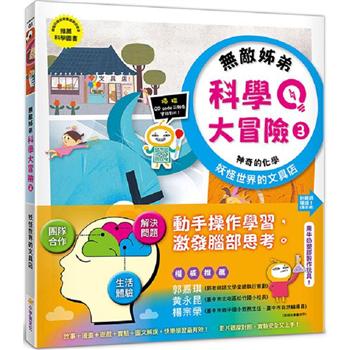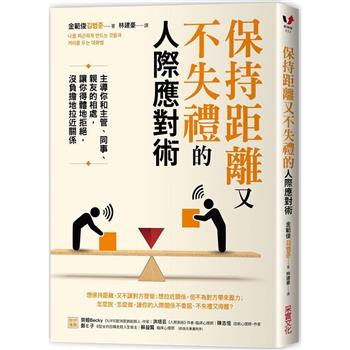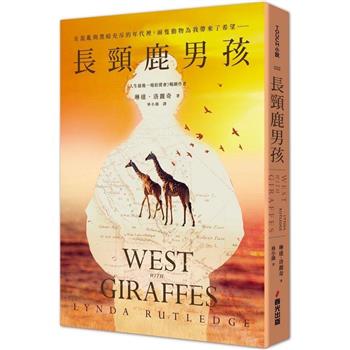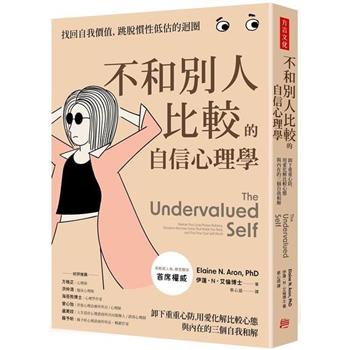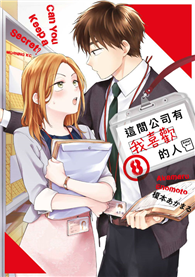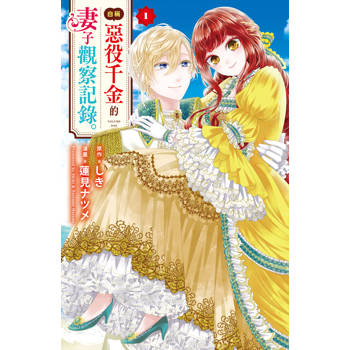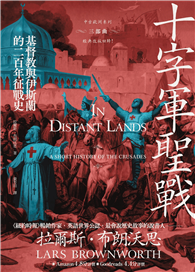唐君毅先生是近代中國最受人注目的一位思想家,惟大部分關於他的討論均忽視了其思想背後的問題意識:唐先生的思想實是對「唯物主義」所作的一個回應。至於唐先生回應唯物主義的方法,並非純然破斥唯物主義的不足,而是強調吾人當開拓一己的心靈,藉以從唯物主義中超拔出來。簡言之,唐先生是希望我們成為更健全的人,從而由最平凡的道理中察看出神聖的價值。
本書嘗試以一嶄新的角度闡釋唐君毅先生的思想及其當代意義,系統地論述唐先生的哲學視域、文化理論與修養工夫,全書不但內容豐富,並有作者的獨特見解,其當對讀者了解唐先生思想的價值乃至當代新儒學的特色有所啟發。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即凡見聖:唐君毅人學論的圖書 |
 |
即凡見聖:唐君毅人學論 作者:趙敬邦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3-03-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10 |
二手中文書 |
$ 395 |
中文書 |
$ 440 |
中國哲學 |
$ 450 |
哲學 |
$ 450 |
社會人文 |
$ 450 |
社會人文 |
$ 475 |
大學出版品 |
電子書 |
$ 500 |
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即凡見聖:唐君毅人學論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趙敬邦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宗教及神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及新亞研究所佛學中心副研究員。著有Thomé H. Fang, Tang Junyi and Huayan Thought: A 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Response to Scient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16)、《激盪即無礙:佛教與儒道思想的互動》(2020)和《唐君毅與香港》(2023)等書籍,學術興趣主要為儒家與佛教之間的對話。
趙敬邦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宗教及神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及新亞研究所佛學中心副研究員。著有Thomé H. Fang, Tang Junyi and Huayan Thought: A 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Response to Scient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16)、《激盪即無礙:佛教與儒道思想的互動》(2020)和《唐君毅與香港》(2023)等書籍,學術興趣主要為儒家與佛教之間的對話。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導論
一、當前的文化問題
二、當前問題的根源
三、本書結構
第二章 視域
一、緒言
二、內容
三、性質
四、方法
五、小結
第三章 文化
一、緒言
二、孝親
三、愛情
四、政治
五、經濟
六、死亡
七、小結
第四章 工夫
一、緒言
二、慎獨
三、辦學
四、啟示
五、讀寫
六、小結
第五章 結語
一、理論困難芻議
二、理論困難再議
三、範式轉移
四、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五、解決問題的希望
跋語
引用書目
索引
第一章 導論
一、當前的文化問題
二、當前問題的根源
三、本書結構
第二章 視域
一、緒言
二、內容
三、性質
四、方法
五、小結
第三章 文化
一、緒言
二、孝親
三、愛情
四、政治
五、經濟
六、死亡
七、小結
第四章 工夫
一、緒言
二、慎獨
三、辦學
四、啟示
五、讀寫
六、小結
第五章 結語
一、理論困難芻議
二、理論困難再議
三、範式轉移
四、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五、解決問題的希望
跋語
引用書目
索引
序
自序
唐君毅先生是筆者最喜歡的思想家,而本書則是筆者對唐先生思想所作的闡釋。初次接觸唐先生的思想是就讀預科的時候。當時香港的預科設有公開考試,該試則設有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唐先生所撰的〈與青年談中國文化〉是該科六篇指定考試範文之一。作為預科的學生,筆者其時對各篇文章均沒有太大的感覺,惟記得任教該科的羅澤民老師曾告誡同學:「唐君毅先生是哲學大師,是近代中國最有學問的其中一位人物,大家閱讀他的文章時要比閱讀其他作者的文章更加小心。」也許是懾於「哲學大師」的稱號,筆者其時便對「唐君毅」這一名字留下深刻印象,並以較為謹慎的態度閱讀〈與青年談中國文化〉一文。惜閱讀時總覺唐先生的文筆不太流暢,文章的重點亦不易把握,及後雖找來收錄該文的《青年與學問》細讀,但閱畢全書後對唐先生的印象未有改善,甚至有一種苦讀的感覺,遂生起考試過後便不再閱讀由他所撰文字的想法。到預科即將畢業,一日在校內巧遇向來尊重的郭志偉老師,隨便問及有什麼書籍值得在暑假閱讀。本是隨便的一問,但郭老師卻認真地在白紙寫上「《人生之體驗續編》.唐君毅」數字,並言該書對筆者培養沉穩的性格和開拓廣闊的胸襟有莫大幫助。筆者當時只奇怪為何不同老師均如此重視唐君毅此人?難道對他的不佳印象只是筆者的個人問題?是以,遂下定決心在暑假把《人生之體驗續編》由頭至尾、逐字逐句精讀,終發現唐先生所講的道理實非常高遠,之前未能掌握他的觀點純然是筆者自己的輕浮所致。至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本科時副修哲學,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選修了由劉國強老師任教的「先秦儒學」。劉老師是唐先生晚年的學生,其在課上特別喜歡引用唐先生的觀點,而在課後則常與學生分享唐先生的軼事。由此,均加深了筆者對唐先生其人其事的興趣和認識,並開始養成閱讀唐先生著作的習慣,繼而把唐先生的著作一本一本地閱讀,甚至以他的思想為題完成研究院的課程。適值近年香港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發生巨變,筆者亦與很多港人一樣思考在新的環境下當如何自處,並反省多年所學對於吾人當下處境究竟有何意義。恰巧去年新亞研究所所長劉楚華教授委託筆者為所內碩博士班同學講授「唐君毅哲學研究」一課,其正好給予筆者一次對唐先生的思想作系統整理的機會。屈指一算,由最初在預科時接觸唐先生的思想,到後來在研究所講授他的學問,至今已二十多年。本書即為筆者對其所作理解的一個小結。
唐先生的思想博大,每人均能循自己的視角對之更作了解。但誠如唐先生在《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中所言:「一切創造我所願學之學術文化之過去人類皆為我之師;而一切現在可能與我互相促進學術文化之陶養者,皆為我之友;一切我之教育之努力所能影響之未來人,皆為我之弟子。」的確,一人之所以對一事或一物作如此這般的了解,背後實涉及無數人對該人的影響;而一人對一事或一物所作的了解,亦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其他人。筆者在本書的立論無疑受著無數人的影響,相信有關立論亦難免多少影響著一些人往後的看法。惟本書的立論如有不濟的地方,其仍是筆者的責任,還請讀者親自翻閱唐先生的著作以求獲得更合理的解讀;假如本書的立論有可取之處,卻賴多年來對筆者有著正面影響的人士。是他/她們讓筆者認識到世界實有不同的價值,故不必以單一價值作為評價事物的唯一標準;正是評價事物可有不同標準,但吾人卻往往用一己的標準來否定他人的標準,故我們才有需要尋找一讓不同價值可以並行不悖的方法。唐先生在哲學上的最大貢獻,正是提出了一個方法以供我們參考。筆者即循以上視角來理解唐先生的思想;也許,是唐先生的思想早已影響筆者當循這一視角來理解世界。感謝所有曾對筆者有過啟發的師友,以及一直支持筆者的家人。沒有這些啟發和支持,相信筆者不會懂得以現有的視角來理解唐先生的思想;不循現有的視角來理解唐先生的思想,便自然不會有如今這本書的出現了。
唐君毅先生是筆者最喜歡的思想家,而本書則是筆者對唐先生思想所作的闡釋。初次接觸唐先生的思想是就讀預科的時候。當時香港的預科設有公開考試,該試則設有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唐先生所撰的〈與青年談中國文化〉是該科六篇指定考試範文之一。作為預科的學生,筆者其時對各篇文章均沒有太大的感覺,惟記得任教該科的羅澤民老師曾告誡同學:「唐君毅先生是哲學大師,是近代中國最有學問的其中一位人物,大家閱讀他的文章時要比閱讀其他作者的文章更加小心。」也許是懾於「哲學大師」的稱號,筆者其時便對「唐君毅」這一名字留下深刻印象,並以較為謹慎的態度閱讀〈與青年談中國文化〉一文。惜閱讀時總覺唐先生的文筆不太流暢,文章的重點亦不易把握,及後雖找來收錄該文的《青年與學問》細讀,但閱畢全書後對唐先生的印象未有改善,甚至有一種苦讀的感覺,遂生起考試過後便不再閱讀由他所撰文字的想法。到預科即將畢業,一日在校內巧遇向來尊重的郭志偉老師,隨便問及有什麼書籍值得在暑假閱讀。本是隨便的一問,但郭老師卻認真地在白紙寫上「《人生之體驗續編》.唐君毅」數字,並言該書對筆者培養沉穩的性格和開拓廣闊的胸襟有莫大幫助。筆者當時只奇怪為何不同老師均如此重視唐君毅此人?難道對他的不佳印象只是筆者的個人問題?是以,遂下定決心在暑假把《人生之體驗續編》由頭至尾、逐字逐句精讀,終發現唐先生所講的道理實非常高遠,之前未能掌握他的觀點純然是筆者自己的輕浮所致。至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本科時副修哲學,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選修了由劉國強老師任教的「先秦儒學」。劉老師是唐先生晚年的學生,其在課上特別喜歡引用唐先生的觀點,而在課後則常與學生分享唐先生的軼事。由此,均加深了筆者對唐先生其人其事的興趣和認識,並開始養成閱讀唐先生著作的習慣,繼而把唐先生的著作一本一本地閱讀,甚至以他的思想為題完成研究院的課程。適值近年香港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發生巨變,筆者亦與很多港人一樣思考在新的環境下當如何自處,並反省多年所學對於吾人當下處境究竟有何意義。恰巧去年新亞研究所所長劉楚華教授委託筆者為所內碩博士班同學講授「唐君毅哲學研究」一課,其正好給予筆者一次對唐先生的思想作系統整理的機會。屈指一算,由最初在預科時接觸唐先生的思想,到後來在研究所講授他的學問,至今已二十多年。本書即為筆者對其所作理解的一個小結。
唐先生的思想博大,每人均能循自己的視角對之更作了解。但誠如唐先生在《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中所言:「一切創造我所願學之學術文化之過去人類皆為我之師;而一切現在可能與我互相促進學術文化之陶養者,皆為我之友;一切我之教育之努力所能影響之未來人,皆為我之弟子。」的確,一人之所以對一事或一物作如此這般的了解,背後實涉及無數人對該人的影響;而一人對一事或一物所作的了解,亦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其他人。筆者在本書的立論無疑受著無數人的影響,相信有關立論亦難免多少影響著一些人往後的看法。惟本書的立論如有不濟的地方,其仍是筆者的責任,還請讀者親自翻閱唐先生的著作以求獲得更合理的解讀;假如本書的立論有可取之處,卻賴多年來對筆者有著正面影響的人士。是他/她們讓筆者認識到世界實有不同的價值,故不必以單一價值作為評價事物的唯一標準;正是評價事物可有不同標準,但吾人卻往往用一己的標準來否定他人的標準,故我們才有需要尋找一讓不同價值可以並行不悖的方法。唐先生在哲學上的最大貢獻,正是提出了一個方法以供我們參考。筆者即循以上視角來理解唐先生的思想;也許,是唐先生的思想早已影響筆者當循這一視角來理解世界。感謝所有曾對筆者有過啟發的師友,以及一直支持筆者的家人。沒有這些啟發和支持,相信筆者不會懂得以現有的視角來理解唐先生的思想;不循現有的視角來理解唐先生的思想,便自然不會有如今這本書的出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