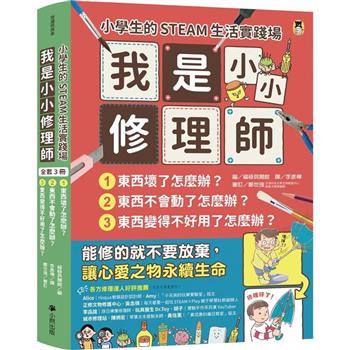第一章 心學《易》流別之始?—《童溪易傳》定位商榷(摘錄)
《童溪易傳》,一曰《童溪王先生易傳》,作者為南宋王宗傳。宗傳字景孟,號童溪(以下簡稱「童溪」),福建寧德人。孝宗淳熙八年(1181)進士,曾為韶州教授,生卒年不詳,《宋史》無傳。傳世之作僅有是書。
《四庫全書總目》(本章下稱《總目》)以為,是書涉於異學,雖鮮有學者誦習,但卻與楊簡(以下簡稱「慈湖」)《易》學宗旨相同,明萬曆以後以心學說《易》的風氣,實自二人起始。
倘是書真如《總目》所言,乃心學《易》流派之原始,即使四庫館臣評價不高,在學術發展史中,仍應具有相當程度的關鍵地位。但問題在於,是書是否的確以心學詮說《易經》?並與慈湖宗旨相同?甚至還涉入異學?《總目》的說法根據何在?
近現代人關於是書的研究不多,較早為1994年康雲山之博士論文,康文以專章討論童溪《易》學,並視之為南宋心學《易》的脈絡之一。之後則是1995年朱伯崑《易學發展史》,朱氏對於《總目》之說不以為然,認為童溪之學不屬心學體系,不宜與慈湖《易》學視為同一系統,但朱書對於童溪學術亦僅寥寥數語帶過,未能詳述;2005年張素梅在大陸期刊中介紹是書現存善本;至2009年,姜穎則有博士論文研究是書,對童溪的學術定位大抵依循《總目》之說;同年,姜氏又發表一篇期刊論文,論述童溪如何由承續程伊川「隨時從道」的思想,轉化為「隨吾心之正」的心學《易》理路。
綜觀《總目》之說與近人研究,《童溪易傳》一書的學術定位,顯然言人人殊,部分學者仍延續《總目》之說,視是書屬心學《易》之脈絡;但亦有學者提出不同見解,將之劃出心學《易》的範疇。筆者擬先釐清《總目》的文意,然後探討是書在南宋以後的大致影響,以及歷來學者對是書的評價,耙梳出自宋以來對《童溪易傳》一書的引用及評論概況,以觀察《總目》說法與歷史事實是否相符。其次,論述《童溪易傳》書中要旨,檢視是書如何詮解《易》中思想。再次,比較是書與楊慈湖《易》學之內容,以見二人是否同樣以心學說《易》。最後為結語。
一、《童溪易傳》之影響及評論
在《總目》中,四庫館臣論及以心學詮說《易經》的趨向時,總是以負面的態度評論,且屢屢提及童溪《易》學。先看《總目》對是書的評論:
【《童溪易傳》三十卷】宋王宗傳撰。宗傳字景孟,寧德人。淳熙八年進士,官韶州教授。……宗傳之說,大概祧梁、孟而宗王弼,故其書惟憑心悟,力斥象數之弊,……焞序述宗傳之論,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語,不免涉於異學,與楊簡慈湖《易傳》宗旨相同。蓋弼《易》祖尚元[玄]虛,以闡發義理,漢學至是而始變。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然胡、程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故似淺近而醇實;宗傳及簡祖其元[玄]虛而索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窅。……然則以禪言《易》,起於南宋之初,特作喆無成書,宗傳及簡則各有成編,顯闡別徑耳。……錄存是編,俾學者知明萬歷[曆]以後,動以心學說《易》,流別於此二人,亦說《周禮》者存俞庭椿、邱葵意也。
此段文字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論點。首先,《總目》因為林焞之序而將童溪與慈湖二人之《易》學視為涉於異學、以心學說《易》,王、楊乃同一路數,故論及學術利弊,往往二人同論。其次,童溪《易》學承自王弼,祖尚玄虛之心性與天道,而與胡瑗、伊川歧出,罕及人事,是以有高深幻窅之病。第三,童溪與慈湖不但因此成為明代後期以心學說《易》流別之始,甚至南宋之初以禪言《易》之現象,亦與二人不無關係。
《總目》的這三個論點,息息相關,而第三個論點,更是在前兩個論點的基礎上,進一步定位楊、王二人在學術史上的影響。關於三點議論的問題,下文將會有詳細的說明。但不論哪一個論點,顯然《總目》對童溪此書的評價相當負面,既然如此,何以《四庫全書》仍要收錄是書?四庫館臣解釋其中因由,即如同收錄俞庭椿《周禮復古編》之情形,「特存其書,著竄亂聖經之始,為學者之炯戒焉。」
在慈湖《楊氏易傳》的提要中,《總目》亦有類似的言論:
【《楊氏易傳》二十卷】宋楊簡撰。……簡之學出陸九淵,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為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略,……考自漢以來,以老、莊說《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始王宗傳及簡。宗傳,淳熙中進士;簡,乾道中進士,皆孝宗時人也。顧宗傳人微言輕,其書僅存,不甚為學者所誦習。簡則為象山弟子之冠,……又歷官中外,政績可觀,在南宋為名臣,尤足以籠罩一世,故至於明季,其說大行。……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心性之理,未嘗不蘊《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遂流於恍惚虛無耳。昔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不刪鄭康成所引讖緯之說,謂存之正所以廢之。……今錄簡及宗傳之《易》,亦猶是意云。
慈湖係象山高足,承象山「心即理」之說,將心學發揚光大,其學術立場相當明確,其書以心學說《易》,自無可疑。而《總目》「存之正所以廢之」之說,正與上文說明收錄《童溪易傳》的原因相仿,即以此作為負面示範,提醒學者避免再入歧途。
《總目》在這段文字中,同樣重複了第三個論點,述說慈湖與童溪乃以心性說《易》之始祖,而慈湖於後世影響尤深,明季之《易》入禪,似乎慈湖得負起不小的責任。值得留意的是,此處點出童溪「人微言輕,其書僅存,不甚為學者所誦習」,似意指此書鮮有學者聞問,故在以心性說《易》的流衍上,影響遠不若慈湖。
今考南宋以來注《易》諸書,引用《童溪易傳》者並不算少,如南宋方實孫《淙山讀周易》、俞琰《周易集說》,元代董真卿《周易會通》、胡震《周易衍義》、李簡《學易記》、王申子《大易緝說》、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明代胡廣《周易大全》、蔡清《易經蒙引》、姜寶《周易傳義補疑》、金賁亨《學易記》、逯中立《周易札記》、熊過《周易象旨決錄》、鄢懋卿《易經正義》、孫從龍《易意參疑》、張元蒙《讀易纂》、張振淵《周易說統》,清代刁包《易酌》、晏斯盛《易翼說》、喬萊《易俟》、胡世安《大易則通》、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陸奎勳《陸堂易學》、王又樸《易翼述信》、沈起元《周易孔義集說》、程廷祚《大易擇言》、王宏《周易筮述》、吳汝綸《易說》、強汝諤《周易集義》、翟均廉《周易章句證異》,民國馬其昶《周易費氏學》、張其淦《邵村學易》等,就筆者所見,約計有32家,雖不算多,但亦不在少數;且歷時數代,自宋至民國,並未湮絶。其中《淙山讀周易》等九書,直接引用次數更多達40次以上,甚至有上百次之多。此一現象,至少可證明此書並非完全沒有受到重視。
如果反覆咀嚼比較《總目》對《童溪易傳》與《楊氏易傳》二書的提要,便不難理解四庫館臣之所以如此評論《童溪易傳》的因由,無非是為了凸顯明季以心說《易》風氣大行的現象,實與慈湖的關係更加密切,相較之下,似乎童溪並未參與助長此一風潮。倘若順著四庫館臣的角度,純粹就心學《易》的流衍來看,慈湖的影響確實遠大於童溪;但筆者要問的是,之所以造成此一現象的因由,難道真的只是因為童溪「人微言輕」?而與童溪的學術內容毫無關係?
在回答此一問題之前,也許應該先回到上文根據《總目》所引出的第一和第三個議題。第一個議題即是《總目》將慈湖與童溪視為同涉異學者,二人論《易》宗旨相同。第三個議題便是在視楊、王二人為同一路數的前提之下,認為心學《易》乃至禪學《易》始於二人。至於問及何以童溪對後世影響不如慈湖,便是由第三議題衍生而來的質疑。這個質疑,自然牽涉到對第一議題的認知,亦即應先確認童溪學術是否真應歸屬於心學派?甚至涉及異學?與慈湖同路?先解決了對第一議題的疑惑後,才能在這個基礎上繼續討論第三議題,以及其所衍生的相關質疑。
將童溪歸屬於心學派的說法,實源起於清《總目》。自《總目》出後,不但總纂官紀昀在為人作序時屢次表達此一立場,其他學者亦迭引其說以議論楊、王二人之入異學。例如清葉昌熾〈古本易鏡序〉云:「楊慈湖、王童溪之《易》,則釋氏之《易》也。」俞樾〈釋淡然周易注序〉亦云:「宋楊簡之《慈湖易解》、王宗傳《童溪易傳》皆高談心性,與禪理通。」而梁章鉅承其師紀昀之說,謂主理者使王宗傳、楊簡之說,溢而旁出,而《易》入於釋氏。王玉樹亦引《總目》之說,謂宗傳已涉異學。
上述學者的說法,均承《總目》而來,故議論相近,甚至直接視楊、王二人之《易》為釋氏之學,跳過心學的範疇。究竟《總目》之根據為何?前引《總目》謂童溪書有林焞序,序中述童溪之論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語,故「不免涉於異學」,此蓋即館臣論斷童溪語涉異學之由來。今引林序原文如下:
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童溪之論性,然也。《易》,盡性書也,而何至於多言!我知之矣。
「性本無說」一句,林氏之意究竟為何?是「性即是無」的主張?還是性原本未見討論?若四庫館臣依此論斷童溪涉於異學,顯然是將此句理解為「性即是無」,並以為童溪之說與釋氏空無之論相近,因而有涉於異學之見。
今查童溪全書,並無「性本無」一語;觀全書內容,亦無與釋氏空無之論相涉者。惟卷十觀卦有一段話謂聖人行「不言之教」的文字似較為相近,茲引述如下,以供討論。其文曰:
或曰:昔者夫子嘗欲无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何言之教,其在聖門如子貢者,猶有所未悟,今而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何也?曰:服有二,有知而服之者,有不知而服之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不知而服之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知而服之者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此一子貢也;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又一子貢也。
此處係以《論語》解釋觀卦〈彖傳〉內容。由此可看出童溪對於「聖人不言性」的主張,乃源自《論語》。此段文字雖非出自林氏之手,未必能直接解釋林序原意,但林氏作序,首先點出童溪在書中著墨最多的「性」,及其說與古代聖人的關聯,筆者可以很合理地推測林氏依循童溪「聖人不言性」的說法,進一步介紹是書內容。如果此一推測成立,那麼林序的本意應譯為:性原本沒有任何討論或說法,就連聖人(孔子)都沒有加以說明,而童溪在書中所談論的人性問題,是很正確的,因為整部《易》的要旨,都與人性相關,所以何需再多說些什麼呢!我只要讀《易》便可明白人性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心學《易》鉤沉的圖書 |
 |
心學《易》鉤沉 作者:賀廣如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4-01-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71 |
中國/東方哲學 |
$ 414 |
中文書 |
$ 414 |
中國哲學 |
$ 423 |
社會人文 |
$ 423 |
哲學 |
$ 423 |
教育學習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心學《易》鉤沉
本書耙梳了宋明學術思想史中一個特殊的途徑——以心學詮釋《易經》。全書由質疑《四庫全書總目》開端,推翻了心學《易》流別之始的認定;其次,以楊慈湖、王龍溪、季彭山、管東溟、孫應鰲等數個重要個案,建構了自宋到明以心學說《易》的脈絡,以及此一脈絡旁支蔓延的複雜關聯。全書對於海內外相關研究有充分的掌握,行文暢達,論證深入細密,資料搜羅閎富,結論信實有力,對於心學與《易》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貢獻。
作者簡介:
賀廣如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所訪問學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詩經、易經、明清學術史、中國思想史,發表多篇期刊論文,著有《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心學《易》流別之始?—《童溪易傳》定位商榷(摘錄)
《童溪易傳》,一曰《童溪王先生易傳》,作者為南宋王宗傳。宗傳字景孟,號童溪(以下簡稱「童溪」),福建寧德人。孝宗淳熙八年(1181)進士,曾為韶州教授,生卒年不詳,《宋史》無傳。傳世之作僅有是書。
《四庫全書總目》(本章下稱《總目》)以為,是書涉於異學,雖鮮有學者誦習,但卻與楊簡(以下簡稱「慈湖」)《易》學宗旨相同,明萬曆以後以心學說《易》的風氣,實自二人起始。
倘是書真如《總目》所言,乃心學《易》流派之原始,即使四庫館臣評價不高,在...
《童溪易傳》,一曰《童溪王先生易傳》,作者為南宋王宗傳。宗傳字景孟,號童溪(以下簡稱「童溪」),福建寧德人。孝宗淳熙八年(1181)進士,曾為韶州教授,生卒年不詳,《宋史》無傳。傳世之作僅有是書。
《四庫全書總目》(本章下稱《總目》)以為,是書涉於異學,雖鮮有學者誦習,但卻與楊簡(以下簡稱「慈湖」)《易》學宗旨相同,明萬曆以後以心學說《易》的風氣,實自二人起始。
倘是書真如《總目》所言,乃心學《易》流派之原始,即使四庫館臣評價不高,在...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最初,好奇的是《易》
謀於天,謀於鬼神。因為徬徨,由於無助,更有太多的不安和恐懼,在得與失之間擺盪,藉由占卜,落定自身的塵埃。但《易》絕不止於此。
感謝毓老師帶我進入《易》經的世界。在臺大就讀時,一週有三個晚上在溫州街的天德黌舍上課,學四書,上《易經》,童蒙的世界,自此打開了古典的大門。我終於知道,古書原來可以如此活讀。毓老師的全名是愛新覺羅毓鋆,是滿清皇族的後裔,生於清光緒卅二年(1906),卒於民國一百年(2011),享耆壽一百零六歲。他解說《易經》時,經常以中國現代史的人事作為例證,但他所經歷...
謀於天,謀於鬼神。因為徬徨,由於無助,更有太多的不安和恐懼,在得與失之間擺盪,藉由占卜,落定自身的塵埃。但《易》絕不止於此。
感謝毓老師帶我進入《易》經的世界。在臺大就讀時,一週有三個晚上在溫州街的天德黌舍上課,學四書,上《易經》,童蒙的世界,自此打開了古典的大門。我終於知道,古書原來可以如此活讀。毓老師的全名是愛新覺羅毓鋆,是滿清皇族的後裔,生於清光緒卅二年(1906),卒於民國一百年(2011),享耆壽一百零六歲。他解說《易經》時,經常以中國現代史的人事作為例證,但他所經歷...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緒論
第一章 心學《易》流別之始?——《童溪易傳》定位商榷
一、《童溪易傳》之影響及評論
二、《童溪易傳》要旨
三、與楊慈湖《易》學之比較
四、結語
第二章 承繼與轉化——邵康節對王龍溪《易》學的影響
一、龍溪對康節的評價
二、心與良知
三、先天後天
四、天根月窟
五、結語
第三章 陸、王之傳——楊慈湖與王龍溪
一、《易》不在書
二、心《易》與良知《易》
三、不起意與絶意去識
四、卦論
五、圖書
六、結語
第四章 季彭山的龍惕之《易》
一、明代的慈湖學
二、「龍惕說」論辯
三、《易學...
緒論
第一章 心學《易》流別之始?——《童溪易傳》定位商榷
一、《童溪易傳》之影響及評論
二、《童溪易傳》要旨
三、與楊慈湖《易》學之比較
四、結語
第二章 承繼與轉化——邵康節對王龍溪《易》學的影響
一、龍溪對康節的評價
二、心與良知
三、先天後天
四、天根月窟
五、結語
第三章 陸、王之傳——楊慈湖與王龍溪
一、《易》不在書
二、心《易》與良知《易》
三、不起意與絶意去識
四、卦論
五、圖書
六、結語
第四章 季彭山的龍惕之《易》
一、明代的慈湖學
二、「龍惕說」論辯
三、《易學...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