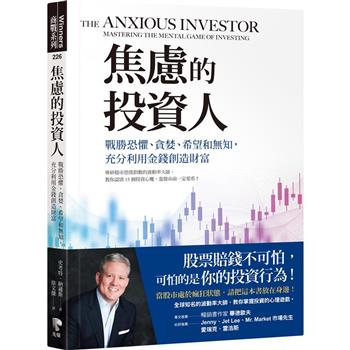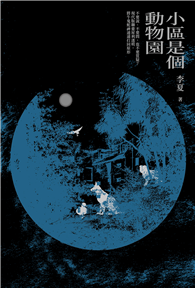導論(摘錄)
情之必要:本書問題與章次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足以當之這生命情感的試煉,是以本書名之以:《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抒情是風雲時代激盪下的天風海濤之曲,也是詩人感官情意的昇華靈視,更是見證苦難的幽咽怨斷之音,「史亡而後詩作」,成為賴以傳世的幽微心史。以抒情為方法重新蠡測清季至民初的詩學,除了可以再思五四所確立的文學典律之外,亦不免有對於抒情起源重探的意義,雖則那是傳統已經被判定(必須掃入茅坑)死亡的終點。
本書以抒情傳統為方法,擇定樊增祥、沈曾植、易順鼎、王國維等個案,緒論則頗及於陳三立,他們的抒情自我分別呈現出樂、哭、怒、悲、慟等的精神癥狀,詩歌裡滿溢著現代的感覺,舊體詩堪堪表現出的是「不壓抑的現代性」,以之重探在清民之際古典詩學的理論維度。首先探測的是詩語言的寫作技術,陳世驤在〈中國抒情傳統〉宣言裡特別強調的「言詞樂章所具備的形式結構」,高友工所強調的「美典」;本書首章以樊增祥為例,探討晚清「可能的」新詩學,從這名通脫樂觀又具吏才的文士,著眼於他擅長的豔情、滑稽詩作,析論這種「餘之餘」書寫本身是一種欲望生產,因難見巧、逆反其意,因此頗能容受現代裡千奇百怪、紛然雜遝的新事物,甚至透出對現代性的反思。他後出的〈今別離〉四章逆寫悲愁,歌頌新科技,不襲舊情,是真正的翻新之作。然而在他最負盛名的前後〈彩雲曲〉裡,面對男女歡愛、家國興亡及個人主義、民族主義擴張等,以前所未有的複雜形成多元矛盾的現代事件,而這已非紅顏禍水的詩史所能處理,詩雖已擴增為「詩史」,但已無法如明清易鼎之際形成一致一色的抒情之音,此已是舊詩裡縛不住者,內中形成不一致的抒情異響,本章以此重估樊增祥詩裡所透出的不壓抑的現代性,是為第一章〈詩之「餘」:樊增祥的「新」詩學〉。
第二個重要個案是同光魁傑沈曾植。乙盦早年即被陳衍推為同光體之魁傑,晚年自述一己平生志業全部體現在詩(詞)之中;更何況,當年張爾田就已對乙盦之史學、佛學成就作出「積薪之嘆」的判斷;顯然,沈曾植的詩歌成就、詩學理想值得進一步分析。沈曾植的學人修養使他得以調動傳統字形、字義之學,轉俗為雅,藉以表徵出其詩學理想。其佛學根柢使他的詩學思考成為內向反溯一途,易三元為三關,形成一種沉潛反思、靜謐觀想的詩學形態,是身處惡世界裡寂然不動的般若蓮華。沈曾植在1899年以詩人的知幾,敏銳與世紀末劫毀有相當的應和,沈曾植隱然也將自己的病身轉成病維摩之說法示道,那是一種雅人之憂的救劫與承擔,由一己通向了國體,以出世之說法,而行入世之悲願。他的「瘣木詩學」是抒情詩的靈視與超越,是詩境的圓滿與和諧,更是由一己而通向大我,在風雨飄搖的惡世界裡,一個昂揚而積極奮起的詩人「怒觀」,完成了士人的政治倫理之承擔;是為本書第二章〈支離瘣木撐風煙:論同光魁傑沈曾植〉。
易順鼎在當時即詩名卓著,作詩既速又富,是堪比樊山的另一「作詩機器」。其與生俱來的早慧靈心,使他感知到時代將變的末世氛圍,然而他只能以哭泣來回應這種「若創巨痛深之在體」的切身之痛,竟自號「哭盦」。早年即有幽臲鬼語之作,堪稱末世詩讖,抒情異化成為一曲穠豔哀歌。五上公車不售,繼而國變、母喪,激起他內在的死亡欲力,表現在乙未年墨絰從戎之舉,顯示古中國原有的般若空寂已經無法安頓他的靈魂,詩歌不免呈現刺怒相尋的變風變雅之作。易鼎改元,在時代風會與詩歌神思的激盪下,以「舊人物而入新世界」,他創作出具有抒情靈視的七古歌行,總結了舊時代的風華,回應了他對新世界的思考――那是愛與死結合所長養出的「惡之華」。不過,這個世界已無舊派文人施展的空間,國變釋放了內在原欲,生命呈現一種自毀傾向,詩歌滿溢抒情異響,他愈見頹唐,只能在「假得十分真」的梨園戲場裡,尋求一種可感的真實,直至「才盡」,方復歸於最後的「平靜」,是為本書第三章〈惡之華:易順鼎的抒情挽歌〉。
王國維身歷清末民初,他遭遇的不是舊時「易鼎」而是全新「革命」,當被迫進入現代,既有的價值塌陷崩毀,王國維的意義危機伴隨著他對現代體驗洶湧而至。在全新的「現代大觀」裡,王國維竟也以「觀」,予之積極回應;他的學問裡對「觀看」十分側重,從〈叔本華像贊〉裡「天眼所觀,萬物一身」的超越之道,迄於《人間詞》裡「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自我救贖之失敗,其中體現的是王國維遭遇現代極限經驗的驚詫,「人間」兼具的煉獄與道場的意義,以及詞作中雖承襲傳統體式、充斥著古典的象徵,究其實是一種「死之凝視」,透出現代的斷零經驗。從叔本華與席勒處所獲取的美學資源,既是時代的解方,也是他自救之道,向西方借來的火種具有啟蒙意味的視覺意象,但從「天眼所觀」的拔昇迄於「身是眼中人」的身外身之反視,最終無處安頓的人生價值,使之破滅成為不可承受之輕的楊花點點,是為本書第四章〈悲歡零星:王國維的現代斷零體驗〉。
從「觀」字所透出的,正是充滿末世情調的悲劇「之眼」。「憂生、憂世」,對世界有如是先在悲劇的認識,那是身處世變之際王國維的切身感受,也成為他由此超越末世的反思之道,於是他對傳統文學有了具哲理悲劇的「隻眼」創造。他在1911年以前的文學活動儘管型態互異,但悲劇「之眼」貫穿了文學批評、詩詞創作與劇本研究。本章從抉發《紅樓夢》的解脫精神,而至《人間詞話》裡因醒與痛之交嬗不息而頓生崇高之感,再迄於《宋元戲曲史》中對悲劇人物行動倫理道德價值之張揚,在在都顯現了他因應現代、重塑中體的努力,其以「悲劇之眼」打開新的文學批評境界。
王國維的文學活動既是國體的救亡,也是個人的超越,因而他在〈紅樓夢評論〉裡抉發的美學直觀,原也要通向倫理價值,也因此讓他對叔本華個人小乘式的解脫不能滿意,加之又無宗教終極信仰,第一期哲理探索遂無能為繼;轉向填詞之後,卻意外在詞話批評的斷簡裡,以文字的跳躍、近乎詩語的引譬聯想,打開新的中西混融的藝術境界。然而文學境界終究不能成為實際生活的等值之物,只能是在象徵層面上肯定了苦難的意義與價值;於是他又只能「遁而作他體」,進而以先行者之姿進入全新的劇曲研究,而終於抉發出、成就了中國悲劇,可謂隻眼,這些考察突出了他文論中的「視覺現代性」,由是說明了他在激進時代裡的先行者身分。在王國維美學—倫理學的理論視野裡,他始終更偏向了後者,本章揭開了王國維從〈紅樓夢評論〉解脫,迄於《宋元戲曲史》裡對悲劇倫理之肯定,其中所開展與完成的當不止有文學批評上的意義,那還讓王國維成為古中國「招魂人」,「三綱六紀」已然依附於其上,那即是陳寅恪所稱的「文化託命之人」,是為本書第五章〈悲劇之/隻眼:王國維的視覺現代性〉。
綜上,這一系列研究,關注到明、清、民國的遺民議題,涉及到歷史真實的重建、思想史、心態史、文學史、詩學研究等學術領域,從斷零主體、盜火者、招魂人迄於狂暴之我,抒情自我在現代裡有其多副「面孔」;另也意在探索抒情傳統論的邊界,澄清箇中的國族意識形態,檢測抒情傳統的現代解釋效力,重新開發數個個案的詩學成就及理想;在揭開這一段抒情光焰的同時,古老的「文」在危急狀態下,迸發出強大的能量,這既是傳統之發明,卻也是自我的反思,更是與當代的積極對話。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的圖書 |
 |
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 作者:曾守仁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5-01-0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
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末文士們被迫成為民國之遺民,在現代╱惡世界的情境裡,為何還要抒情(寫詩)?本書擇定樊增祥、沈曾植、易順鼎、王國維等個案,緒論則及於陳三立──他們的抒情自我分別呈現出樂、哭、怒、悲、慟等的精神癥狀,詩歌裡滿溢著「現代的感覺」,堪堪表現出「不壓抑的現代性」。抒情是風雲時代激盪下的天風海濤之曲,也是詩人感官情意昇華的抒情靈視,更是見證苦難的幽咽怨斷之音,成為賴以傳世的幽微心曲―詩是危機狀態下的語言。
作者簡介:
曾守仁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專長和研究興趣涵括:中國詩學、晚清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評點。已出版《金聖嘆評點活動研究──擬結構主義的重構與解構》、《王夫之詩學理論重構:思文/幽明/天人之際的儒門詩教觀》等專書,並發表二十多篇論文。
章節試閱
導論(摘錄)
情之必要:本書問題與章次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足以當之這生命情感的試煉,是以本書名之以:《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抒情是風雲時代激盪下的天風海濤之曲,也是詩人感官情意的昇華靈視,更是見證苦難的幽咽怨斷之音,「史亡而後詩作」,成為賴以傳世的幽微心史。以抒情為方法重新蠡測清季至民初的詩學,除了可以再思五四所確立的文學典律之外,亦不免有對於抒情起源重探的意義,雖則那是傳統已經被判定(必須掃入茅坑)死亡的終點。
本書以抒情傳統為方法,擇定樊增祥、沈曾植、易順鼎、王國維等...
情之必要:本書問題與章次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足以當之這生命情感的試煉,是以本書名之以:《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抒情是風雲時代激盪下的天風海濤之曲,也是詩人感官情意的昇華靈視,更是見證苦難的幽咽怨斷之音,「史亡而後詩作」,成為賴以傳世的幽微心史。以抒情為方法重新蠡測清季至民初的詩學,除了可以再思五四所確立的文學典律之外,亦不免有對於抒情起源重探的意義,雖則那是傳統已經被判定(必須掃入茅坑)死亡的終點。
本書以抒情傳統為方法,擇定樊增祥、沈曾植、易順鼎、王國維等...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跋
2024年6月,疫情後重訪義大利。矗立於聖彼得大教堂廣場(St. Peter’s Square)上的難民船塑像令我印象深刻。有別於以白色大理石為基調的教堂與廣場建物,名為《Angels Unaware》黑色的青銅雕像尤其顯得突兀,船上匯聚的140位難民,遷移流徙於不同時代、不同區域,再現了人類史重複的苦難。隱身於當中的天使僅露出一對翅膀,而朝向大教堂的船身,似乎隱喻著微渺希望。Unaware或意謂著流人前途未卜的將來,或者也暗示著人們應該以更開放的胸懷來接納陌生人,因為無人所知曉的天使即隱伏其中。
米蘭大教堂(Milan Cathedral)裡,再...
2024年6月,疫情後重訪義大利。矗立於聖彼得大教堂廣場(St. Peter’s Square)上的難民船塑像令我印象深刻。有別於以白色大理石為基調的教堂與廣場建物,名為《Angels Unaware》黑色的青銅雕像尤其顯得突兀,船上匯聚的140位難民,遷移流徙於不同時代、不同區域,再現了人類史重複的苦難。隱身於當中的天使僅露出一對翅膀,而朝向大教堂的船身,似乎隱喻著微渺希望。Unaware或意謂著流人前途未卜的將來,或者也暗示著人們應該以更開放的胸懷來接納陌生人,因為無人所知曉的天使即隱伏其中。
米蘭大教堂(Milan Cathedral)裡,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圖片目錄
導論 世變與抒情
一、到今日山殘水剩
二、此身合是詩人未?
三、晚清「新」詩學
四、末世之試煉/情:以抒情傳統為方法
五、抒情之必要:本書問題與章次
第一章 詩之「餘」:樊增祥的「新」詩學
一、引論
二、餘之餘:豔情與滑稽
三、餘與有:以舊人物而詠新世界
四、慷慨有餘音:詩史的變奏
五、結語:不壓抑的現代性
第二章 支離瘣木撐風煙:論同光魁傑沈曾植
一、乾淨土與惡世界
二、詩以史為
三、脫縛、解執與「活」六朝
四、乙盦「示疾」:末世的瘣木詩學
五、結語
第三章 惡之華:易順鼎的...
導論 世變與抒情
一、到今日山殘水剩
二、此身合是詩人未?
三、晚清「新」詩學
四、末世之試煉/情:以抒情傳統為方法
五、抒情之必要:本書問題與章次
第一章 詩之「餘」:樊增祥的「新」詩學
一、引論
二、餘之餘:豔情與滑稽
三、餘與有:以舊人物而詠新世界
四、慷慨有餘音:詩史的變奏
五、結語:不壓抑的現代性
第二章 支離瘣木撐風煙:論同光魁傑沈曾植
一、乾淨土與惡世界
二、詩以史為
三、脫縛、解執與「活」六朝
四、乙盦「示疾」:末世的瘣木詩學
五、結語
第三章 惡之華:易順鼎的...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