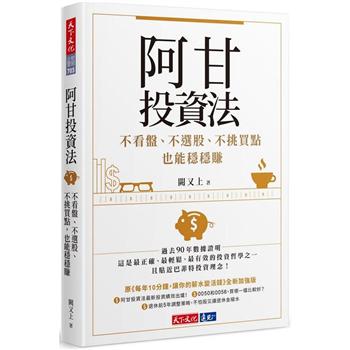從狂人、多餘的人到大寫的人
本書以魯迅、瞿秋白與曹禺為具體之實例研究,分別代表小說、散文、政論、戲劇和電影數種文類,論證文學如何結合政治,並再現於跨文類、跨領域與跨文化等多層面上。指陳「以俄為師」這一主題從晚清浪潮興起到全盤建構,其實是一系列有計畫、有組織和有系統的傳播、運動與實踐成果。呈現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戰爭、如何挑戰西方文明、如何選擇現代性,以及如何吸收俄羅斯與蘇聯以改造自我的心態與寫作風格。本書的主要研究方法奠基於比較文學與跨文化分析之上,並融入中國、日本與俄羅斯對此主題的學術成果,且與英美觀點相互辯證,勾勒出二十世紀前半葉左傾/翼文學的意識形態。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以俄為師:中國現代作家的改造的圖書 |
 |
以俄為師:中國現代作家的改造 作者:陳相因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5-01-0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97 |
中文書 |
$ 497 |
文學史 |
$ 567 |
文學作品 |
$ 567 |
小說/文學 |
$ 599 |
大學出版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以俄為師:中國現代作家的改造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相因
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語文系俄國文學暨語言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斯拉夫研究系與東方研究系兩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東亞語言文明系與斯拉夫研究系三系聯合訪問學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訪問教授,以及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俄羅斯暨蘇聯文學、比較文學與影音研究。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戰爭、傳統與現代性:跨文化流派爭鳴》與《聶隱娘的前世今生》等書。
陳相因
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語文系俄國文學暨語言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斯拉夫研究系與東方研究系兩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東亞語言文明系與斯拉夫研究系三系聯合訪問學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訪問教授,以及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俄羅斯暨蘇聯文學、比較文學與影音研究。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戰爭、傳統與現代性:跨文化流派爭鳴》與《聶隱娘的前世今生》等書。
目錄
序言
圖表目次
第一章 導論
一、「五四」百年:意識形態與體系研究
二、「以俄為師」:文藝與政治共謀
三、狂人:魯迅創作的瘋狂與馴化
四、多餘的人:瞿秋白的自我編碼、符碼與戲碼
五、「大寫的人」:曹禺、奧斯特羅夫斯基與高爾基的戲劇展演
六、跨文化例證與跨領域的研究理論和方法
第一部 以俄為師
第二章 俄蘇翻譯、中國故事與黨國怪獸
一、「故事」及其無與倫比的影響
二、五四運動、「英特納雄耐爾」與被錨定的現代性
三、再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從史達林主義到毛澤東主義
四、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期間反蘇聯修正主義的文藝浪潮
五、1980年後俄蘇文學的翻譯與文藝迴響
六、結語:回到「故事」及其敘述的影響
第二部 狂人
第三章 瘋狂與黑暗的魅惑:魯迅與果戈理的狂人蠡探
一、魯迅與果戈理的文學關係
二、「瘋狂」、「黑暗意識」與「非理性」的連結
三、鬼、神、人的遠航想像與黑暗世界的形成
四、結語
第四章 瘋狂、戰爭與現代性批判:魯迅與日俄作家的狂人系譜
一、戰爭、現代性與瘋狂
二、從清日到日俄戰爭:「黑暗意識」與現代性的批判
三、進擊的狂人:世界大戰前後瘋狂的世界文學光譜
四、結語
第三部 多餘的人
第五章 自我的編碼:「多餘的人」之發端、形成及其嬗變
一、俄羅斯「多餘的人」之發端、定義與演變
二、「編碼」:從「多餘的人」到「空人」
三、變體:「零餘者」的編碼
四、變異:「浪子」、「窺淫者」與「孤臣孽子」的問題
五、變形:讀書人的西化與孤獨者的馴化
六、結語
第六章 自我的符碼:論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
一、幕前幕後
二、登臺前的文學預演:遺/戰書〈自殺〉、自白書《餓鄉紀程》與自新
三、政治舞臺的文學首演:遺/情書〈中國之「多餘的人」〉與自剖
四、結語:中、俄文藝遺產的綜合體與矛盾源
第七章 自我的戲碼:瞿秋白之〈多餘的話〉
一、政治後臺的演變:「驚恐者」與崛起的史達林主義
二、拆臺:大小諸葛、多餘的人與「系主任」
三、下臺與擂臺:〈多餘的話〉的密碼與綜合文體
四、結語:蓋棺不落幕
第四部 大寫的人
第八章 吸收俄羅斯:論曹禺的《雷雨》與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大雷雨》在中國
一、偉大的劇作天才?
二、同名類義
三、同中求異、殊歸同途:誰的創意?
四、結語:同歸於盡,抑或時代的考驗?
第九章 展演階級?論《底層》的跨階級、跨領域與跨文化實踐
一、「階級意識」如何被言說、展演、代言到構築?
二、階級問題與《底層》的文本生成
三、《底層》的寫作目的與跨領域思考
四、傳播無產階級意識?《底層》在日本與法國的跨文化實踐
五、搭建黑暗背景與革命舞臺:高爾基和《底層》的中國化
六、結語
第十章 從《底層》到《日出》:多餘的知識分子與大寫的勞動階級
一、掛著「日出」賣「黑夜」?從黑暗王國到日出東方
二、版本與階級意識的問題:情之認同與人物形象的演變
三、再現勞動階級?論《伏爾加船夫曲》、《小海號》與《軸歌》的聲音形式問題
四、結語:從「多餘的人」到「大寫的人」
第十一章 結論:「人」與中國現代作家的改造
後記
引用書目
索引
圖表目次
第一章 導論
一、「五四」百年:意識形態與體系研究
二、「以俄為師」:文藝與政治共謀
三、狂人:魯迅創作的瘋狂與馴化
四、多餘的人:瞿秋白的自我編碼、符碼與戲碼
五、「大寫的人」:曹禺、奧斯特羅夫斯基與高爾基的戲劇展演
六、跨文化例證與跨領域的研究理論和方法
第一部 以俄為師
第二章 俄蘇翻譯、中國故事與黨國怪獸
一、「故事」及其無與倫比的影響
二、五四運動、「英特納雄耐爾」與被錨定的現代性
三、再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從史達林主義到毛澤東主義
四、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期間反蘇聯修正主義的文藝浪潮
五、1980年後俄蘇文學的翻譯與文藝迴響
六、結語:回到「故事」及其敘述的影響
第二部 狂人
第三章 瘋狂與黑暗的魅惑:魯迅與果戈理的狂人蠡探
一、魯迅與果戈理的文學關係
二、「瘋狂」、「黑暗意識」與「非理性」的連結
三、鬼、神、人的遠航想像與黑暗世界的形成
四、結語
第四章 瘋狂、戰爭與現代性批判:魯迅與日俄作家的狂人系譜
一、戰爭、現代性與瘋狂
二、從清日到日俄戰爭:「黑暗意識」與現代性的批判
三、進擊的狂人:世界大戰前後瘋狂的世界文學光譜
四、結語
第三部 多餘的人
第五章 自我的編碼:「多餘的人」之發端、形成及其嬗變
一、俄羅斯「多餘的人」之發端、定義與演變
二、「編碼」:從「多餘的人」到「空人」
三、變體:「零餘者」的編碼
四、變異:「浪子」、「窺淫者」與「孤臣孽子」的問題
五、變形:讀書人的西化與孤獨者的馴化
六、結語
第六章 自我的符碼:論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
一、幕前幕後
二、登臺前的文學預演:遺/戰書〈自殺〉、自白書《餓鄉紀程》與自新
三、政治舞臺的文學首演:遺/情書〈中國之「多餘的人」〉與自剖
四、結語:中、俄文藝遺產的綜合體與矛盾源
第七章 自我的戲碼:瞿秋白之〈多餘的話〉
一、政治後臺的演變:「驚恐者」與崛起的史達林主義
二、拆臺:大小諸葛、多餘的人與「系主任」
三、下臺與擂臺:〈多餘的話〉的密碼與綜合文體
四、結語:蓋棺不落幕
第四部 大寫的人
第八章 吸收俄羅斯:論曹禺的《雷雨》與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大雷雨》在中國
一、偉大的劇作天才?
二、同名類義
三、同中求異、殊歸同途:誰的創意?
四、結語:同歸於盡,抑或時代的考驗?
第九章 展演階級?論《底層》的跨階級、跨領域與跨文化實踐
一、「階級意識」如何被言說、展演、代言到構築?
二、階級問題與《底層》的文本生成
三、《底層》的寫作目的與跨領域思考
四、傳播無產階級意識?《底層》在日本與法國的跨文化實踐
五、搭建黑暗背景與革命舞臺:高爾基和《底層》的中國化
六、結語
第十章 從《底層》到《日出》:多餘的知識分子與大寫的勞動階級
一、掛著「日出」賣「黑夜」?從黑暗王國到日出東方
二、版本與階級意識的問題:情之認同與人物形象的演變
三、再現勞動階級?論《伏爾加船夫曲》、《小海號》與《軸歌》的聲音形式問題
四、結語:從「多餘的人」到「大寫的人」
第十一章 結論:「人」與中國現代作家的改造
後記
引用書目
索引
序
序言
這是一本專為華語讀者寫的書。
寫此序的當下,我憶起二十餘年前那些將近零下二十度的彼得堡深夜,孤獨地坐在刺骨透風的蘇聯式公寓敲打著俄文鍵盤,一心為自己的學位奮鬥。所謂「寒窗」無人問的心境,我早在青年時期就已深切「體」會。後來因緣際會,我輾轉進入了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一間或許能貼切地體現在英語共榮圈(commonwealth)裡,所謂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最高學術殿堂。曾以為,那解體後破敗的俄羅斯大地上乏人問津的共產主義寒窗,在我人生苦痛的閱歷中難以被超越。豈知,走在三一學院的王謝堂前,反映照出自身對自己與他人的文化,以及這廣闊世界竟是如此無知得寒愴,才體認到這是個人與集體社會最悲哀的時刻。於是,為了擺脫當時自己知識和見識的貧乏,奮力敲打著英文鍵盤的同時,我立下志願:若有朝一日能活著回到故鄉,我的專書要為華語讀者而寫,希望我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單一政治意識形態的箝制,努力擺脫威權或極權下人民對國家文藝與歷史真相的無知窘境。我寫書,不願單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語言天分和學術能力。
回臺十餘年,我始終沒忘記那顆天真的初心。然而,書寫時我常常感到相當慚愧:原來把中文寫好其實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有時候甚至感覺比寫英文或俄文還難!回國前的我也始料未及,比起在國外學術體制下生存,中文學術界往往需要我們拿出更多「自我的證明」。於是,這本書就在內外多種力量拉扯、交織的環境中跌跌撞撞,在無限迴圈的中文評審意見裡浮浮沉沉。成書前,此書內容曾經過多篇期刊論文與多位評審委員的審查,也是在英美或斯拉夫語系學術圈裡罕見的狀況。歷經十餘年,此書終於要付梓。正敲打著注音符號鍵盤,撰寫此序的我,腦海中閃現幾個畫面――彼得堡黑夜的蒼涼雪白,三一學院後門那排高聳入雲的大樹在晨暮中透露出來的森嚴魅惑,最後卻落在亞熱帶小島上美食佳釀溫暖的炊煙蒸氣中。酷暑中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深感惶恐與心驚。這本書實在有太多未竟之處,全歸咎於我個人憊懶又不夠努力。然而我深信,此書的議題絕對是當代華語讀者,尤其是與我同住在這座亞熱帶島嶼,被溫暖舒適包圍的居民最不容忽視,也無法逃避的問題。我自是希望,至少此書猶如拋下一塊磚,在居安思危的日常生活中泛起漣漪,能招引更多美玉,而不是浸泡在酒池肉林裡消聲匿跡。
此書得以完成,必須歸功於余英時(1930-2021)先生。非常感謝他在我回臺的學術生涯中最困難的時刻,慷慨地捐獻了一部分的唐獎獎金給這本書,讓我的研究此後更為順利。儘管我從未有幸得見他老人家,但他的研究中散發出來的人文精神,常與我心同在。也謝謝科技部/國科會繼之而來對此書的獎助。
我何其有幸,能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如此優渥又相對和諧的環境底下工作。我十分感謝文哲所幾位亦師亦友的同事們長期的幫助,讓我的研究得以持之以恆。這一路走來,如果沒有曉真於公於私的提點和提攜,瓊云的友誼陪伴與砥礪,在無涯的學海中,我是孤獨又容易迷失自我的。而瑋芬和冠閔兄在我身心最脆弱,差點就要「誤入」比較哲學組時,能指點迷津並伸手援助,讓我重回比較文學「正軌」。我特別感謝貞德老師,她真乃聖女,是我在學術批判能力和為人處世上的學習楷模。學術生涯當然不可能一帆風順,所以每當我心困頓,學海生波,感到天地昏暗時,貞德老師就是我的一座明燈。沒有這些同事的幫忙,這本書要問世,只怕遙遙無期。最後,因為中研院的獎助,2010年我得以至哈佛大學進修一年。期間,我旁聽了王德威院士開設的中國現當代戲劇課程,開啟了我另一個學術視野。沒有王老師的指點和幫助,此書第四部「大寫的人」就無法完成。
過去的五年中,我活著的每一天都不免要感謝我在天上的朋友――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所前所長李柏靜教授。因為她的驟然離世,讓在喪禮上哭得悽然的我敲響了心中的警鐘,才明白肺腺癌像是一種文明症候與國民病一樣,如此容易入侵我們的日常生活。柏靜的離世提醒我去做低輻射胸腔電腦斷層掃描(LDCT),正因如此,我很幸運,在癌細胞尚未擴散前手術切除,得到根治。在此,我要感謝我的主治醫師臺大醫院陳晉興教授,還有高雄醫學大學的鐘育志校長,多年來在醫療方面提供協助,讓我不至於英年早逝。這幾位救命恩人讓我在寫此書時,常心存感激。若讀者讀到我的這些親身經驗,或許不妨也在每年的健康檢查中加入這個項目,及早發現、及早治療,也有較高機率能及早康復。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當然要感謝我的母親蘇美玉女士,以及弟弟陳俊安博士。沒有家人的奔走照顧、情感支持和醫療知識,我的身體也無法復原得如此迅速。另外,還要感謝摯(損?)友至柔、盈盈、卉、玲珍和仲如,就在我努力寫書、做研究和擺脫重大傷病時,不停地找我出去吃喝玩樂,讓我笑口常開。沒有他們,這本書早在五年前就能完成,但很可能會是我的第一本,也是最後一本的專書。
謹將此書獻給臺灣。
這是一本專為華語讀者寫的書。
寫此序的當下,我憶起二十餘年前那些將近零下二十度的彼得堡深夜,孤獨地坐在刺骨透風的蘇聯式公寓敲打著俄文鍵盤,一心為自己的學位奮鬥。所謂「寒窗」無人問的心境,我早在青年時期就已深切「體」會。後來因緣際會,我輾轉進入了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一間或許能貼切地體現在英語共榮圈(commonwealth)裡,所謂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最高學術殿堂。曾以為,那解體後破敗的俄羅斯大地上乏人問津的共產主義寒窗,在我人生苦痛的閱歷中難以被超越。豈知,走在三一學院的王謝堂前,反映照出自身對自己與他人的文化,以及這廣闊世界竟是如此無知得寒愴,才體認到這是個人與集體社會最悲哀的時刻。於是,為了擺脫當時自己知識和見識的貧乏,奮力敲打著英文鍵盤的同時,我立下志願:若有朝一日能活著回到故鄉,我的專書要為華語讀者而寫,希望我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單一政治意識形態的箝制,努力擺脫威權或極權下人民對國家文藝與歷史真相的無知窘境。我寫書,不願單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語言天分和學術能力。
回臺十餘年,我始終沒忘記那顆天真的初心。然而,書寫時我常常感到相當慚愧:原來把中文寫好其實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有時候甚至感覺比寫英文或俄文還難!回國前的我也始料未及,比起在國外學術體制下生存,中文學術界往往需要我們拿出更多「自我的證明」。於是,這本書就在內外多種力量拉扯、交織的環境中跌跌撞撞,在無限迴圈的中文評審意見裡浮浮沉沉。成書前,此書內容曾經過多篇期刊論文與多位評審委員的審查,也是在英美或斯拉夫語系學術圈裡罕見的狀況。歷經十餘年,此書終於要付梓。正敲打著注音符號鍵盤,撰寫此序的我,腦海中閃現幾個畫面――彼得堡黑夜的蒼涼雪白,三一學院後門那排高聳入雲的大樹在晨暮中透露出來的森嚴魅惑,最後卻落在亞熱帶小島上美食佳釀溫暖的炊煙蒸氣中。酷暑中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深感惶恐與心驚。這本書實在有太多未竟之處,全歸咎於我個人憊懶又不夠努力。然而我深信,此書的議題絕對是當代華語讀者,尤其是與我同住在這座亞熱帶島嶼,被溫暖舒適包圍的居民最不容忽視,也無法逃避的問題。我自是希望,至少此書猶如拋下一塊磚,在居安思危的日常生活中泛起漣漪,能招引更多美玉,而不是浸泡在酒池肉林裡消聲匿跡。
此書得以完成,必須歸功於余英時(1930-2021)先生。非常感謝他在我回臺的學術生涯中最困難的時刻,慷慨地捐獻了一部分的唐獎獎金給這本書,讓我的研究此後更為順利。儘管我從未有幸得見他老人家,但他的研究中散發出來的人文精神,常與我心同在。也謝謝科技部/國科會繼之而來對此書的獎助。
我何其有幸,能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如此優渥又相對和諧的環境底下工作。我十分感謝文哲所幾位亦師亦友的同事們長期的幫助,讓我的研究得以持之以恆。這一路走來,如果沒有曉真於公於私的提點和提攜,瓊云的友誼陪伴與砥礪,在無涯的學海中,我是孤獨又容易迷失自我的。而瑋芬和冠閔兄在我身心最脆弱,差點就要「誤入」比較哲學組時,能指點迷津並伸手援助,讓我重回比較文學「正軌」。我特別感謝貞德老師,她真乃聖女,是我在學術批判能力和為人處世上的學習楷模。學術生涯當然不可能一帆風順,所以每當我心困頓,學海生波,感到天地昏暗時,貞德老師就是我的一座明燈。沒有這些同事的幫忙,這本書要問世,只怕遙遙無期。最後,因為中研院的獎助,2010年我得以至哈佛大學進修一年。期間,我旁聽了王德威院士開設的中國現當代戲劇課程,開啟了我另一個學術視野。沒有王老師的指點和幫助,此書第四部「大寫的人」就無法完成。
過去的五年中,我活著的每一天都不免要感謝我在天上的朋友――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所前所長李柏靜教授。因為她的驟然離世,讓在喪禮上哭得悽然的我敲響了心中的警鐘,才明白肺腺癌像是一種文明症候與國民病一樣,如此容易入侵我們的日常生活。柏靜的離世提醒我去做低輻射胸腔電腦斷層掃描(LDCT),正因如此,我很幸運,在癌細胞尚未擴散前手術切除,得到根治。在此,我要感謝我的主治醫師臺大醫院陳晉興教授,還有高雄醫學大學的鐘育志校長,多年來在醫療方面提供協助,讓我不至於英年早逝。這幾位救命恩人讓我在寫此書時,常心存感激。若讀者讀到我的這些親身經驗,或許不妨也在每年的健康檢查中加入這個項目,及早發現、及早治療,也有較高機率能及早康復。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當然要感謝我的母親蘇美玉女士,以及弟弟陳俊安博士。沒有家人的奔走照顧、情感支持和醫療知識,我的身體也無法復原得如此迅速。另外,還要感謝摯(損?)友至柔、盈盈、卉、玲珍和仲如,就在我努力寫書、做研究和擺脫重大傷病時,不停地找我出去吃喝玩樂,讓我笑口常開。沒有他們,這本書早在五年前就能完成,但很可能會是我的第一本,也是最後一本的專書。
謹將此書獻給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