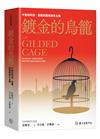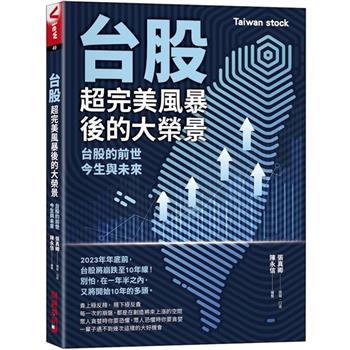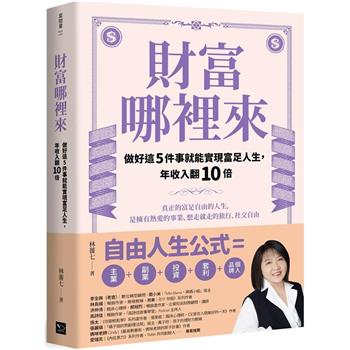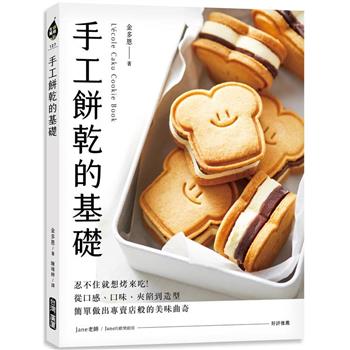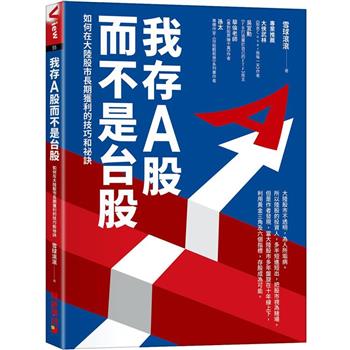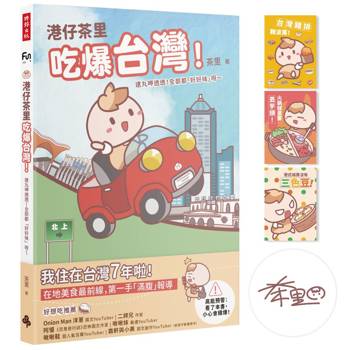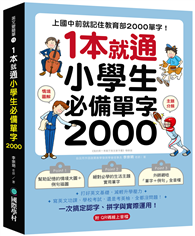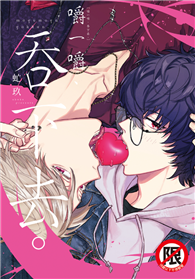從農民工、平台騎手到科技精英,窺見低端與高端的希望、幻滅和掙扎。
中國又是如何大展律法及體制的籠,淘汰過時的舊鳥,監管擴張的新鳥?
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逐漸從勞動密集、出口導向的製造業,轉向以數位科技為中心的社會發展進程。有些人將中國的後改革時期與美國的鍍金時代來相提並論;本書則認為前者更像是一只鍍金的鳥籠,中國政府與科技資本正使得社會不平等逐日加劇,並製造新形式的社會排斥。在這些矛盾之中,中國的鳥籠經濟演變為一種高度控制的體系,部分群體被排除在成長與繁榮的機會之外,沒有人擁有真正的自由和安全感。
作者描繪這種科技發展體制的輪廓及其產生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並透過針對低端與高端人口,以及從傳統製造業、外送平台到科技公司之間的深入訪談及親身觀察,講述那些因中國迅速崛起成為經濟和科技主導地位而改變生活的人及其背後的故事。
作者簡介:
雷雅雯
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密西根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亦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威瑟海德國際事務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成員。曾任哈佛學會(Society of Fellows)青年研究員。研究聚焦於中國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深入探討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著有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等書。研究成果發表於頂尖社會學期刊,並多次榮獲美國社會學協會、法律與社會學會及《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的多項獎項,彰顯其在社會學和中國研究領域的卓越貢獻。
譯者簡介:
李宗義(第一至五章)
政大英語系、東亞所畢業,清大社會所博士,主要研究興趣為災難治理。
許雅淑(第六至十章)
臺大圖資系畢業,清大社會所碩士、博士,目前關注女性主義、父權體制與男性困境、母職貨幣化等議題。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導論(摘錄)
1998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展開前瞻性的訪華之旅。此行距他推動美國國會通過「中美貿易協定」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僅兩年時間。柯林頓竭盡心力強化美中關係,試圖幫助美國公司在中國銷售及分銷由美國工人製造的產品,「而無須被迫把生產遷到中國、透過中國政府銷售或把有價值的技術移轉」。此外,他也希望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絕對要齊頭並進」。
柯林頓1998年的訪華之旅受到美國內部鋪天蓋地的批評,因為這次訪問終結了美國總統在中國政府鎮壓六四天安門後,長達九年不訪華的紀錄。不過,柯林頓為中國的未來喝采,並想利用此次訪問開創未來經濟交往的條件。1998年6月30日,柯林頓在希拉蕊的陪同下,召集幾位「重要的變革者」在上海圖書館舉行了主題為「構築21世紀中國」(Shaping China for the 21st Century)的圓桌座談。這些變革者包括法學教授、消費者權益倡導者、小說創作者、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主教,以及一家網路公司的執行長。
在圓桌會議上,科技成為柯林頓和座談參與者共同感興趣的突出話題。有位與會者認為中國需要科技來支撐經濟的永續發展,並問到中、美在這個領域的合作機會。柯林頓指出,兩國在科技領域的合作夥伴關係不斷成長,美國也竭力促進技術轉移並處理相關的國家安全問題。因為此次訪問恰逢美國網路熱潮,他對於網際網路在中國發展和傳播尤感興奮。當與會的網路企業家問到中美企業之間的交流機會,柯林頓說到由於網路產業是美國經濟成長最快速的領域之一,中美企業在網路部門會有豐富的交流機會。談及中國地方政府在擴大教育管道方面所面臨的困難,柯林頓分享他對中國未來的願景:
我認為我們將會在中國看到──我相信技術革命將會帶來──你們經濟成長可以跨越舊歐洲或許還有美國一整個世代的經濟經驗,你們基本上同時創造一個工業化和後工業化社會。因此,比起美國,你們必須讓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
基本上,柯林頓預言中國的工業與後工業的同時發展是由於技術變革與隨之而來的中國經濟飛躍。
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讀到柯林頓總統在上海提到後工業社會的新聞充滿驚喜。自1960年代起,貝爾就如先知般地提出「後工業社會」的概念,作為一種「推測性建構」(speculative construct),在此基礎上「測量幾十年的社會學現實……確定影響社會變革的作用因素」。貝爾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世界的未來都深感興趣,發展後工業社會這個概念,作為引導研究和比較研究的框架。1976年,他將中國歸為前工業化的集體主義社會。1998年,看到柯林頓對中國後工業化發展的評論後,貝爾致電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詢問柯林頓的講稿是由誰撰寫。當電話的另一頭告知總統的評論屬即興發表,貝爾很高興看到自己的觀點傳播得如此之廣,影響力如此之大。
在1973年出版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書中,貝爾列出後工業社會的特徵。他預測後工業社會將從製造經濟轉向服務型經濟;專業技術階級崛起;科技重新成為創新、經濟增長和政策制定的來源;國家規劃與控制技術增長;在決策過程中,智慧技術或演算法將取代直覺判斷。6因為貝爾比很多科學家更早聚焦於經濟、社會和科技之間的關係,他的著作大大影響了資訊、知識和網絡社會的學術研究。
貝爾預言後工業社會將是二十一世紀的主要特徵。重要的是,他並不認為一種社會將完全取代前一種社會:「後工業社會……不會取代工業社會,正如工業社會並未消除經濟中的農業部門一樣。新的發展有如疊層石(palimpsests),覆蓋在之前的地層之上,抹去了一些特徵,同時加深整個社會的紋理。」
雖然學者和評論者在引用貝爾的著作時,往往偏好以服務業來定義後工業社會,但貝爾明確指出,後工業社會的新穎和核心特徵是科學、技術和經濟之間的相互生成(mutually generative relationship),以及「基於科技的工具性權力的增強,包括對自然的掌控力量,甚至對人類的掌控力量」。貝爾認為工業社會的「設計」是「對抗人造自然(fabricated nature)的競賽」,集中在人類與機器的關係,並利用能源將自然環境轉化為技術環境;相較之下,後工業社會的「設計」則是「人與人之間的賽局」,在這場賽局中,智慧技術建立在資訊、資料、計算、演算法和編碼之上,與機器技術一同崛起。隨著智慧技術的崛起,決策者會更加面向未來,注重預測和規劃,而不是臨時的(ad hoc)調適和實驗。貝爾預測智慧技術將在後工業社會中扮演要角,並與通訊系統共同構建和促進一種嶄新且以數位為媒介的全球經濟。儘管貝爾的研究現在基本上已遭到美國的社會學界遺忘,並存在一些問題和局限性,但我認為他在1960至1970年代間就已預見在後工業社會中,基於科技的工具性權力的增強,有著深邃的眼光及洞見。
基本上,柯林頓和貝爾預言的未來已在中國實現。當然,柯林頓關於中國未來的一些說法都已經證實有誤。而且,他利用中國重振美國資本主義的戰略給美國埋下後患。但是,柯林頓認為中國將同時實現工業發展和後工業發展顯示出他的遠見,儘管這兩種發展形式的實際速度有別。事實上,柯林頓的預測與發展研究學者提出的「壓縮發展」(compressed development)概念不謀而合。這個觀點認為,後發展國家能夠透過學習和借鑑先發國家的經驗,並獲得先發國家的投資與授權,從而實現比先發國家更快速的經濟增長。此外,當今許多快速發展的國家同時經歷工業化和去工業化。發展研究學者進一步主張,由於發展的地緣政治、制度、技術與意識形態背景會隨時間改變,發展出現在哪個歷史階段相當重要。據這些學者的觀點,他們所謂的「壓縮發展時期」始於1990年前後,當時資訊和通訊技術(ICT)興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加速。他們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當成極端的個案,說明「壓縮發展時期」的壓縮發展還有跨越歷史階段的「趕超」。
如同日本、南韓和臺灣等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中國的國家角色在引導經濟發展上非常關鍵。然而,南韓和臺灣在經濟學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所說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即石油、汽車和大規模生產時代)時期開始發展,中國的壓縮發展則是在第五次技術革命(即資訊和電信時代),始於全球化程度更高的時代。中國從早期的開發者(包括但不限於東亞鄰國)獲得很大的好處,也從加速資本、技術、商品和服務跨國流動的國際機構,特別是多邊貿易協定獲益。儘管經歷1989年的政治動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承諾把經濟改革推行到底之後,外國直接投資(FDI)迅速飆升,推動勞力密集與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快速成長。2001年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境外的新聞媒體把中國描繪成一座即將形成的「世界工廠」。從二十一世紀剛開始到2010年代初,中國第二產業的就業,包括製造業和建築業,穩步上升,並在2012年達到頂峰,但2012年後趨勢逆轉。
1980年代也見證中國資訊技術(IT)相關產業的興起。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在北京中關村創辦IT公司,國務院於1998年批准在中關村設立北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這一帶立即成為中國創新重鎮,許多科技公司的總部也紛紛設立於此。事實證明,柯林頓對中國網際網路行業的重要性和發展前景的判斷正確。1998年柯林頓訪華時,正是新浪、騰訊、網易、京東、百度、阿里巴巴等眾多網際網路公司成立的風口。2008年金融危機後標誌一個新的時代。由於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受到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中國政府更加努力,試著減少對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等製造業的依賴,轉往以科技導向的社會經濟發展(S&T-oriente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以下稱「科技驅動型發展」),在這種發展模式中,國內消費與國際貿易一起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其中一部分的努力是中國政府刻意且成功將網際網路行業培育成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2008年後,中國在美國的網路公司迎來股票首次公開發行(IPO)的熱潮,還有在世界舞台上的快速崛起。截至2022年6月,全球前十大網路公司有五家來自中國,另外五家則是美國企業。2021年,中國數位經濟總值達6.72兆美元,占中國GDP的39.8%。中國與美國無疑是數位資本主義的兩個超級強權。儘管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對於中國現在是否算是後工業社會有不同意見,但他們都同意現在的中國已經具備貝爾後工業社會概念中的許多特徵。事實上,中國的科技驅動型發展也同時是後工業轉型的過程。
雖然中國是後發展國家,政治上也還是威權政體,但它已成為世界的領頭羊,中國的發展經驗如今已是一種振奮人心的模式。政治學者洪源遠(Yuen Yuen Ang)將中國的後改革時期與美國的鍍金時代作類比。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甚至進一步宣稱中國是「資本主義的未來」,並指出中國共產黨「很諷刺地已經被公認為是一個效率遠勝於自由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管理者」。他也認為,資本主義與西方秩序的未來將是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與威權主義政治與社會的混合,例如中國與新加坡。社會心理學家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書指出,自由民主國家的一些評論家和學者對於市場民主的動盪感到失望,現在冀望能效仿中國。另外,開發中國家的領導人也渴望中國由國家引導的經濟發展經驗。比方說2022年,南非洲六國執政黨資助、中國共產黨所支持的「姆瓦利姆.朱利葉斯.尼雷爾領導學院」(Mwalimu Julius Nyerere Leadership School)在坦桑尼亞(Tanzania)舉行開學典禮。六國執政黨的領袖參加典禮時,對於有機會向中國共產黨學習表示興奮──他們希望這將促進「非洲的發展和振興」。由於中國現今的全球影響力,了解中國的科技驅動型發展不僅本身具有重要意義,還具有深遠的影響。
第一章 導論(摘錄)
1998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展開前瞻性的訪華之旅。此行距他推動美國國會通過「中美貿易協定」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僅兩年時間。柯林頓竭盡心力強化美中關係,試圖幫助美國公司在中國銷售及分銷由美國工人製造的產品,「而無須被迫把生產遷到中國、透過中國政府銷售或把有價值的技術移轉」。此外,他也希望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絕對要齊頭並進」。
柯林頓1998年的訪華之旅受到美國內部鋪天蓋地的批評,因為這次訪問終結了美國總統在中國政府鎮壓六四天安門後,長達九年不訪華的紀錄。不過,柯...
作者序
中文版序(摘錄)
科技、社會、權力和政治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都是學者們關注的議題。早在1960至1970年代,隨著工業社會逐漸轉型為後工業社會,社會學者開始探討這種轉型對社會結構及不同群體的影響。1973年,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提出,後工業社會的「設計」將會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賽局」,這種賽局以資訊、數據、計算、演算法和程式設計等智慧技術為基礎,並與工業社會的機械技術共存。貝爾認為,在後工業社會中,科技作為一種工具對人類的控制力量將會增強,但他對科技仍持非常樂觀的態度,強調科技將促進社會進步,不同的社會群體都會從中受益,他堅信這種進步還將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貝爾在退休前曾在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我也在哈佛任教,藉此地利之便,曾經好奇地在學校圖書館的檔案室翻閱貝爾未發表的文件,試圖進一步了解他對科技的樂觀態度。在他的手記中,我看到他對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如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持的批評態度,因為貝爾不接受這些學者對科技的批判立場。然而,1990年代後期,貝爾在反思自己在1960至1970年代對未來的預測時,承認他忽略了在科技發展的進程中,會產生一群被遺忘和淘汰的人群。
對科技的反思也出現在近年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著作中。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提醒,雖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著科技公司看似免費的服務,這些服務卻建立在對我們各種數據的蒐集之上。科技公司利用這些數據發展許多可以預測及影響我們各種行為的模型,從網路購物到投票。當技術進步以數據監控為核心時,科技不再僅是提供便利的工具,而是成為削弱個人自由、隱私和自主性的機制。
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賽門.強森(Simon Johnson)在《權力與進步》(Power and Progress)中強調,科技進步往往鞏固了少數精英的權力和利益。歷史上,科技雖然推動了經濟增長,但其帶來的紅利分配並不平等,通常集中於少數掌控資源的群體手中。他們指出,不同社會的制度、對科技的認知以及集體行動的能力各不相同,而這些差異會影響科技所帶來的利益和挑戰在社會中的分配。確實,每個社會可能擁有不同的科技發展文化和制度。
《鍍金的鳥籠》正是在這些理論背景下展開,並以中國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的發展作為一個案例。我從2011年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觀察到在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這個以「世界工廠」著稱的國家快速轉向高科技發展,迅速成為數位經濟大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網路公司,只有美國的數位經濟和科技公司能與之相比。2013年以後,儘管中國的政治管控日益嚴格,公共領域逐漸縮小,但人們普遍認為經濟欣欣向榮,科技高速發展,中國毫無疑問地崛起成為科技強國。我在中國研究時,朋友及受訪者經常自豪地向我提起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高速鐵路、網購、行動支付、共享單車。這些科技確實讓生活變得極為便利,象徵著科技與經濟的快速發展。
然而,隨著研究的開展,我發現這個表面光鮮的「科技奇蹟」背後,還有一個複雜的故事。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工具理性逐漸成為支配發展的至高原則,這個故事牽涉到中國鳥籠經濟的轉型。鳥籠經濟是一個形象化的比喻,用來描述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所採取的經濟政策,旨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維持國家的經濟控制。鳥籠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中國應該釋放經濟活力,就像讓「鳥」在籠子裡自由飛翔一樣,但要確保這隻「鳥」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活動,避免飛出「籠子」而失控。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政府對「鳥」的種類並沒有太多區分,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然而,為了解決資源稀缺的問題,特別是沿海省份的土地稀缺問題,地方政府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提出「騰籠換鳥」的策略,積極推動淘汰落後過時的「舊鳥」,以便引入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的「新鳥」。
在鳥籠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國家依賴技術工具來解決傳統發展模式的局限,許多官員對科技抱有崇高的信仰,儘管他們可能不完全了解技術本身及其限制。他們認為,量化指標、數據科學、大數據、平台系統等各種技術可以幫助政府運用「看得見的手」來協調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從而實現資源配置的最佳化,遴選出優質的「新鳥」,並透過法律手段懲罰市場中落後的「舊鳥」。因此,政府極力透過技術手段來科學化引導和管理鳥籠經濟。
在我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基層地方官員、企業主、經理人和各類勞動者的生活和工作都圍繞這些技術和法律工具展開,試圖在貝爾所說的「人與人之間的賽局」中爭取最佳結果,甚至鑽這些技術規則的漏洞,導致許多數據和指標失真。然而,多數人對於這個「鳥籠」的工具設計缺乏控制,也難以提出改進建議。那些被體系評估為「舊鳥」而遭受懲罰的企業和勞動者,幾乎沒有任何救濟途徑。更令人不安的是,技術和法律工具的標準和規則可能隨時變動,難以預測。許多傳統產業的企業和工人在這個過程中被邊緣化和汙名化,被視為低價值的勞動者,不僅地位低於工廠引進的機器人(機器人甚至受到推崇!),他們的子女受教育的機會也受到影響。在科學化的鳥籠經濟中,這些被認為落後和過時的勞動者和企業,幾乎被視為不值得享有資源。
除了政府之外,大型網路科技公司也是科學化鳥籠經濟中「鳥籠」的建構者。從金融危機過後到2020年政府決定打壓這些公司之前,這些科技公司一直是政府眼中珍貴的「新鳥」。與其他「鳥」相比,政府給予它們高度的自由,允許它們自由發展。與政府類似,這些公司也是技術工具的愛好者。正如祖博夫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中所描述的美國科技公司,中國的大型網路科技公司也在建造自己的王國。我們可以想像它們在一個相對自由的「鳥籠」中打造數位經濟的「鳥籠」,利用大數據、演算法、雲端計算和契約條款等技術和法律工具來規範數位經濟中的消費者、勞動者和其他參與者。由於政府對它們的監管相對寬鬆,這些公司獲得了極大的權力,能夠在其構建的「鳥籠」王國中影響數以萬計的人,例如,那些被困在演算法中的外賣騎手,以及因996工時而過勞的網路精英從業人員。在我的訪談中,少數網路精英開始反思個人和家庭在這種「科技奇蹟」與國家快速發展中所付出的犧牲,並質疑這樣的犧牲是否值得。
但這些大型網路科技公司沒有預料到,有一天他們也會成為被政府嚴懲的「鳥」。雖然它們擁有技術、資源和權力,依然是國家的籠中鳥。在鳥籠經濟的轉型中,政府並未預見科技公司作為「新鳥」竟然在短時間內擁有足以威脅政府和國家的能力,因此政府開始建造更堅固的「鳥籠」,以避免失去對這些「新鳥」的控制。
總結來說,《鍍金的鳥籠》揭示了中國在科技驅動型發展光環下所掩蓋的矛盾:一方面是炫目的數位創新與經濟成長,另一方面則是在技術和法律工具構建的「鳥籠」中,我看到了表象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政府與資本的矛盾、政府對部分公民的不平等對待,以及科技資本與勞工之間的衝突。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認為,發展與人類福祉應以公共論證為基礎。然而,在中國的經濟轉型中,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為達到特定目標而選擇最有效方法的思維方式—不斷擴張,而哲學家兼社會學家哈伯瑪斯所提出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透過討論和相互理解來達成共識的理性思維,則在日益緊縮的政治環境和萎縮的公共領域中逐漸消失。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被工具理性支配,缺乏反思對技術崇拜的機會,也無法檢討技術及法律工具的負面影響。人本關懷被埋沒在冷漠的數據、指標、演算法以及不確定且難以救濟的法律制度之下。在這些矛盾之中,中國的鳥籠經濟逐漸演變為一種高度控制的體系,部分群體被排除在成長與繁榮的機會之外,而在這個「鳥籠」中,沒有人擁有真正的自由和安全感,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韋伯所描述的「鐵籠」(iron cage)。
《鍍金的鳥籠》雖然聚焦於中國,但類似的挑戰也在全球各地發生。隨著科技日益滲透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每個社會都需要反思其技術發展的方向,重新審視科技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如何在追求效率和增長的同時,確保人本關懷和社會正義不被忽視,是每個社會都應謹慎考量的問題。我們應該警惕工具理性是否在無意間成為社會發展的唯一指導原則,並確保技術進步真正造福廣大民眾,而非僅僅服務於少數權力集團的利益。本書希望能為理解這些全球性的議題有些許貢獻,引發更多人對科技發展與社會價值之間平衡的深思。
中文版序(摘錄)
科技、社會、權力和政治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都是學者們關注的議題。早在1960至1970年代,隨著工業社會逐漸轉型為後工業社會,社會學者開始探討這種轉型對社會結構及不同群體的影響。1973年,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提出,後工業社會的「設計」將會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賽局」,這種賽局以資訊、數據、計算、演算法和程式設計等智慧技術為基礎,並與工業社會的機械技術共存。貝爾認為,在後工業社會中,科技作為一種工具對人類的控制力量將會增強,但他對科技仍持非常樂觀的...
目錄
中文版序
致謝
圖表目次
第一章 導論
金玉其外
對科技發展體制的探究
鍍金的鳥籠
本書章節概述
方法論說明
第二章 從勞動力到土地和技術
勞動力驅動的發展
土地驅動的發展
科技發展主義
國家統治技術的科學化
結語
第三章 轉向科技驅動的發展模式
鳥籠經濟科學化
激化的爭議
鞏固科技發展體制
科技驅動發展下的工具性體系
臺灣和南韓轉向科技驅動型的發展
結語
第四章 過時的資本和勞動力
淘汰過時者
大力整頓
苦苦掙扎的企業
工人
結語
第五章 機器人化
中國的機器人之夢
電子製造領域的機器人化
地方科技發展型國家
製造商:機器人之夢的願景與現實
工人:進步、焦慮和冷漠
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爬上社會流動的階梯
雖毒卻抗拒不了的新鳥
結語
第六章 大型科技企業的崛起
支持和寬容的政府
政府與科技巨頭的合作
跨越邊界的新鳥
新鳥的力量
與南韓、臺灣、美國的比較
結語
第七章 從工廠到平台
成長中的送餐平台
平台騎手
控制和管理的平台架構
從夢想到不滿和幻滅
矛盾的感受
結語
第八章 編碼精英
軟體工程師及其社會再生產的困難
勞動力市場
勞動控制和管理,以及加班文化
階級出身與勞資關係
政府、國家與發展
「不是我們的錯」
結語
第九章 重塑科技國家資本主義
觸動包容審慎的紅線
監管整頓行動
政府重塑鳥籠
培育下一代新鳥
結語
第十章 結論
「鍍金的鳥籠」中的秩序與矛盾
科技發展體制的比較
再探相關文獻
鍍金鳥籠的未來
方法論附錄
引用書目
索引
中文版序
致謝
圖表目次
第一章 導論
金玉其外
對科技發展體制的探究
鍍金的鳥籠
本書章節概述
方法論說明
第二章 從勞動力到土地和技術
勞動力驅動的發展
土地驅動的發展
科技發展主義
國家統治技術的科學化
結語
第三章 轉向科技驅動的發展模式
鳥籠經濟科學化
激化的爭議
鞏固科技發展體制
科技驅動發展下的工具性體系
臺灣和南韓轉向科技驅動型的發展
結語
第四章 過時的資本和勞動力
淘汰過時者
大力整頓
苦苦掙扎的企業
工人
結語
第五章 機器人化
中國的機器人之夢
電子製造領域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