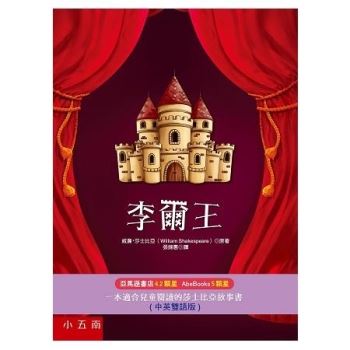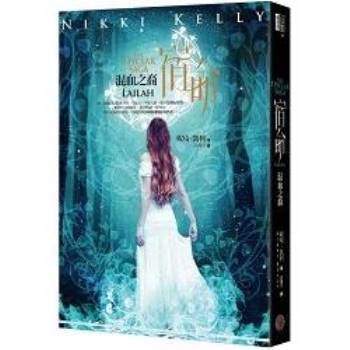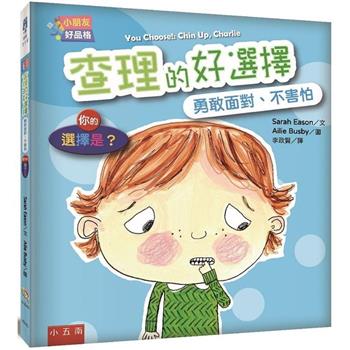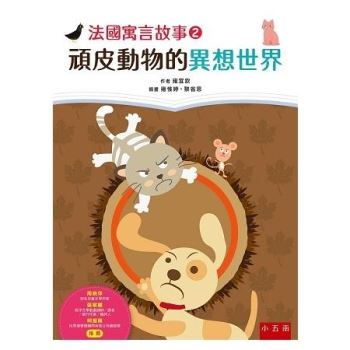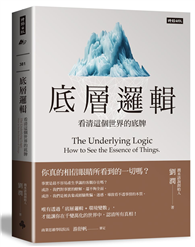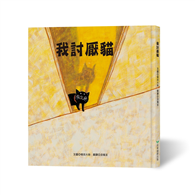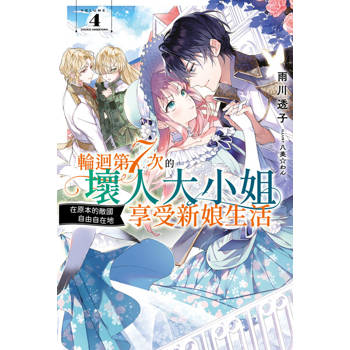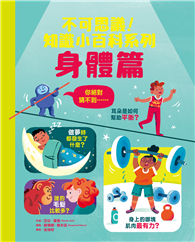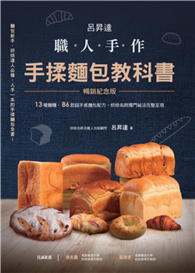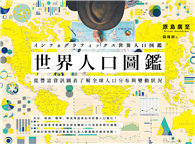前言 關於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摘錄)
這是一本討論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的宗教改革的書,書名訂為《說服與鎮服: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副標題使用「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因為本書要討論的是歐洲宗教改革中的英格蘭,尤其聚焦在亨利八世國王階段;採用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來表述,有傳達此改革為國王意志之意涵。本書想要回答一個核心的問題:亨利八世國王如何達成他的宗教改革?這個問題的答案線索便在本書的主標題裡:說服與鎮服。
歐洲宗教改革與英格蘭
1517年,日耳曼的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薩克森邦(Saxony)的威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發表他的〈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標誌了歐洲宗教改革的開始。以路德為代表,從文藝復興的基督教人文主義以降對羅馬教廷累積的質疑,自此浮上檯面。宗教改革的風暴襲捲各國,從原本的宗教與學術領域,蔓延至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甚至國際局勢的層面。這個風暴一直要到17世紀中旬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1618-1648)才暫告歇息。但西歐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以及宗教陣營間檯面下的競合餘震不斷,至今仍影響著世界。
關於歐洲宗教改革與英格蘭,有兩個主要的討論脈絡:一是「宗教改革在英格蘭」(Reformation in England),一是「英格蘭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這兩個看起來頗為相近的表述,其實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視角。前者將宗教改革視為一個主旋律,強調這個主旋律在不同地區的變奏。所以,有「宗教改革在日耳曼」、「宗教改革在法國」、「宗教改革在波蘭」,也有「宗教改革在英格蘭」。各國因著特有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結構,讓宗教改革在不同地區發展出不同的樣態。依此脈絡,則「宗教改革在英格蘭」要討論的便是這個運動主旋律到了英格蘭後呈現出怎樣的形貌?又,為什麼是這樣的形貌?這個「宗教改革在英格蘭」的研究除了幫助我們瞭解改宗運動在英格蘭的發展,也協助我們拼貼出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全貌。
對比之下,「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取徑比較強調英格蘭的主體性。亦即,宗教改革的風潮吹進了英格蘭王國,這個外來的成分如何揉雜進入英格蘭自己的發展,影響著王國的歷史路徑。這個取徑的背景前提是:宗教改革風潮影響了英格蘭,而英格蘭經歷了「自己的」宗教改革運動。
本書採取的是第二種視角:作者最終想要回復的不是歐洲宗教改革的形貌,而是英格蘭王國的歷史軌跡。本書想要探索的是:經歷了宗教改革這個關鍵歷史事件之後的英格蘭王國走上了一條怎樣不同的道路?君主專制?議會政治?新教信仰?上述這些關鍵的歷史轉折元素,未來將匯流在一起,形塑接下來的聯合王國,以及一度傲視世界的英帝國(British Empire)。
關於英格蘭宗教改革
同樣是宗教改革,英格蘭與歐陸國家有一個本質上的差異,那就是,它是一個「由上而下」(reformation from above),由國王發動的改宗運動。也就是說,它不是因民間對天主教會不滿所釀成的社會運動。而這一切都要從「國王的婚姻大事」(King’s Great Matter)說起。亨利八世國王的第一任妻子是西班牙公主凱撒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但凱撒琳原本的婚配對象並不是亨利。亨利八世的父親亨利.都鐸(Henry Tudor, r. 1485-1509)在三十年的薔薇內戰(the Wars of the Roses)(1455-1485)中驚險擊敗理查三世(Richard III, r. 1483-1485),入主王庭,創建都鐸王朝(House of Tudor)(1485-1603),成為歷史上所稱的亨利七世國王(Henry VII, r. 1485-1509)。亨利七世雖然贏得政權,但統治基礎薄弱:他的父系來自威爾斯,出身仕紳階級,完全沒有英格蘭王室的血統(甚至連貴族都談不上)。亨利.都鐸與英格蘭王室牽扯上關係是透過他的母親,蒲福夫人(Lady Margaret Beaufort, 1443-1509)。蒲福一族的血統最早可追溯至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 r. 1327-1377)的兒子,也就是亨利四世(Henry IV, r. 1399-1413)的父親,岡特的約翰(John of Gaunt, 1340-1399)。不過,岡特的約翰雖然其父親與兒子都擔任過國王,自己卻從不曾登上王位。此外,蒲福一支本是庶出:約翰一生娶過三任妻子,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就是蒲福一支的母親,凱撒琳.斯溫福德(Katherine Swynford, c. 1350-1403),在與約翰正式結婚之前一直是他的情婦。斯溫福德與約翰的三個兒子都是在兩人尚未取得婚姻關係之前生下,是不受法律保障的私生子。而他們的長子約翰(John Beaufort, c. 1373-1410)就是蒲福夫人的祖父。也就是說,都鐸家族的王室血統是透過母系、通過庶出的蒲福一系取得。母系加上庶出,讓都鐸家族的繼承正統性極為薄弱。
尤有甚者,都鐸王朝建立在三十年的內戰之後。長期的戰爭讓英格蘭充斥暴戾之氣,王室更迭頻仍,以武力競逐大位成為常態。如何讓英格蘭人民體認到都鐸王朝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不是另一階段逐鹿爭奪的起點?這是亨利七世嚴峻的挑戰。亨利七世為了宣示內戰結束,家族和解,以「紅薔薇」的身分迎娶了來自敵對陣營「白薔薇」家族的伊莉莎白(Elizabeth of York, 1466-1503),開啟「紅」「白」薔薇家族的結合共治。而為進一步鞏固根基羸弱的王朝,他積極為長子亞瑟(Arthur, Prince of Wales, 1486-1502)尋求強大的姻親奧援。當時歐陸最強大的國家是西班牙王國,亨利於是向西班牙提出了聯姻的請求。西班牙當時正面臨來自法國的挑戰,兩雄爭霸,英格蘭成為值得爭取的第三方。但,身為二級國家的英格蘭要「高攀」西班牙仍需付出一些誠意代價。一生謹慎的亨利七世因此答應了西班牙方面的要求,加入同盟,共同出兵法國。簡言之,凱撒琳是亨利七世費盡心思為長子亞瑟聘得的西班牙公主。凱撒琳在15歲時帶著豐厚的嫁妝來到英格蘭與亞瑟完婚,然而,王子跟公主的婚姻並沒有如童話故事般展開。婚後五個月,亞瑟就染上汗熱病(sweating sickness)急症去世。亨利七世費盡心思締結的聯姻同盟眼看就要瓦解,焦急的國王於是提出讓凱撒琳改配次子—新任王儲亨利—的建議。
「兄嫂改嫁小叔」在以婚姻為結盟手段的年代並非匪夷所思,然而《聖經》中有不少地方明文禁止近親通婚。舉例來說,〈利未記〉「有關淫亂的禁令」中有:「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體;這本是你弟兄的下體。」(18:16)。又譬如該篇在「處罰悖逆之人」的條例中寫道:「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汙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20:21)。因此,依照嚴格的教會法,迎娶兄弟的妻子是為禁忌:要達成亨利與凱撒琳的聯姻必須先克服一些困難。
最需要解決的是凱撒琳為亨利兄嫂的身分。英格蘭與凱撒琳方面主張,凱撒琳雖然曾與亞瑟舉行婚禮,但兩人不曾有過「夫妻之實」,不是真正的夫妻。而西班牙方面為求嚴謹,特別敦請教廷,由教皇儒略二世(Pope Julius II, 1503-1513)出面頒布赦令(dispensation),免除這項婚姻可能涉及的「罪」(sin)。最終,在雙方均有意願且兼顧法理人情的情況下,凱撒琳成為了亨利王子的未婚妻,續留英格蘭。
1509年4月亨利七世去世,同年6月11日亨利與凱撒琳完婚。兩個星期後,亨利被加冕成為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凱撒琳同時被冊封為王后。亨利八世與凱撒琳王后在婚姻初期相當恩愛,可謂「公主童話」的真人版:亨利英俊活躍、聰明優雅、才華洋溢。凱撒琳也不遑多讓,她端莊美麗、才德兼備,深獲英格蘭臣民的愛戴。然而,兩人的婚姻始終存在著缺憾,那就是結褵九年,凱撒琳雖然多次懷孕,卻只得一女瑪麗(Mary I, r. 1553-1558)存活。因此,當「繼承人」成為亨利八世心中的關鍵詞時,美麗的童話就開始變調了。
亨利與凱撒琳的關係在1520年代開始惡化:年過35歲的凱撒琳逐漸喪失對亨利的吸引力,而一直未得男嗣也讓國王感到焦慮。亨利曾經打算「向命運低頭」,接受自己只有女兒的現實。他設法為瑪麗尋找有力的夫家後臺,幫助她鞏固未來的執政之路。亨利覓婿的首選是和瑪麗有著表親關係的查理五世(Charles V, r. 1516-1556)。查理在1516年繼承西班牙王位,1519年進一步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君主。另外,查理轄下的尼德蘭(Netherlands)一直是英格蘭最重要的商業夥伴。查理事務繁多,不可能長居英格蘭,這可使英格蘭保有實質上的獨立。而瑪麗與查理倘能產下子嗣,那麼這位繼承人很可能成為基督教世界的實質統治者。凡此種種,都吸引著亨利八世。
亨利在1521年向查理提出了聯姻的要求。這項提議對查理有一定的吸引力:查理在打敗一同競逐的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 r. 1515-1547)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後,哈布斯堡家族的勢力就圍繞住法國,兩者間的矛盾益深。在法、西爭霸的格局中,英格蘭是值得查理爭取的對象。於是,在雙方都有意願的情況下,1516年出生的瑪麗公主,雖然只有5歲,被婚配給了當時已經21歲的查理五世國王。
然而,這項兼顧英、西兩方需求的協定在1525年時破局。已值盛年的查理五世改變心意,不願再等待年幼的瑪麗長大成人,他要求英格蘭立即履行婚約,否則就要改娶另一位表妹—葡萄牙公主伊莎貝拉(Isabella of Portugal, 1503-1539)。查理的要求顯然強人所難(在英格蘭方面解讀,這是解除婚約的藉口):瑪麗當時不足10歲,根本未達適婚年齡。婚姻協議最終破裂,查理五世另結姻緣。
查理的悔婚對亨利八世是個重大的打擊。他在1522年至1525年間為了支援查理,投入對法戰爭,耗費了大量的資源與人力。查理的反悔毋寧是種背叛,它讓亨利八世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或許是出於對西班牙方面的強烈不滿,亨利開始思考另立繼承人的可能。
性別是亨利八世的首要考量,取代瑪麗最具正當性的理由便是男性繼承人。1525年6月,亨利將他的私生子亨利.費茲洛依(Henry Fitzroy, 1519-1536)召至宮中,當著廷臣的面冊封他為里奇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這是極具政治意涵的動作,因為里奇蒙是亨利七世在成為國王之前的封號,對都鐸家族有著特別的意義。亨利將里奇蒙公爵的頭銜賜給費茲洛依便是承認他的身分,宣告他是都鐸家的繼承人。然而,私生兒子扶立為儲君,這在傳統的封建社會終究是過於大膽的嘗試,此議引起各方反對,最終胎死腹中。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說服與鎮服: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圖書 |
 |
說服與鎮服: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 作者:李若庸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5-01-2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40 |
中文書 |
$ 450 |
世界歷史 |
$ 450 |
社會人文 |
$ 450 |
旅遊 |
$ 475 |
大學出版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說服與鎮服: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
這是一本討論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的書。本書的副標題訂為「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因為作者要討論的是歐洲宗教改革中的英格蘭改宗,尤其聚焦在亨利八世時代。作者選擇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來表述意在傳達此改宗為國王意志之落實。
本書想要回答一個核心的問題:在缺乏資源且危機重重的亨利八世朝,國王是如何達成他的宗教改革?答案的線索便在本書的主標題裡──說服與鎮服。作者最終想要回復的不是歐洲宗教改革的形貌,而是英格蘭王國的歷史軌跡。本書想要探索的是:經歷了宗教改革這個關鍵歷史事件之後的英格蘭王國,走上一條怎樣不同的道路?議會政治?新教信仰?這些關鍵的歷史轉折元素未來將匯流集結,形塑接下來的聯合王國,以及一度獨擅世界的英帝國。
作者簡介:
李若庸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英國近古史、歐洲宗教改革、英帝國史。發表〈亨利八世的修院整頓〉、〈亨利八世的佈道管控與輿論偵防〉、〈1583年倫敦商人東方行〉、〈英帝國與傳教〉等十餘篇相關論文。
章節試閱
前言 關於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摘錄)
這是一本討論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的宗教改革的書,書名訂為《說服與鎮服: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副標題使用「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因為本書要討論的是歐洲宗教改革中的英格蘭,尤其聚焦在亨利八世國王階段;採用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來表述,有傳達此改革為國王意志之意涵。本書想要回答一個核心的問題:亨利八世國王如何達成他的宗教改革?這個問題的答案線索便在本書的主標題裡:說服與鎮服。
歐洲宗教改革與英格蘭
1517年,日耳曼的...
這是一本討論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的宗教改革的書,書名訂為《說服與鎮服: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副標題使用「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因為本書要討論的是歐洲宗教改革中的英格蘭,尤其聚焦在亨利八世國王階段;採用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宗教改革來表述,有傳達此改革為國王意志之意涵。本書想要回答一個核心的問題:亨利八世國王如何達成他的宗教改革?這個問題的答案線索便在本書的主標題裡:說服與鎮服。
歐洲宗教改革與英格蘭
1517年,日耳曼的...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序 臺灣世界史書寫的新境界
楊肅献(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一
熟悉英國史學的人都瞭解,都鐸時代一直是英國史研究的顯學。這個時期,英國正處於從「中世紀」國家轉型為「近代」國家的關鍵時刻,近代英國政治、宗教、社會、語言和文學各方面,都在此時奠定基本型態,形塑英格蘭文化的獨特面貌。由是之故,都鐸史研究長期受到英美史學界重視,發展為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
在都鐸史研究中,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是焦點中的焦點。英格蘭的宗教改革不只是個單純的宗教課題,也關涉英格蘭王權、議會政治、語文發展、國族認同諸問題,是英...
楊肅献(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一
熟悉英國史學的人都瞭解,都鐸時代一直是英國史研究的顯學。這個時期,英國正處於從「中世紀」國家轉型為「近代」國家的關鍵時刻,近代英國政治、宗教、社會、語言和文學各方面,都在此時奠定基本型態,形塑英格蘭文化的獨特面貌。由是之故,都鐸史研究長期受到英美史學界重視,發展為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
在都鐸史研究中,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是焦點中的焦點。英格蘭的宗教改革不只是個單純的宗教課題,也關涉英格蘭王權、議會政治、語文發展、國族認同諸問題,是英...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臺灣世界史書寫的新境界/楊肅献
自序
前言 關於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
第一章 宣傳戰開打:《真相的鏡子》
第一節 《真相的鏡子》
第二節 《義大利與法國最著名與傑出大學的決議》
第三節 雷金納德.波爾與帕度亞的英格蘭留學生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言論管制:肯特郡的聖女
第一節 「肯特郡聖女」的政治預言
第二節 「巴頓案」的人際網絡
第三節 「巴頓案」的後續調查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服從論述與王權宣傳
第一節 服從論述
第二節 王權的新詮釋
第三節 戲劇宣傳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佈道管...
自序
前言 關於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
第一章 宣傳戰開打:《真相的鏡子》
第一節 《真相的鏡子》
第二節 《義大利與法國最著名與傑出大學的決議》
第三節 雷金納德.波爾與帕度亞的英格蘭留學生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言論管制:肯特郡的聖女
第一節 「肯特郡聖女」的政治預言
第二節 「巴頓案」的人際網絡
第三節 「巴頓案」的後續調查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服從論述與王權宣傳
第一節 服從論述
第二節 王權的新詮釋
第三節 戲劇宣傳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佈道管...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