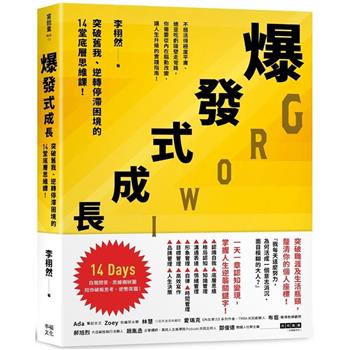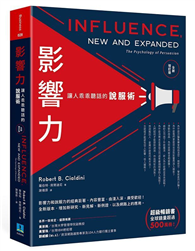再好的人不可能一輩子做的全是好事,而再壞的人,也不可能一輩子不做一件好事。藥也一樣。
許老靠在沙發裏,道:「前段時間,美國藥物管理局批准了用三氧化二砷治療某種癌症。而在我們的《藥典》中,這卻是明令禁止使用的大毒藥。我最近翻了翻醫書,發現其中有很多使用砒霜治病的醫案。聽說最早用砒霜注射液治療癌症的,還是我們國內的一些鄉村老中醫?」
曾毅點了點頭,三氧化二砷就是俗稱的砒霜了,毒性很強。以前確實有中醫用它來治療白血病和癌症,後來這位中醫被抓了起來,也就沒人再敢用了。反倒是美國的一些科研機構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而且取得了成果。
許老歎道:「不能因為一味藥有毒,就把它一棍子打死。美國人的實踐告訴我們,只要加強管理,毒藥也是可以變成救命良藥的。」
曾毅再次頷首,這世上沒有絕對的黑白,「天生其物,必有其用」,所以古代醫生才發明了各種各樣的藥品炮製方法,目的也就在於要讓藥物發揮其正面作用。可惜的是,像許老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
◎藥草知識:百合
百合味甘,性寒。歸心、肺經。功效養陰潤肺、清心安神。臨床用名有百合、蜜炙百合。《神農本草經》記載:「味甘,平。主治邪氣腹脹,心痛,利大、小便,補中益氣。」《名醫別錄》記載:「無毒。主除浮腫,臚脹,痞滿,寒熱,通身疼痛,及乳難喉痺腫,止涕淚。」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首席御醫Ⅱ之11:名醫較量的圖書 |
 |
首席御醫II之11名醫較量【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銀河九天 出版社: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1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256頁/15*21mcm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57 |
現代小說 |
$ 157 |
現代華文創作 |
$ 169 |
小說/文學 |
$ 179 |
文學作品 |
$ 179 |
科幻/奇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首席御醫Ⅱ之11:名醫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