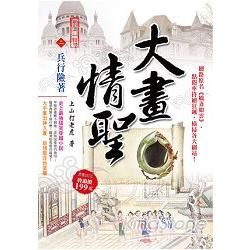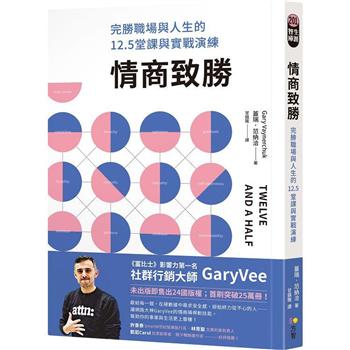趙樞的車駕比尋常的皇子要華麗不少,他的性子本就有幾分張揚,再者,在宮中不受寵幸,索性也就無所謂了,平時的用度都是最好的。
坐在車廂裏,趙樞一頭霧水,稀奇古怪地赴了宴,正主兒沒有見到,就連那沈傲也中途離了席,不知這背後到底在弄什麼玄虛。
趙樞不安地張開眼,撩開車窗道:「福安。」
隨身伺候的主事福安立即快步到趙樞的車窗前,一邊追著車子一邊道:「殿下有什麼吩咐?」
「打聽清楚了?只是太后要辦的一個家宴?」
「都打聽清楚了,準沒有錯的。」
趙樞這才稍稍放下心來,正要鬆一口氣出來,車馬卻突然停住了,趙樞道:「是什麼事?」
福安道:「有一隊校尉攔住了殿下的去路。」
「又是校尉?」趙樞惡狠狠地從車廂裏鑽出來,果然看到車駕的正前方是一隊騎馬的校尉不聲不響地駐馬而立,日頭正烈,十幾個人端坐在馬上不動,座下的戰馬似有不安,偶爾抖抖鬃毛打個響鼻。
趙樞勃然大怒,怒斥道:「好大的膽子,知道這是誰的車駕嗎?你們是瞎了眼嗎?來人,趕開他們。」
馬夫應命,好歹是王府出來的下人,腰桿子挺得直,得了主人的吩咐,立即拿著鞭子過去:「瞎了狗眼,肅王就在這裏,誰敢攔路?」想用馬鞭去抽開為首韓世忠的馬,韓世忠卻是比他更早先動手,揚鞭狠狠甩下,朝車夫的頭上抽了過去。
車夫的臉上立即一道血痕,痛得嗚哇作響,耳邊聽到韓世忠慢吞吞地道:「好大的膽子,天子門生也是你這奴才說打就打的?記著,這一鞭子是要你記住本分。」
趙樞臉色更是難看,大喝道:「叫你們的主子沈傲過來,我要看看,他哪裡來的膽子,敢支使人衝撞我的車駕。」
韓世忠恬然道:「沈大人即刻就到。」
正說著,街尾處一陣喧鬧,沈傲領著一列校尉打馬過來。
「沈傲!」趙樞怒不可遏地用手指向沈傲:「你要造反嗎?本王在這裏,你也敢帶兵來堵?這大宋的天下,還輪不到你姓沈的來說話。」
沈傲落了馬,當沒有聽見他的話似的,將馬繩交給一個親衛手裏,一步步走過來,撇撇嘴道:「敢問兄台是誰?」
趙樞怒道:「我是肅王趙樞,莫以為當作無知便可將此事揭過去,我要向父皇稟告,要向宗令府那邊狀告你。」
沈傲淡淡笑道:「你若是肅王,我就是太子了,諸位看看,我大宋朝的皇子個個都是高貴無比,就他這個樣子,像不像是皇子?」
校尉們哄笑,偶爾有幾個膽大的道:「不像。」
沈傲負著手,走到趙樞面前,冷笑著打量他,一字一句道:「這就是了,狗模狗樣的也敢冒充龍子龍孫!」
趙樞咬牙切齒,大怒道:「狗東……」
後面一個西字還未落下,沈傲手已揚起來,趙樞眼中閃過一絲驚恐,隨即啪的一聲,已被打翻在地。
趙樞的長隨頓時慌了,福安匆匆過來:「你……你們好大的膽……」
沈傲一腳踩在倒翻在地的趙樞身上,連正眼都不瞧他,慢吞吞地道:「狗東西是不是?這三個字也是你能叫的?你再叫一句來看看。」
趙樞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跡,他哪裡受過這樣的屈辱,憎恨地盯著居高臨下的沈傲,啐地吐出一口含血的痰:「我不殺你,誓不為人!」
沈傲呵呵一笑,臉上卻只是漠然:「好,我等著!」說罷,將腳從趙樞身上收回去,下令道:「來人,將這冒充皇子的狗賊拿了,帶回去細細地審問。」
校尉們立即蜂擁上去,將趙樞拖起來,用繩索將他綁了。趙樞的幾個長隨要來攔,這些校尉也絕不是好惹的,一拳過去,便將他們一個個打翻,捂著頭臉肚子嗚呼不絕。
趙樞吼叫道:「瘋了,沈傲,你瘋了,福安……快,快去稟告太子,去宮裏報信,還有宗令府,快!」
他的聲音越來越小,已被校尉們拖著越走越遠;福安嚇得面如土色,又不敢過去搶人,站在街上愣了片刻,才意識到真正出了大事,堂堂皇子,竟被人當街如死狗一般地拖走,這……還有沒有王法?
福安謹記著趙樞的吩咐,立即將長隨召集起來:「一個回府去向王妃報信,劉三,你去太子那邊,宗令府那邊我親自去……」
這般大的動靜,又在繁華鬧市裏,這裏已圍了不少人,也有幾個京兆府的差役看了,聽說是武備學堂的沈大人帶了人把肅王打了,這種神仙打架的事,他們也不敢出來主持什麼公道,立即從人群中縮出去,馬不停蹄地回京兆府稟告。
京兆府的當值判官聽了這個消息,也是嚇了一跳,有宋以來,固然皇子宗親的權勢得到了極大的壓制,可是當街毆打皇子的,那是絕無僅有的;便忍不住地問:「被打的當真是肅王?」
差役答道:「鐵定是的,肅王家裏有個主事叫福安的,也是經常在街面上露臉的人物,當時他也在場,還被校尉打了一拳。」
判官苦笑,道:「立即去請府尹大人來。」
那府尹心急火燎地過來,劈頭就問:「打的是肅王?肅王府上有沒有人來京兆府狀告?」
判官朝府尹行了個禮,道:「大人……這倒沒有。」
府尹鬆了口氣:「沒有就好,沒有就好,若是他們有人來,京兆府這邊少不得要硬著頭皮去向沈楞子要人了,肅王惹不起,可沈楞子我們也惹不起啊,這件事就當作什麼也沒有聽說過,不要插手,若是有人來問,就說京兆府沒有聽到傳報。」
判官頷首點頭:「下官明白了。」
京兆府那邊沒有動靜,刑部、大理寺也沒有動靜,各大衙門都有送消息的方式,可是難得的是,竟是一片沉默。
當街打皇子固然是死罪,卻也要看打的人是誰,沈楞子要打,你敢咬他?這種事還真不能去出頭,只能乾瞪眼,瞪眼也不對,只能當作什麼都沒有發生。
倒是事情傳到了御史台那裏,御史們就像打了雞血似的興奮起來,如蒼蠅盯到了臭蛋,一個個捋起袖子,就等著趁這個機會揮斥方遒一番。
兵部這邊,兵部尚書蔡絛的態度卻不是息事寧人,聽了傳報,他先是拍案而起,隨即道:「好大的膽子,姓沈的是要造反嗎?」
下頭的各司主簿卻都是一副不以為然,尚書大人太小題大做了,這是京兆府和宗令府管的事,兵部名義上雖然轄著武備學堂,但這種事又何必要管?
蔡絛的心思卻不同,這件事不管也得管,至少也要作出一個管的樣子,五皇子趙樞和他關係不錯,若是他作壁上觀,到時候怎麼好相見?雖說事情棘手,涉及到了沈傲,蔡絛也不得不作出個姿態,眼眸落在兵部侍郎身上,道:
「楚大人……」
兵部侍郎叫楚文宣,一聽到尚書大人點了他的名字,背脊一涼,心裏想:「莫不是叫我去交涉吧?」想著,已嚇得身如篩糠,眼珠子都快要突出來了,期期艾艾地道:「下官在……」
蔡絛道:「本官下個條子,你立即帶到武備學堂去,叫那姓沈的放人。」
楚文宣啊呀一聲,卻不敢答應,一邊是部堂,一邊是沈楞子,哪邊都不好得罪,若是其他的上官,他身為侍郎的頂回去就是了,可是偏偏蔡絛乃是太師的次子,身分擺在這裏,那也不是好玩的。
猶豫了一下,楚文宣道:「大人……若是武備學堂不肯又當如何?」
蔡絛沉吟片刻道:「拿我的條子,先去步軍司那邊借人,本官不信,他們武備學堂敢翻了天。」
楚文宣只好應命,等蔡絛寫了條子,攥著條子坐著軟轎到步軍司去,兵部名義上管著步軍司,可是高級軍官的任免卻不是兵部說了算的,不過,糧餉和低級軍官的功考卻是攥在兵部的手裏,多少要給幾分顏面,再加上下條子的是蔡絛,不看僧面看佛面,總算是調撥了一隊禁軍給他。
楚文宣心頭有了點底氣,立即帶人趕赴武備學堂。
一到武備學堂門口,撲面而來的就是令人生畏的肅殺之氣,數十名校尉按著腰間的刀柄,如標槍一樣在門口站定,連眼珠子都不去瞧他們一眼。
楚文宣要進去,卻被一個校尉攔了,厲聲道:「什麼人,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擅闖的,殺無赦!」
楚文宣止了步,略帶些尷尬,好在身後也有禁衛,朗聲道:「我是兵部侍郎,要見你們沈大人!」
那校尉上下打量他一眼,道:「先拿名刺來,看我家大人見不見你。」
楚文宣好歹也是從二品的大員,沈傲的幾個差事,不管是寺卿還是司業,滿打滿算也不過是正三品,只是形勢比人強,見個下官少不得要低聲下氣,只好拿出名刺,正色道:「快去稟告吧。」
校尉進去,過不多時,沈傲快步過來,門房處的校尉立即以他為首,以扇形拱衛住他。
沈傲慢吞吞地道:「兵部侍郎楚文宣?沒聽說過,找我何事?」
楚文宣見沈傲這般態度,心裏苦笑不迭,只好道:「奉尚書大人之命,請沈大人放人。沈大人,你是聰明人,毆打皇子已是罪無可赦,再拘禁龍子,就形同謀逆了。」
沈傲淡然地道:「兵部下個條子,我就得放人?當日我下的條子,兵部那邊為什麼不理會?你這算不算欺負我?」
欺負他?楚文宣心裏想:「誰敢欺負你?你倒是會惡人先告狀了。」面上只能正色道:「沈大人三思,這事兒鬧大,對誰都沒有好處。」說罷,忍不住看了周圍的步軍司禁軍一眼,膽氣大壯地道:「今次只是下條子讓你借坡下驢,下次只怕就是直接來拿人了。」
沈傲撣了撣身上的紫衣公服,慢吞吞地道:「我若是不放,你能如何?」
楚文宣一時愣住,隨即也有些怒氣了,道:「武備學堂還是不是下轄在兵部?你今日不放人,莫說宗令府那邊尋你的麻煩,將來就算你躲過這一劫,兵部這邊也絕不讓你好過。」
原以為說一句重話,能讓沈傲服軟;誰知沈傲眉宇一壓,一巴掌甩過來,直接打在楚文宣臉頰上,這一巴掌並不重,卻也讓人消受不起,楚文宣愕然,捂著腮幫道:
「你……你瘋了……」
沈傲一巴掌下去,後頭的校尉頓時升騰起無窮殺機,一個個將儒刀拔出半截,鏘的一聲,明晃晃的尖細長刀嗡嗡作響。
楚文宣身後的步軍司禁軍,原本還想為楚文宣討個公道,見到了這個地步,又看這些校尉隨時要殺人的勢態,一個個如霜打的茄子立即癟了,只好當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沈傲撇撇嘴,冷笑道:「回去告訴你的那個什麼尚書,就你和他還不配和我說這個,我給兵部下條子,那是給你們臉面,就憑你們的條子,也配支使我?滾吧!」接著旋過身去,對校尉們道:「沒有我的允許,誰敢踏入武備學堂一步,就是蔡京父子來了,也立即格殺,人死了再來稟告!」
話說到這個份上,沈傲理也不理外頭的人,已大步進去,留下目瞪口呆的楚文宣。
「聽到沒有,沈大人叫你們趕快滾,不要在這兒堵路,再敢停留,殺無赦!」校尉呼喝一聲,按著的儒刀仍然沒有回鞘,虎視眈眈地看著楚文宣和禁軍。
楚文宣看著隨來的一個步軍司禁軍虞候,那虞候當作沒有看見,咳嗽一聲,道:「沈大人的面子,我們要給的;他說什麼就是什麼,大家都在汴京當差,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何必要弄得這麼僵。」說著乾笑兩聲,不忘拉扯了一下楚文宣:「大人,咱們還是不要打擾了,走吧。」
楚文宣丟了面子,卻又無可奈何,只好乖乖回到兵部,心裏對步軍司那些禁軍忿忿不已。來的時候,這些人拍著胸脯保證,只要他們出馬,武備學堂多少會給幾分顏面,實在不行,也能保住侍郎大人的周全,誰知真遇到了事,一個個連大氣都不敢出。
回到兵部,楚文宣添油加醋地將沈傲的話說了,尤其是加重了他吩咐校尉時那一句「就是蔡京父子來了也立即格殺」。蔡絛臉色大變,道:「豈有此理,姓沈的辱我太甚!」說罷又看向臉頰高腫的楚文宣:「楚大人的臉沒有事吧?」
楚文宣咬牙道:「下官在回來的路上已經想好了,好歹下官也是讀書人出身,那沈傲在大庭廣眾之下毆打下官,下官一定要上疏彈劾。」
蔡絛頷首點頭:「不但要彈劾這個,還要彈劾拘禁皇子的罪,這事要鬧到滿城風雨,才能讓那姓沈的知道厲害。這事本官會去聯絡,一定會為你討個公道。」
楚文宣心裏想:「挨了一巴掌得了蔡絛引為心腹,倒也值了。」接著道了一聲謝,才退了出去。
武備學堂明武堂。
左右兩隊校尉叉刀而立,幾個博士各在案下落座,沈傲高踞在案上,臉色淡然。
堂中的趙樞被幾個校尉按在地上,雖在掙扎,可是哪裡掙得脫?口裏忍不住大罵:「沈傲,你記住今日……你這天殺的狗才,竟敢動我……」
沈傲不去理會他,那趙樞也是罵得累了,氣喘吁吁了一陣,再發不出聲音。
沈傲這才慢吞吞地開了口:「沈某人活在世上這麼多年,還沒有見過有人敢冒充皇子的,你是頭一個。」說罷冷笑道:「這般大的膽子,我今日算是見識了。說吧,你原名叫什麼,說了就輕饒了你。」
趙樞怒不可遏地道:「我叫趙樞,你裝什麼糊塗?」
沈傲淡淡一笑道:「你還在嘴硬是不是?還敢冒充皇子是不是?來人,賞他兩巴掌。」
一個校尉毫不客氣地抓住趙樞的頭髮將他的頭昂起,另一個左右開弓,啪啪地兩巴掌下去,打得趙樞嗚嗚地叫了兩聲。
沈傲闔著眼,又慢吞吞地道:「再問你,你原名叫什麼,是哪裡人士,竟敢冒充皇子?」
趙樞的門牙也落了一顆,臉色猙獰地吐了一口含血的吐沫:「你比我清楚!」
沈傲微微一笑道:「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了,到了這裏,你還想心存僥倖?來,掌嘴!」
校尉們如法炮製,四五個巴掌下去,打得趙樞差點兒昏厥,他咬著牙關,一字一句道:「沈傲……你……你這是要謀反,是要指鹿為馬……好,好,有本事,你殺了我……」
沈傲面無表情,繼續問:「你到底說不說?叫什麼,哪裡人士?」
趙樞咬牙不語,沈傲輕描淡寫地道:「繼續掌嘴!」
十幾個巴掌下去,趙樞的臉已經腫得老高,牙齒被打掉好幾顆,痛得趴在地上抽搐。
到了這個地步,固然他心裏再有傲氣,也不得不服軟了,自生下來起,雖說受人冷落,趙樞卻不曾吃過這樣的苦,終於含糊不清地道:「我說……我說……」
沈傲用眼神制止用刑的校尉,淡淡一笑道:「來,作記錄。」
一個博士已提起筆,蘸墨做好了準備。
「你叫什麼名字?」
「我……我叫趙……劉書。」
「籍貫?」
「汴京人士。」
「家裏還有誰?」
「……」
「為什麼不說?」
「有高堂在。」
「為什麼要冒充皇子!」
「我……」趙樞無力的吐出一口血水,這個時候卻是乖了:「臨時起意罷了。」
「臨時起意?」沈傲冷笑:「你好大的膽子,天潢貴胄那都是雲端上的人物,何其尊貴?當今聖上更是睿智神武,英俊不凡,他生出的皇子,豈是你能冒充的?」
沈傲說完這番話,隨即對記錄的博士道:「這番話要記好,一個字都不要漏。前頭最好寫上沈傲面北而拜,曰:……」
博士汗顏,點了個頭,按沈傲的吩咐繼續記錄。
沈傲繼續道:「冒充皇子,這就是謀逆,不過本官念你還能知錯,就打三十板子吧,來人,叉出去。」
如狼似虎的校尉將趙樞帶下去,隨即便傳出慘呼。
沈傲好整以暇地叫那博士取了筆錄來看,確認沒有差錯,才道:「立即報到宗令府去,到時候把這人一併帶過去,就說本官抓了一個該死的傢伙冒充宗室,只是打了一頓,具體如何處置,還要請宗令府那邊拿主意。」
博士頷首點頭,沈傲慢吞吞地喝了口貢茶,口中含著茶香,愜意地坐在位上,等那慘呼聲戛然而止,過了片刻,便有個校尉疾步過來,低聲道:「沈大人,按你的吩咐,搜出了點東西,請大人過目。」
說著,一塊香帕小心呈上來,沈傲摸了摸香帕,微微笑道:「一看就是御用之物,果然不出所料。」
說罷叫人備了馬,徑往宮裏去,甫一入宮,那邊楊戩聽到傳報,立即過來,急促地道:「沈傲,你是不是拿了五皇子?」
沈傲朝他點點頭。
楊戩嘆了口氣道:「宮裏頭已經有了消息,現在官家還不知道,被咱家壓住了,你快把人放了,去官家那兒請罪去。這是大罪啊,不管怎麼說,那趙樞也是龍子龍孫,當街毆打不說,還拘禁起來,到時候若是有人彈劾,誰也捂不住。」
沈傲含笑道:「泰山放心,我自有辦法,這件事和你一時也說不清楚,到時再向你道明吧,官家那邊,還得您老人家先穩住,我先去見太后。」
楊戩還要勸,那邊敬德也匆匆過來,這宮裏的消息本就靈通,沈傲入宮的事只怕早就傳到不少人耳中了,敬德含笑過來,先給楊戩行了禮,才道:「沈傲,太后聽說你入宮了,請您速速過去。」
沈傲頷首點頭,向楊戩行了個禮:「泰山大人,小婿先去了。」
說也奇怪,當著楊戩的面,沈傲也不好自稱小婿,可是有別人在場,他反而叫得順溜至極。
楊戩嘆了口氣,也不說什麼,隱隱覺得這背後或許和太后有什麼干係,只好道:「你好自為之吧。」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大畫情聖II之(2):兵行險著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畫情聖II之(2):兵行險著
大畫情聖第二輯隆重登場!看沈傲如何繼續在大宋朝出神入畫、呼風喚雨、耍賤搞笑,坐擁美女!
史上最強搞笑穿越小說,一代驚世笑典!網路原名《嬌妻如雲》,點閱率持續狂飆,橫掃各大網站!
不是只有外星人才有超能力!不是來自星星,而是來自現代的沈傲,自從穿越時空,意外回到大宋之後,徹底發揮他前世專業大盜的超能力,成了皇帝身前的第一紅人;更徹底發揮男人本性,將四個如花似玉的大美女娶進門。然而,伴君如伴虎,危機四伏、黨派鬥爭不斷的大內皇宮中,他真的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否極泰來嗎?
琴棋書畫難不倒他,談情說愛他的強項; 臨摹複製不算什麼,嬌妻如雲他的最愛! 大手筆出神入畫 新情聖非他莫屬 穿越不可怕,怕的是沒才華! 第一神偷穿越時空之後, 上至當今聖上,下至絕色美女,遠到邊藩外邦,皆拜倒臣服在他的伶牙俐嘴、厚顏無恥下, 憑著這股超強的「技藝」,沈傲將繼續為禍人間,誓言成為史上最強情聖!
【沈傲座右銘】
該罵的人不能少罵,該賺的錢不能少賺; 該泡的妹不能少泡,該娶回家的更不能錯過!
能文能武的沈傲,不只畫的一手好畫,偽造工夫一流,竟連帶兵打仗也難不倒他,武備學堂的菜鳥兵在他的魔鬼訓練下,不但建功立業,更成了大宋各軍營的儲備精英,使眾人再也不敢小覷。而沈傲也因立下大功,終於得以如願娶到帝姬安寧公主,讓他的嬌妻名冊上又多添了一筆。接下來,他將整頓大宋的海上勢力,他能排除萬難,順利達成任務嗎?
作者簡介:
上山打老虎——
只要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上山打老虎,網路超級新星,也是目前最炙手可熱的文壇黑馬,擅以輕鬆搞笑的文字,穿插真實的歷史背景,穿越上下,橫掃古今,只要一讀便難以釋手。另著有《士子風流》《明朝好丈夫》等精彩小說。
章節試閱
趙樞的車駕比尋常的皇子要華麗不少,他的性子本就有幾分張揚,再者,在宮中不受寵幸,索性也就無所謂了,平時的用度都是最好的。
坐在車廂裏,趙樞一頭霧水,稀奇古怪地赴了宴,正主兒沒有見到,就連那沈傲也中途離了席,不知這背後到底在弄什麼玄虛。
趙樞不安地張開眼,撩開車窗道:「福安。」
隨身伺候的主事福安立即快步到趙樞的車窗前,一邊追著車子一邊道:「殿下有什麼吩咐?」
「打聽清楚了?只是太后要辦的一個家宴?」
「都打聽清楚了,準沒有錯的。」
趙樞這才稍稍放下心來,正要鬆一口氣出來,車馬卻突然停住了,趙樞道:「是什...
坐在車廂裏,趙樞一頭霧水,稀奇古怪地赴了宴,正主兒沒有見到,就連那沈傲也中途離了席,不知這背後到底在弄什麼玄虛。
趙樞不安地張開眼,撩開車窗道:「福安。」
隨身伺候的主事福安立即快步到趙樞的車窗前,一邊追著車子一邊道:「殿下有什麼吩咐?」
「打聽清楚了?只是太后要辦的一個家宴?」
「都打聽清楚了,準沒有錯的。」
趙樞這才稍稍放下心來,正要鬆一口氣出來,車馬卻突然停住了,趙樞道:「是什...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上山打老虎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20 ISBN/ISSN:978986352018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奇幻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