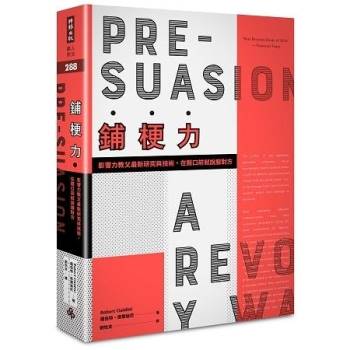◎史上最強搞笑穿越小說,一代驚世笑典!網路原名《嬌妻如雲》,點閱率持續狂飆,橫掃各大網站!
◎不是只有外星人才有超能力!不是來自星星,而是來自現代的沈傲,自從穿越時空,意外回到大宋之後,徹底發揮他前世專業大盜的超能力,成了皇帝身前的第一紅人;更徹底發揮男人本性,將四個如花似玉的大美女娶進門。然而,伴君如伴虎,危機四伏、黨派鬥爭不斷的大內皇宮中,他真的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否極泰來嗎?
穿越不可怕,怕的是沒才華!
第一神偷穿越時空之後,
上至當今聖上,下至絕色美女,遠到邊藩外邦,
皆拜倒臣服在他的伶牙俐嘴、厚顏無恥下,
憑著這股超強的「技藝」,沈傲將繼續為禍人間,
誓言成為史上最強情聖!
琴棋書畫難不倒他,談情說愛他的強項;
臨摹複製不算什麼,嬌妻如雲他的最愛!
大手筆出神入畫 新情聖非他莫屬
【沈傲座右銘】
該罵的人不能少罵,該賺的錢不能少賺;
該泡的妹不能少泡,該娶回家的更不能錯過!
早已與清河郡主互生情愫的沈傲,眼看著清河郡主竟將下嫁蔡家,不惜帶人準備搶親,誰知更令人咋舌的事還在後頭,新娘竟不是郡主,而被換成了郡主的貼身丫環。這是怎麼回事?而蔡府一場喜事變成衰事,又該如何收場?皇室又會如何處理善後?為了將功贖罪,沈傲奉命出使西夏,參加西夏公主的招親,這一趟出使,他是否能再立佳績,順利完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