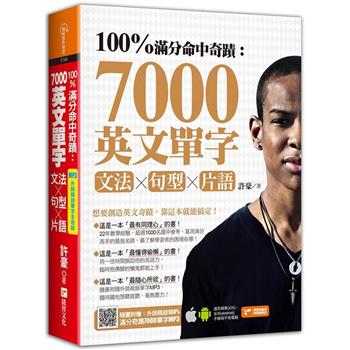泉州的天氣說變就變,可是在靠近永樂坊的春樓裡,這朦朧細雨,卻彷彿是調情的美酒,使這滿樓春色更顯香濃。
童虎笑吟吟地拉著一個人上了樓,二人笑嘻嘻地說著話,被童虎拉扯著的,不正是那讓整個汴京和福建路雞飛狗跳的蔡健?
其實這蔡健年歲也是不小,三十多歲的樣子,酒色掏空的身子顯得有點兒弱不禁風,穿著一件開襟的圓領衫子,開心地和童虎寒暄。
說起來,童虎和蔡健也算是老相識,當年童貫還在汴京的時候,為了巴結蔡京,便叫童虎專門去與蔡家人結交,因此童虎寫了張條子,說一句為兄在泉州盡情招待,便把蔡健給叫了來。
這樓裡的姑娘,真真是妖嬈狐媚至極,貝齒輕輕咬合,眼眸兒一勾,便叫人酥了,一邊祝酒,少不得還要唱首曲兒,無非是柳永柳相公或是平西王沈相公的詞兒。這些詞兒朗朗上口,既有幽怨,又含嗔帶著輕浮,最受煙花女子們喜歡。
一曲唱畢,兩個貴客已是開懷大笑了,不過這蔡健也是不明就裡,若他知道這曲子是沈傲那廝去勾引安寧帝姬的《長相思》,多半就笑不出來了。
狐朋狗友相聚,自然少不得閒聊兩句,兩杯酒下肚,蔡健已是滿肚子怨氣,說是自家好歹也是太師的嫡孫,卻被打發到那興化軍去,那裡的姐兒如何如何,自是不能和汴京、泉州相比,真真是悶出個鳥來了。
說罷,摟著一個姐兒調笑,嫺熟地將口中的酒送到姐兒的香口去,兩根舌頭攪在一起,已是欲火難耐,正要扶著兩個姐兒到樓上去,童虎卻是板起了臉,拍了下桌子道:「都出去。」
做這營生的人一瞧,哪裡不知道客人要談正事,立即如風一樣蓮步走了,臨走時,還不忘給蔡健拋個媚眼。
蔡健心裡有些不悅,直勾勾地用眼神送別了幾個頗有姿色的姐兒,才道:「童老弟這是做什麼?」
童虎朝他猙獰一笑,道:「蔡兄,你大禍將至了,居然還有閒心喝花酒?」
蔡健呆了一下,道:「這是什麼意思?」
童虎從懷裡掏出一樣東西狠狠拍在桌上,蔡健拿起一看,卻是一張文告,大意是衙門裡緝拿蔡健的文引,拿了這東西,才能調差役去捉人。
蔡健看了,卻是笑了起來,道:「哪個傢伙膽子這麼大?這泉州府難道不知道本老爺是誰?」
童虎嘿嘿一笑道:「就是知道你是誰,他們當然不敢拿你,可是有聖旨過來就不同了。」
「聖旨……」蔡健在蔡家算不得什麼人物,再加上自從來了興化軍,蔡京早已嚴令這裡的家小不得參與到裡頭來,所以這蔡健才對當前的朝局懵然不知,甚至連童虎去了武備學堂也不知道。
童虎道:「平西王你可知道?」
蔡健呆了一下,問道:「平西王是誰?」
「那蓬萊郡王呢?」
「沈傲!」蔡健不由咬牙切齒地道:「自然知道。」
童虎呵呵一笑道:「如今他已是平西王了,正是他唆使興化軍知軍彈劾你,陛下聽了勃然大怒,說你當街殺戮官差,罪無可恕,欽命了人來押解去你汴京。實話和你說了吧,便是太師也保你不住了。」
蔡健先是不信,可是漸漸地不得不信,又看了一眼那文引,上頭蓋了知府衙門的大印沒有錯,還有當地判官的大印也沒有錯,自家是什麼身分,泉州府會不知道?他們這麼做,自然是有恃無恐。再者說,自己是在泉州犯的事,泉州這邊下引也是正常,只是想不到,這件事竟是捅破了天,連宮裡都知道了。
蔡健咬了咬牙道:「好個狗賊。」隨即卻是一副六神無主的樣子道:「這該怎麼辦?不行,我該立即去汴京,有我……」
童虎打斷他道:「有太師在也不成,你糊塗了嗎?太師位高權重,豈會為了一個不肖子孫而毀了自家在陛下面前的前程?到時候少不得要上一道奏疏,說什麼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類的話了。」
童虎的話確實沒有說錯,蔡健便是再蠢,也知道一點端倪,他整個人一下子癱了下去,慌張地道:「這該怎麼辦?」
童虎一副沉重的樣子道:「遠走他鄉,立即就走,去南洋,去流求,只要不是大宋就可以,等風頭過了再回來。」他嘆了口氣,又道:「我已經為你安排好船隻了,就看你想不想走,想不想要這條命。」
蔡健臉上陰晴不定,半晌才是咬了咬牙道:「好,走!」
童虎心裡想笑,段海已經吩咐下來,令他送這位蔡公子滾蛋,若是不肯走,自然是殺無赦了,他肯點頭,倒是少了許多麻煩。立即帶了他出去,一面道:「若不是看在你我多年的交情上,我才不肯冒這麼大的風險知會你,不說也罷,時候來不及了。」
蔡健這時候當真是六神無主,只能乖乖聽話,隨著童虎到了城外的碼頭,果真有一艘小船等著。
童虎目送著蔡健上了船,什麼也沒說,立即往那望遠樓去,直接上了第五層,已經有人等著了。
南洋水師指揮楊過慢吞吞地喝著茶,請童虎坐下,望著窗外的海天一線,道:「事情辦妥了?」
童虎呵呵一笑道:「都妥當了,將他送走,保準以後再也回不來。」
楊過頷首點頭道:「當然回不來,那船上的人都不是善類,蔡公子死在海裡,便是神仙也撈不回來。」
童虎愣了一下,道:「怎麼……不是說……」
楊過深望童虎一眼,道:「平西王的意思是斬草除根,莫要走了一個。」
童虎倒吸了口涼氣,突然感覺那個平時嘻嘻哈哈的平西王,原來做起事來這般的狠辣。他哪裡知道,但凡能混到他叔父這個位置以上的人,哪一個都不是婦人之仁的角色,若真是這般手軟,只怕早已蹲到交州去玩泥巴了。
從福州到興化軍距離不過百餘里路,雖是不遠,可是蔡攸點了三百人之後,一刻也不敢耽擱,只用了半個時辰,便過了興化軍地境。
蔡家老宅位於興化軍仙遊縣,取名仙遊,八成是哪個糊弄人的傢伙胡扯見了神仙之類,神仙肯定沒有,可是仙府卻有一處,便是仙遊縣縣治不遠的一處大宅。
這處大宅幾經擴建,幾乎見證了蔡家的興盛,到如今,占地已經多達百畝之多,比之宮城也不遑多讓,一路的歌臺舞榭,還有福建路特色的院落,放眼過去看不到盡頭,一到夜間,更是無數的燈籠高高掛起,宛若平地仙境一般。
此時天色將晚,府邸裡頭的貴人們也都安生待在家裡,星光點點,與宅中的燭火輝映,有著說不出的炫目。
此時正是晚宴的時候,歡笑和絲竹聲響起,端地讓人羡慕無比,不遠處的田埂偶有佃戶扛著農具回家,望著這裡,都不禁要多看幾眼,自然沒人滋生出吾可取彼而代之的心思,只是嘖嘖稱羨。
可是這時候,官道上卻是塵土飛揚,黑暗中無數差役打馬過來,非但如此,還有一隊隊步卒手執兵刃,凶神惡煞般打破了這寧靜,田埂裡的人呆了一呆,立即一哄而散,走了個乾淨。
隊伍有些駁雜,既是差役,又有水軍,還有不少廂軍,差役在前打頭,後頭的水軍緊緊跟上,附近還有騎著馬的廂軍在旁警戒,隊伍簇擁著幾頂轎子,轎夫們健步如飛,走得極快。
這支人馬足有千人之多,尤其是那水軍,都是全身披甲,長刀出鞘,像是隨時準備上陣拼殺一樣。
到了蔡府外頭,轎子穩穩停住,差役和水軍已經來到門房,隱隱的燈籠,黑壓壓的人,說不出的詭異。
「你們是誰?可知道這是誰的府上?好大的膽子!」門房被這個場景嚇了一跳,隨即鎮定下來,想到自家老太爺,膽氣不禁壯了幾分。
從轎子裡走出兩個人來,起先的一個是個公公,正是楊碧兒,此後便是興化軍知軍段海。這兩個人一齊出轎,在燈火中相視一笑,早已有了默契。
打話的事自然不必他們去做,已經有個殿前禁軍衝上去道:
「奉旨拿辦蔡健!」
奉旨兩個字很是洪亮,底氣十足,門房嚇了一跳,什麼也不再說,立即去通報了,接著有人腳步匆匆地出來,正是蔡家的老七蔡淡,抱手行了個禮,道:「蔡健去了泉州,是哪個公公傳的旨意?先進來坐坐。」
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蔡淡甚至連消化的時間都沒有,況且蔡健確實去了泉州,先問問清楚再說。
換了其他的公公,在這興化軍蔡府門前,肯定要乖乖進去坐一下的,可是楊碧兒卻是咯咯冷笑一聲,道:「不必了,咱家欽命辦差,豈能和欽犯家人有糾葛?快把人交出來,好讓咱家早些回去繳了差事才是正理。」
蔡淡微微皺眉,此時已經感覺異常了,只好據實道:「蔡健確實是被友人叫去了泉州,請公公擔待。」
「哪個友人?」
「童虎!」
「童虎是誰?」
「童貫的侄兒。」
這不由引來一陣哄笑,連那段海也忍不住笑了,捋著鬚,看向楊碧兒。
楊碧兒的笑聲格外的陰森,惻惻道:「這麼說,是童貫童公公欺君罔上,刻意藏匿了欽犯了?」
段海笑得更是燦爛,待會兒回去,少不得要和楊碧兒商議一下如何給童貫寫封信了,攀咬到了童貫身上,還是欺君罔上,以童貫的性子,還不和蔡家之人拼命?
蔡淡見他們笑,已經有些惱羞成怒了,傳旨的公公又是這般無禮,以他的性子哪裡吃得消?冷哼一聲,道:「蔡健不在,不信,請上差搜查便是。」說著退到門房處,一副任君搜查的樣子。
楊碧兒和段海相視一笑,楊碧兒道:「搜是自然要搜的,搜出來了便好說話。要是沒搜出來,藏匿欽犯的罪名,只怕你們蔡家也擔待不起,來人。」
「在。」差役們紛紛吆喝一聲。
「挖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出來。」楊碧兒陰惻惻笑起來。
「遵命!」差役們就要蜂擁進去。
蔡淡卻是氣極了,原本以為這些人不敢進去,畢竟是蔡府,誰知他們卻是一點顧忌都沒有,一時吹起鬍子,瞪大眼睛要發作,可是念及那楊碧兒是欽差的身分,終究只好忍住。
「且慢!」段海笑著阻撓了差役。
蔡淡以為這段海服軟,臉上露出些許冷笑,還是這段知軍有眼色,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至於那個公公,到時候再收拾不遲。
誰知段海慢吞吞地道:「沒聽見楊公公吩咐嗎?挖地三尺,拿著水火棍進去如何挖?去,到附近農家尋些鍬鏟、鋤頭來。」他深望了蔡淡一眼,呵呵笑道:「不把地挖開三尺,我等如何回去覆命?」
「你……」蔡淡已經氣得說不出話,怒目瞪視著段海。
這時候蔡淡再蠢,也發覺出了異常,這些欽差就是來找碴的,他們的背後一定有人,否則憑一個公公和知軍,哪裡敢欺到蔡府頭上?
那些在外圍騎馬的廂軍聽了段海的命令立即去了,過了片刻,竟真的尋了許多挖地的工具來,差役們各自尋了個趁手的,都望向段海聽他吩咐。
段海朝楊碧兒笑了笑道:「公公,可以開始了嗎?」
段海是平西王的人,楊碧兒又是楊戩的人,在楊碧兒看來,大家是一家人,段海說的話和他說的沒什麼兩樣,方才段海既然敢叫人去挖地,背後肯定有平西王授意,自家還能說什麼?今日索性給平西王納一份投名狀。
想著,楊碧兒便冷聲道:「蔡府藏匿欽犯,罪無可赦,今日咱家倒要看看,是誰有這麼大的膽子,是誰給這蔡家撐腰,竟敢欺君罔上,做這等大逆不道的事。」
他撣了撣身上的灰塵,正色道:「挖!出了事咱家擔著,咱家是皇差,就不信什麼人敢阻攔!」
這句話直接給蔡府扣了個藏匿欽犯的帽子,有了理由,上頭又有通天的人物,還有什麼好怕的?楊碧兒放肆地咯咯一笑,聲音都尖銳起來:「殿前禁衛也一道去,誰敢阻攔,殺無赦!」
「遵命!」有楊碧兒這句話,大家的畏懼之心也就散了,正要蜂擁進去,卻聽到遠處隆隆的馬蹄聲響起來。
段海淡淡一笑,心裡想,福州的人這時候也該來了,平西王神機妙算,果然料定了蔡家那一對兄弟能看出端倪,他們不來,或許蔡家還有一條生路,來了就是死路一條。
段海高吼一聲:「黑燈瞎火的,是什麼人來,列陣!」
千名水師磨刀霍霍,早已按捺不住,依著蔡府的高牆列出方陣,長刀前指,鋒芒一片。
慘澹的月光下,三百騎兵飛馬過來,蔡攸跑得最近,看到蔡府門前這個樣子,已是驚怒交加,當先勒馬過來,大喝道:「什麼人敢在這裡放肆?」
蔡淡見蔡攸過來,猶如有了主心骨,高聲大叫:「大哥,他們這是要拆咱們蔡家的屋了!」
蔡攸冷笑一聲,向蔡淡道:「蔡健呢?」
蔡淡正要回答,楊碧兒尖聲大叫:「大膽,什麼人敢調動軍馬,驚動皇差行轅,可是要造反嗎?全部落馬,放下武器,來人,先把他們拿下再說!」
話音剛落,水師已經爆發出一陣怒吼,趁著這些騎馬的廂軍紛紛駐足的功夫,隨著號令,潮水一般衝過去,將廂軍撞了個人仰馬翻。
蔡攸大急,立即道:「胡說八道,我奉命前來協助皇差拿人……」話說到一半,便被震天的吼聲掩蓋下去,整個蔡府門前已是亂哄哄的一片。
這時,楊碧兒和段海相視一笑,猶如早有預謀一般,各自回了轎子,吩咐道:「走,一炷香之後收兵,就說賊勢盛大,我等始料不及,只好先行撤退。」
水師沒命地一衝,廂軍已經七零八落,對方先動了手,廂軍又沒弄清楚狀況,見對方殺氣騰騰,當然有回擊自保的必要,一場衝突便這樣產生。那蔡攸嚇得魂不附體,不斷地呵斥,卻無可奈何,好在他騎在馬上,也沒人理會他,倒是撿了一條性命在。
血腥化開,人一旦見了血,便開始變得瘋狂了,搏殺漸漸激烈,蔡府大門立即緊閉,唯恐有亂兵衝進去,差役紛紛散開,足足廝殺了一炷香,突然鳴金聲驟響,有人大吼:「賊勢太大,走!」一聲令下,水師便又如潮水一般褪去。
福州廂軍又是追殺了一陣,蔡攸大喊:「都不要動,你們這是要做什麼?」
好不容易勒住軍馬,蔡攸的臉色已經是難看到了極點,看到地上有幾十具屍首,大多是福州廂軍,其中還有一個,竟是殿前禁衛,臉色更是慘白,叫人去叫了門,蔡府把門打開,蔡攸衝進去,當先抓住躲在門後的蔡淡衣襟,大吼道:「蔡健呢?」
「去泉州了。」蔡淡期期艾艾地道。
「泉州?是誰請去的?」蔡攸的眼睛都快要冒出火來了。
「童虎……」
「童虎是武備學堂的人!」蔡攸急得跺腳,便立即明白,人家是早有預謀,這蔡健只怕是再也回不來了。他慘然地嘆了口氣,喃喃道:「蔡家要完了!」
蔡淡期期艾艾地道:「完……完……什麼,是他們先動的手……」
這蔡淡只是個紈褲子弟,被蔡攸一叫,真真是三魂六魄都給嚇散了。
蔡攸冷笑道:「皇差出了事,就是我們的錯。到時候,陛下會問,這個節骨眼上,為什麼福州廂軍會出現在這裡,會和皇差滋生衝突?以陛下的心思,我們說得清嗎?」
蔡淡呆了一下,牙關打顫:「要不要給爹傳信?」
「遲了。」蔡攸話語中有一種徹骨的寒意,無奈地道:「大難臨頭各自飛吧。」
原本是想趕在欽差之前先把蔡健控制住,誰知對方好像掐準了時間一樣,眼下又見了血,童貫那裡自然不必說,童虎一參與,必然鐵了心地攀咬到蔡家頭上。如今又死了殿前禁衛,殿前司自然也要反目,如今是三人成虎,已有牆倒眾人推的趨勢。
蔡攸森然道:「府裡藏了多少錢財?」
蔡淡不禁呆了一下。
蔡攸抬腿出去,叫來幾個呆著的廂軍虞候低語了幾句,虞候們立即叫了百來個人衝進去,隨蔡攸往蔡家庫房走。
蔡淡追過來道:「大哥,你這是要做什麼?」
蔡攸冷笑道:「收拾細軟逃命!」
「逃……」蔡淡期期艾艾地道:「逃個什麼,爹還在,再壞也壞不到那個地步。」
蔡攸卻不理他,到了府庫,叫人撬開鎖,紅著眼道:「只要黃金,能帶多少是多少。」接著森然笑道:「咱們現在都是謀逆之罪,方才是你們廂軍自個兒殺了禁衛,如今出了事,你們也跑不了,倒不如隨我出海。」他冷笑一聲繼續道:「幸好我在泉州還有點兒產業,經營了一支商隊,否則要逃也沒這麼容易,都換了衣衫,先把兵器丟了,帶了東西隨我走!」
蔡攸確實是個聰明人,若不是放出來太晚,也不至於到這個地步,如今步步落入沈傲的算計,蔡攸已經明白大勢已去,這時候逃命起來也絕不拖泥帶水,連汴京的家人都可以毫不猶豫地捨棄。
百來個廂軍呆了一下,也被蔡攸的話嚇住了,一時六神無主,咬了咬牙,只當蔡攸是主心骨,竟真的衝了進去。
蔡淡見狀,大怒道:「大哥,你這是要做什麼?」
蔡攸反手甩了蔡淡一巴掌,惡狠狠地大罵:「死到臨頭,還窮吼什麼?滾一邊去。」
帶著三百多個廂軍,都換了衣衫,拋了兵器,又套了幾十輛大車,帶著細軟,蔡攸騎在馬上,在蔡府外頭大聲吼道:「要活命的,隨我去泉州,現在他們只怕還沒有反應,咱們乘了船,揚帆出去。留在這裡只有死路一條,可有人敢隨我去嗎?」
他冷冽一笑,繼續道:「出了海,一樣和本大人吃香喝辣,妻兒沒了,到了那裡多的是女人,照樣給你們生孩子,離開這裡,總比任人宰割的好。」
廂軍冷靜下來,看到一地的屍首,也是沒了主張,這時候蔡攸一副不容置疑的樣子,又是許諾了前程,竟有一大半的廂軍跟了蔡攸去,其餘的,多半是捨棄不掉家人的,呆呆地望著這些人消失在黑夜之中。
蔡家這裡也是沒有反應過來,否則真要糾集起莊客和佃戶,也決不讓蔡攸這般恣意胡為,蔡攸聰明之處就在這裡,一眼便看透了他們的心思。
蔡淡倚在門上,已經有許多蔡家的人過來了,都問出了什麼事。蔡淡跺了跺腳道:「問什麼,去書房,寫信!」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大畫情聖Ⅱ之(6):奪嫡之爭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畫情聖Ⅱ之(6):奪嫡之爭
琴棋書畫難不倒他,談情說愛他的強項;
臨摹複製不算什麼,嬌妻如雲他的最愛!
大手筆出神入畫 新情聖非他莫屬
穿越不可怕,怕的是沒才華!
第一神偷穿越時空之後,
上至當今聖上,下至絕色美女,遠到邊藩外邦,
皆拜倒臣服在他的伶牙俐嘴、厚顏無恥下,
憑著這股超強的「技藝」,沈傲將繼續為禍人間,
誓言成為史上最強情聖!
【沈傲座右銘】
該罵的人不能少罵,該賺的錢不能少賺;
該泡的妹不能少泡,該娶回家的更不能錯過!
不知是穿越出了問題,還是沈傲辦事不利?雖然沈傲娶了好幾房嬌妻,卻一直沒有子嗣,不想他一到了西夏,西夏公主淼兒立即有孕,沈傲也父以子貴,晉升為議政王。回到大宋後,安寧帝姬竟也傳出好事,身懷龍胎。然而,兩個金孫竟成了大宋與西夏國力與地位的較勁,夾在中間的沈傲頓時頭大不已。而宿仇蔡京亦企圖力挽劣勢,保全蔡家,他與沈傲之間的恩怨又會如何發展?
重點:
◎史上最強搞笑穿越小說,一代驚世笑典!網路原名《嬌妻如雲》,點閱率持續狂飆,橫掃各大網站!
◎不是只有外星人才有超能力!不是來自星星,而是來自現代的沈傲,自從穿越時空,意外回到大宋之後,徹底發揮他前世專業大盜的超能力,成了皇帝身前的第一紅人;更徹底發揮男人本性,將四個如花似玉的大美女娶進門。然而,伴君如伴虎,危機四伏、黨派鬥爭不斷的大內皇宮中,他真的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否極泰來嗎?
作者簡介:
上山打老虎——
只要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上山打老虎,網路超級新星,也是目前最炙手可熱的文壇黑馬,擅以輕鬆搞笑的文字,穿插真實的歷史背景,穿越上下,橫掃古今,只要一讀便難以釋手。另著有《士子風流》《明朝好丈夫》等精彩小說。
章節試閱
泉州的天氣說變就變,可是在靠近永樂坊的春樓裡,這朦朧細雨,卻彷彿是調情的美酒,使這滿樓春色更顯香濃。
童虎笑吟吟地拉著一個人上了樓,二人笑嘻嘻地說著話,被童虎拉扯著的,不正是那讓整個汴京和福建路雞飛狗跳的蔡健?
其實這蔡健年歲也是不小,三十多歲的樣子,酒色掏空的身子顯得有點兒弱不禁風,穿著一件開襟的圓領衫子,開心地和童虎寒暄。
說起來,童虎和蔡健也算是老相識,當年童貫還在汴京的時候,為了巴結蔡京,便叫童虎專門去與蔡家人結交,因此童虎寫了張條子,說一句為兄在泉州盡情招待,便把蔡健給叫了來。
這樓裡...
童虎笑吟吟地拉著一個人上了樓,二人笑嘻嘻地說著話,被童虎拉扯著的,不正是那讓整個汴京和福建路雞飛狗跳的蔡健?
其實這蔡健年歲也是不小,三十多歲的樣子,酒色掏空的身子顯得有點兒弱不禁風,穿著一件開襟的圓領衫子,開心地和童虎寒暄。
說起來,童虎和蔡健也算是老相識,當年童貫還在汴京的時候,為了巴結蔡京,便叫童虎專門去與蔡家人結交,因此童虎寫了張條子,說一句為兄在泉州盡情招待,便把蔡健給叫了來。
這樓裡...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上山打老虎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9-21 ISBN/ISSN:978986352022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開數:正25K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奇幻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