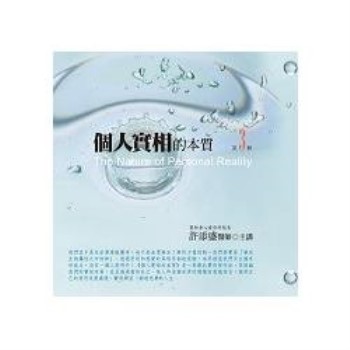琴棋書畫難不倒他,談情說愛他的強項;
臨摹複製不算什麼,嬌妻如雲他的最愛!
大手筆出神入畫 新情聖非他莫屬
臨摹複製不算什麼,嬌妻如雲他的最愛!
大手筆出神入畫 新情聖非他莫屬
穿越不可怕,怕的是沒才華!
第一神偷穿越時空之後,
上至當今聖上,下至絕色美女,遠到邊藩外邦,
皆拜倒臣服在他的伶牙俐嘴、厚顏無恥下,
憑著這股超強的「技藝」,沈傲將繼續為禍人間,
誓言成為史上最強情聖!
【沈傲座右銘】
該罵的人不能少罵,該賺的錢不能少賺;
該泡的妹不能少泡,該娶回家的更不能錯過!
太原突然發生地崩,不但造成流民失所、餓莩載道,竟成了當地巨商大發國難財的好時機。祈國公周正奉旨前往太原賑災,也因糧商哄抬物價,以致無法完成任務,背上賑災不力的黑鍋因而下獄,祈國公府頓時愁雲慘霧。且看沈傲如何智用妙計解救祈國公!又如何與當地富豪鬥法,懲治不良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