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書畫難不倒他,談情說愛他的強項;
臨摹複製不算什麼,嬌妻如雲他的最愛!
大手筆出神入畫 新情聖非他莫屬
臨摹複製不算什麼,嬌妻如雲他的最愛!
大手筆出神入畫 新情聖非他莫屬
穿越不可怕,怕的是沒才華!
第一神偷穿越時空之後,
上至當今聖上,下至絕色美女,遠到邊藩外邦,
皆拜倒臣服在他的伶牙俐嘴、厚顏無恥下,
憑著這股超強的「技藝」,沈傲將繼續為禍人間,
誓言成為史上最強情聖!
【沈傲座右銘】
該罵的人不能少罵,該賺的錢不能少賺;
該泡的妹不能少泡,該娶回家的更不能錯過!
太原的地崩,不只造成當地人民頓失家園、饑荒遍地,更造成了一場不小的政治地震。有心人趁著這場變故,不僅大賺黑心錢,更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剷除異己。這當中尤以懷州幫的勢力最為蠻橫。為了救出恩公祈國公,沈傲不惜以身試法,不經上奏便斬殺了當朝國公及封疆大吏,使趙佶震怒不已,不得已下令將沈傲押回京師,進行御審。而宮廷內私底下的派系鬥爭亦搬上檯面,火熱展開,究竟勝負如何?沈傲真能扳倒不良富豪,阻止惡勢力的蔓延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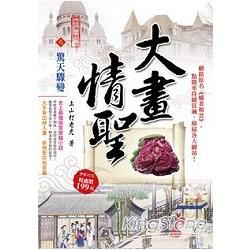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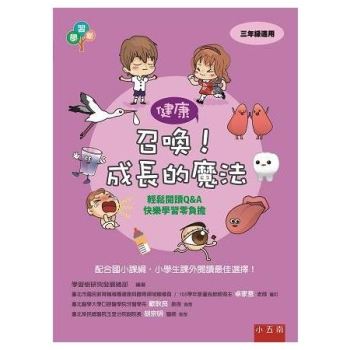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