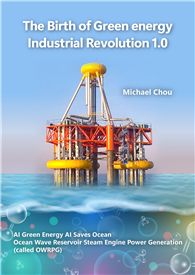施琅只是眼睛一瞄,便笑道:「是鄭老三啊!我料想此次若不是鄭芝龍親來,便一定會委鄭老三為將,果不其然。」在鄭鴻奎身邊繞上一圈,感慨道:「想我施琅初投鄭芝龍時,因性格脾氣與鄭氏兄弟不合,屢次被他們陷害,若不是鄭一念我有些本事,早就砍了我。嘿嘿,還好我遇著廷斌和志華兄,若不然,我可死的比眼前此人早得多了。」
說罷令道:「來人!將這賊的首級剁下,用木盒裝好了,回去獻給指揮使大人。」
他與周全斌親見鄭鴻奎的首級被親兵用大刀剁下,小心擦乾脖子上的血跡,裝在了木盒之中,施琅嘆道:「若是鄭芝龍的首級,大人便可以高枕無憂了。」
周全斌沉吟道:「便是如此,亦無憂矣。此戰之後,鄭芝龍用來橫行海上的勢力已被連根拔起,他便是不被打垮,想恢復元氣也是不可能的事了。他一個海防游擊,手頭上半艘船一個水手也無,熊文燦還能信任他,倚重他麼?沒有海外貿易,沒有收取水引的實力和特權,就憑他陸上的幾千名烏合之眾的步兵,拿什麼來和大人鬥?他留在澎湖的上百條大小商船必將為大人所得,就是安海還有一些,沒有保護又怎地敢出海?別說有大人在,就是那些被他得罪過的小股海盜也不會讓他安生,此人算毀了。」
施琅聽他說完,微笑道:「全斌,你當真是出師了!分析的中肯實在,絲絲入扣。不錯!鄭芝龍此人便是活著,要麼就做個面團團的富家翁,還可保一生平安,享享清福;若是還想東山再起,我料大人不會讓他活著的。」
此時,那鄭氏艦船已然遠遠逃出火槍射程,那兩千神策軍士早已停止射擊,因適才太過緊張,各人雖沒有得到命令仍原地戒備站立,卻是一個個神色疲憊,萎頓不堪,一個個用槍拄地,勉強能夠站著罷了。
周全斌伸手招來一個果尉,問道:「現下各船傷亡如何?咱們死傷多少,大概打死打傷多少敵人,可有計數?」
「回大人的話,適才用旗語問過了,咱們戰死了三名弟兄,不是被敵人砍死,卻是不小心失足落水淹死的,當真是可惜!餘者有十幾名傷者,亦是不小心擦傷者多,各船加起來不過躍上來不到百人的敵軍,皆是一上來便被亂槍射死,是以沒有對咱們造成什麼損傷。至於敵人,據估計,敵人來攻時有五六千人,適才退走時,留下的屍體足有三千餘具,逃走的也大半帶傷。情況大略就是這樣,若是大人想知道的詳細,那只有再加統計後,才能知曉。」
周全斌嘿了一聲,也不知道是可惜那三名落水而亡的士兵,還是驚異於這麼大的傷亡比重。
那都尉見他無話,便躬身一禮,逕自去了。
周全斌正待回頭尋施琅說話,卻聽得船上火炮轟然而響,原來是船上的炮擊又開始了。
敵船來時順風,回去逃命時卻是逆風,逃得慢了,自然會多吃上幾顆炮彈,不一會兒工夫,幾十艘船便又有不少起火下沉的,海面上起起伏伏的漂著被丟下的屍體,不慎落水的士兵或傷兵,他們原是弄潮的好男兒,此時卻是精力疲敝,哪有力量游得動?不一會工夫,那水面上如同熱鍋裏餃子一番翻騰掙扎的士兵們,便一個個靜止不動,安詳地趴在這湛藍的海面上,一切人世間的紛爭苦楚,從此便不再與他們相關了。
這些船隻原本也不想向那澎湖逃走,此時的澎湖是兵凶戰危之地,各人逃跑,自然是想往內陸安海逃跑。只是對方的那十幾艘小炮船卻是返回,隱隱約約將向陸地的海面封鎖,各船誰先靠近,自然會被準備好的炮擊打沉,誰還願意做這傻蛋,去為別人開路?無奈之下,只得拚了命的向澎湖跑,指望著這洋人不敢上陸搏鬥,可以在澎湖堅守一陣子,等候鄭芝龍派兵來援助。饒是如此,亦是有十餘艘小船向大陸方向逃去,施琅見追之不及,也只得罷了。
這夥人失了指揮,只是拚了命的駕船向澎湖港口駛去,雖然施琅命令大小艦船不停地開炮射擊,開花彈實心彈不停地在他們頭頂掠過,這些人也不管不顧,一心逃命,如此這般,倒是比開始進攻時早受了不小損失。
待澎湖港口在望,那些大大小小的軍官總算鬆了一口氣,看著身後追擊而來的軍艦,各人心裏都在想,你們的火槍兵再厲害,總不成敢深入內陸和我們打,雖說我們只剩下不到四千的疲敝敗兵,不過在陸上可不是海上,靠近不易,就是被你們打死幾百人,總該能衝到你們陣裏了吧,到時候憑著咱們的刀頭工夫,你們可不是找死麼!
各人想到此節,均是心中大定,那緊張的身軀便慢慢鬆弛下來,各軍官都吆三喝五的吩咐手下士兵手腳俐落些,待上岸後,立時休息,提防敵軍來攻。
各鄭軍士兵大半也是同將領們的想法相同,待船隻進港口,大家均是鬆了口氣,匆忙將船靠上碼頭,搭上舢板,立時一窩蜂的衝下船去,待踏上陸地之時,這些橫行海上多年的水師官兵們,竟然一起嘆一口氣,然後歡呼起來。
各人都是面露喜色,料想那可怕的炮艦再怎麼厲害,可也沒有辦法上內陸來炮擊了吧?於是待上岸整隊完畢,十幾名中高級軍官合議完畢,一聲令下,便全隊將澎湖本島的原鄭氏所居的城鎮方向行去。這幾千人馬早已疲乏之極,需得早些尋得一個安全地方休整歇息,不然若是敵軍真的攻來,那只有死路一條了。
鄭芝龍雖是有錢,卻懶於花錢在修路上,從碼頭到鎮上約有五六里地,都是草草鋪就的土路,此時雖未至夏,卻也是乾燥異常,幾千人在這土路上揚塵帶風的走,不一會工夫便是塵土飛揚,隔著數里路也能看到騰空而起的煙塵。
除了留下看守港口的哨探,所有的鄭軍士兵皆隨大隊向鎮內撤退,各將領都打定了主意,待到了鎮街,便拆了街頭的房屋,用來築守防禦工事,讓敵人不能順順當當扛著火槍靠前。
那各千戶、百戶官都走在最前,原本是有馬代步,只是在碼頭匆忙,忘了這事,每人都是開動雙腿,走得辛苦不堪。
有一何姓百戶心中鬱憤,心裏想,待會建好了街壘,讓哨探多多打探敵軍消息,自個兒可要回到鎮上的青樓,找個紅倌人摟著睡個好覺,非得好生壓一下驚才可。待走到鎮頭處一里開外,那眼尖的士兵卻看到鎮首處有豎起的尖木樹柵,還有些屋料木桌之類,亂七八糟的擺滿了一街,將原本只有一條入口進出的大路堵得嚴嚴實實。
看到此番混亂模樣,有一千總便罵罵咧咧說道:「娘的,不知道是哪個膽小鬼,他娘的咱們人還沒有進鎮,就堵成這般模樣,這可叫咱們怎生進去,難不成老子累成這樣,還得爬進去不成?」
眾人原本吃了敗仗心中不樂,又見有人拋棄友軍,自己拚了命的跑回將路堵死,都是勃然大怒,於是突然間步履蹣跚的眾軍官都突然間有如神助,一個個甩開雙腿拚了命的跑將起來,身後大隊見軍官帶著頭向前跑,於是也一個個甩腿向前,只苦了那些有傷在身的士兵,一個個疼得直咧嘴,卻也是不敢掉隊,只拚了命的跟隨向前。
待堪堪行到那街壘前數十米,便有幾個官兒大聲叫道:「裏面是誰的部隊,怎地跑得這麼快,快把街壘移開,放咱們進去!」
見裏面一時沒有反應,便有人議論道:「裏面的人也太過膽小,他娘的現在就弄成這副模樣,顯是船隻落在後面,見了咱們被打的慘狀,於是想起要弄這玩意,不知道是誰帶的兵,一會兒查出來,非稟報了鄭爺,重重的處罰才是。」
見裏面還是沒有反應,眾人又向前行,邊走邊喊道:「快給老子出來!」
卻聽得有人大笑著答道:「哎,乖兒子,你爹就出來了!」
眾軍官聞言大怒,一起罵道:「他娘的是誰在裏面,把他揪出來一頓臭揍!看他還敢不敢!」
卻見那街壘內突然有一頭戴大紅紗帽,身著錦衣棉甲的軍官站將起來,此人二十多歲年紀,臉上正是笑意盈盈,見各人目瞪口呆,便將身一躍,跳上一張桌子,叉腰大笑道:
「老子在這裏等你們多時了,嘿嘿,海上打仗沒有辦法,總會有漏網之魚,是以全斌他們易裝改扮,老子卻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子姓張名鼐,台北衛指揮僉事,今日奉指揮使大人的命,將你們一網打盡!」
鄭軍將領正自發呆之際,卻見那張鼐將手一揮,數千名持槍士兵如同鬼魅一般從屋頂、壘牆上冒了出來,槍口平端,正瞄準了這支狼狽不堪的逃亡軍隊。
這夥人剛剛見識了火槍齊射的厲害,見眼前這麼近的平地上突然有這麼多的火槍瞄準自己,各人皆是嚇得魂飛魄散,一時竟然沒有反應之力,那些嚇破了膽的,竟然連尿都流將下來。
只聽那張鼐大聲喊道:「金吾衛眾軍士,聽我命令,齊射!」
喊罷,便見那些青衣軍士伸在火槍扳機裏的手指一扣,砰砰砰,兩千支火槍一起開火,向那些殘兵敗卒射去。
張鼐站在那破木桌上,看著眼前的鄭軍殘部被手下的精銳打得抱頭鼠竄,適才對方因猝不及防,離得距離又太近,第一波槍響過後,已是黑壓壓打倒了幾百號人,又因軍官急著入鎮,大半行在隊列前面,故而那渾身鮮血淋淋倒在地上抽搐掙命的,十有八九都是鄭軍的中下層軍官。
那些士兵原本就被嚇破了膽,現下槍聲又在眼前響起,各人都是魂飛魄散,發一聲喊,連手中武器都拋卻不要,什麼行伍隊列亦是不顧,又因沒有軍官約束,一瞬間,這三千餘人便星散而逃。張鼐的金吾衛只開了不到三槍,那些鄭軍已是跑得蹤影不見。
張鼐身邊的金吾衛參軍向他笑道:「大人,這夥賊當真無勇之極,怎地連象徵性的衝鋒都不做,就跑成這般模樣。看來,他們的隊伍是散了,咱們可以放心派人追擊了。」
「不急,留在台北的神策和金吾還有指揮使大人的飛騎衛就要到了,咱們是打頭陣的,功勞已然立下了,總得留些給後來的兄弟們。」
「嘿嘿,大人是想讓張傑將爺立些功勞吧?」
張鼐不隱瞞道:「沒錯。我們兄弟三人,就我和張瑞坐上了正四品指揮僉事的位置,張瑞統領飛騎一軍,職權皆重,我又是領金吾四千人馬,只有張傑,現下不過是校尉,兄弟三人在一起,怪尷尬的。」
他自然不知張偉將監視軍中將領的另一特務派系交給了張傑,張傑與那羅汝才不同,只是對內而已。若論起信任親近,張傑絕不在他二人之下。因見張傑還只是個校尉,心中只欲他立功,便止住部下追擊的念頭,只待張傑領後續兵馬坐船而來,便令張傑漫山遍野的去追殺那些殘兵,功勞自然是輕鬆落袋了。
看著逐漸遠去的敗兵,張鼐沉思片刻,終下令道:
「適才只是將鎮圍住,沒有仔細搜索,現下以每五十人為一列,撒開五里範圍,搜索逃走躲藏的鎮民,將他們一併驅趕到鄭氏大宅。」
又沉吟道:「至於港口的漁民行商,自有周將爺那邊處置,不需咱們動手。快,傳令全軍,立刻行動。各人聽好了,若是走脫了一人,便拿帶隊的果尉抵還。若是走脫了十人,便拿都尉、校尉問罪!」
他身邊的諸校尉都尉見他臉色鐵青,殺氣十足,各人從未見他如此模樣,皆是嚇了一跳,忙各自帶著手下人馬,四散開來去搜索澎湖鎮民去也。
張鼐突然想起一事,忙對身邊一參軍道:「你快帶幾個人去碼頭,估計施將爺快到了,你問他,這鄭氏留在島上的鎮民知道怎麼處置,但是四散在本島上的幾千名墾荒的農夫,他們可不是鄭氏的人,問施將爺,指揮使大人可曾有令,該當如何處置?」
見那參軍領命去了,張鼐也自去帶隊搜索,一直忙到傍晚時分,那留在台北島上的金吾和神策兩軍,及張瑞帶領的飛騎衛也乘船趕到。
又接到施琅傳令,道:「那些農民暫且不問,待大人有了處置意見再說。若是有協助藏留鄭氏敗軍的,誅殺!」
此時澎湖港口已被施琅的水師控制,又派遣了上百艘小船在海上四處巡邏搜索,以防有人從島上偷偷尋得小船,下海而逃。那澎湖本島卻已齊集了九千多台北大軍,雖然天已近晚,但各部短暫休整過後,便打著火把分路搜索。
那澎湖鎮民早就被搜捕一空,盡數關押在鄭氏大宅之內,除了留下兩百人看守之外,所有的台北士兵全數出動,在整個澎湖島上搜索敗軍。
這一夜,幾十里方圓的澎湖島上火光四起,火槍發射的彈道不時射向半空,劃出一道道美麗的光影。那些敗兵各自躲藏在山谷、河灘、樹林、民居,一個個驚慌失措,疲累不堪,又已被嚇破了膽,雖然人數還有兩三千之眾,卻是星散而逃,最大的一股敗兵也不超過百人,故而被台北軍隊一一從藏身之所尋到,也不管他們是逃走還是投降,見面便是一槍。
後來殺得多了,那些敗兵知道無法脫身,倒是又有膽大些的集合人數,三二百人的一股向搜索部隊反擊,雖然勇則勇矣,卻也只是死得更快一些罷了。他們大半沒有武器,且是又餓又累又驚又怕,鼓足的勇氣不過是求生的欲望罷了,面對五百人一隊的搜索大隊,又有何威脅可言?
砰砰一陣槍響過後,僥倖未死的便又奪路而逃。如此這般反覆拉鋸,待到了下半夜,周邊的敗兵已由郊野被攆到鎮子四周。
張鼐與周全斌會議之後,決定留半數士兵在外線駐守,半數由兩人帶領,用半圓形方式向內搜索。
此番回頭搜索是以搜索民居為主,什麼馬廄、草堆、豬圈,皆以飛騎的長刀刺入查看,那些敗兵果然大半藏身於內,一刀刺入,便可聽到裏面發出一聲慘叫,待長刀抽回,便見刀上鮮血漓淋,待那傷兵竄將出來,便是一陣槍響。
如此這般來回掃蕩數次,其間又燒毀了十數家窩藏敗兵的民居,將居民與所藏敗兵盡數殺了,直到天明後日上三竿,再也尋不到一個敗兵,周全斌與張鼐又調集了鎮外所有的健壯農夫,沿路收集屍體,將數千具屍體集中在一起,又以平板大車拖向海邊,一個個裝進麻包,扔下海裏了事。
周全斌待搜索完畢,已是疲累不堪,卻又接了張偉手書,令他將澎湖墾荒的農民及漁民驅趕上船,每家只許帶隨身的物品,至於農具等物,由台北派人前來收取。
他接令後不敢怠慢,立時派兵挨家挨戶的催逼,待傍晚時分,終將澎湖農戶及漁民四五千人盡數驅趕到台北前來的船隻之上。
周全斌站立於一艘炮船的船首,眺望整個澎湖島方向,只見島上火光大起,想來是張鼐開始屠殺鎮上與鄭家相關的被押平民。周全斌心中不忍,隱隱約約彷彿聽到火光中傳來一陣陣的呼喊求饒聲。
周全斌將雙目緊閉,心中很感激張偉先調他回台北。如若不然,留在島上,那又是別有一番滋味了。
他慶幸溜得快,張鼐卻倒楣許多,忙了兩天一夜,卻不得休息。這也罷了,還不得不面對那些老弱婦孺的哭喊求饒。他倒還撐得住,只是手下的士兵卻有些遲疑,若不是經年的訓練他們要服從命令,這樣殺戮平民的事,到底是讓人不好下手。
他心裏正自埋怨張偉,心中只道這些人與其殺了,還不如盡數運到台北做苦力的好。
張鼐身為軍人,自是不知政治上的錯綜複雜,現下攻打澎湖是以英軍名義,待過一陣子,張偉自會奏報朝廷,道是打跑英軍,收復澎湖。若是將這些人送往台北,難保不走漏風聲,況且這些人大多與鄭家有著複雜的關係,張偉實在難以信任。若是留在台北,與台北的異己分子勾結,那高傑的巡捕營樂子可就大了。是以張偉思來想去,終究下定了屠戮決心。
數日之後,張偉自離開鄭芝龍前往台灣之後,終於又再次踏足澎湖。在何斌、施琅等人的陪同簇擁下,張偉自台北乘船至澎湖。
於碼頭上岸後,便直奔自己原本在澎湖的宅子而去。
興沖沖進門之後,四處流連不休,直待何斌不耐煩向他道:「志華,你要是喜歡這裏,乾脆從台北搬過來住好了。何苦在此轉個不休,所有的金吾、神策衛的軍官都在鄭家大宅等你去訓話呢。」
張偉眼見自己初到明末的物品皆封放於這宅中庫房之內,心中喜悅,向何斌笑道:「看著這些舊物,緬懷一下過往罷了,你何苦這麼著急。」又道:「怎地在那宅中,去,把人都叫到這邊來!那邊雖大,血腥之氣太重,我不喜歡。」
「嘿,殺人的命令是你下的,現下卻嫌血腥氣重了。」
「那是不得已,你當我好殺麼?那宅子自從李旦一家被殺於內,又有鄭芝龍常在那裏暗中殺人,現下我又在那兒殺了不少人,當真是怨氣十足,能不去還是不去的好。」
邊說邊行,到得他原本的臥房之內,便躺倒在那大床之上,舒服地伸個懶腰,笑道:「還是舊床睡得舒服,人總是追求新房子,新床,新老婆,其實,還是舊家什使喚起來舒服啊。」
何斌卻不理他,只將張鼐等人召將過來,問及當日戰況。他雖不是領兵大將,不過在台灣也只有少數人能與張偉言笑不忌,他便是其中之一。更何況手握財賦大權,現下過問幾句,張鼐等人自是恭敬有加,一五十一向他說了。
待聽完之後,何斌向張偉喟然嘆道:「鄭鴻奎死,水師全部敗亡,澎湖基業被奪,鄭芝龍想不吐血都難。」
「哼,他不吐血,我也打得他吐血。」
說到此處,張偉翻身而起,看向那何斌神情,見他神情黯然,卻又噗嗤一笑,道:「到底他曾經救過我,又曾是我老大,只要他安心做個富家翁,我日後再不會為難於他。憑他的家資,只怕是十輩子也享受不完,是福是禍,只看他自選吧。」
「唔,這也是正理。咱們不可逼人太甚,凡事留三分餘地的好。」
張偉「哈哈」一笑,不再多說,起身向外行去,道:「成了,咱們到外堂說話,想來那些軍官也都該到了。」
待一行人隨他到了外堂,卻見院子裏站著水師及金吾神策兩衛的都尉以上軍官,一群人無聊,正嘻嘻哈哈打鬧說話,遠遠見張偉來了,頓時沒有人再敢作聲,各人皆是垂手侍立,只待張偉上前訓話。
「此番攻澎湖一役,打得甚好。我也不必多誇你們,各人的帳各人有數,該賞便賞,出多大力,拿多少賞,何爺就是囊中無錢,賞銀卻都是備好了的。」
見各將微微一笑,張偉又道:「只是此戰咱們以強擊弱,也算不得什麼。鄭軍人數雖眾,武器船隻落後咱們太多,又是在海上接戰,妄圖以跳幫肉搏之法打咱們,卻遇著幾千的火槍兵,那不是自尋死路麼!是故,打勝了也甭驕傲自得,以為咱們台北之師便是精銳之至,橫行天下無敵了,差得遠呢!」
諸將凜然諾道:「是!指揮使大人訓斥的是,職部們不敢。」
「很好!和你們說這些,倒不是有意要打壓你們,我手下不要唯唯諾諾的庸材,該得意時,你們想藏著,也是不成。聽我說,待此事風聲平息,我便要令水師出海,威逼倭國,把鄭芝龍的倭國貿易搶將過來。水師以炮艦轟擊那倭人的港口,你們步卒也得準備隨時上岸,以便擴大戰果。海陸並進,一定要讓倭人知道厲害,從此臣服咱們!」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新大明王朝(3)【中日大戰】的圖書 |
 |
新大明王朝(03)中日大戰【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淡墨青杉 出版社: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1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288頁/15*21mcm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57 |
仙俠/武俠 |
$ 169 |
小說/文學 |
$ 179 |
科幻/奇幻小說 |
$ 195 |
東方玄幻/歷史 |
$ 199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新大明王朝(3)【中日大戰】
穿越時空 回到大明
復興王朝 龍騰天下
內憂外患的明朝末年,誰能力挽狂瀾,救黎民於水火之中?來自現代的他,該如何扭轉乾坤,改變命運?
大明末年,天下大亂。
農民起義軍在李自成的率領下攻城掠地,所向披靡。
與此同時,關外一代人傑皇太極親率十萬精銳八旗騎兵,隨時準備入關,奪取大明天下。
張偉——一個整天沉迷在電玩遊戲的現代宅男,因意外穿越時空,回到十七世紀的大明末年。此時大明王朝已是千瘡百孔,搖搖欲墜。張偉利用自己現代的知識,自一個小小的海盜起家,步步走上了問鼎天下的道路,從而改變了大明王朝的歷史……
淪為海盜,落草為寇的張偉,在鄭芝龍的幫忙下,竟也闖出一番成績。然而,在眾人一片看好下,為謀求日後的大業,他竟自願退居開墾當時還是一片蠻荒、百廢待興的台灣,他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他與鄭氏的海上地盤之爭也終於展開,又是否能如他所願呢?
作者簡介:
淡墨青杉,網路上異軍突起的新一代人氣作家。作品多以結合歷史和現代為主,依據真實歷史為背景,或史上知名人物為主旨,加上輕鬆幽默的對話及流利暢快的劇情,讓人一讀便無法放下,堪稱現今最夯最熱的青年作家,獨霸書市。
章節試閱
施琅只是眼睛一瞄,便笑道:「是鄭老三啊!我料想此次若不是鄭芝龍親來,便一定會委鄭老三為將,果不其然。」在鄭鴻奎身邊繞上一圈,感慨道:「想我施琅初投鄭芝龍時,因性格脾氣與鄭氏兄弟不合,屢次被他們陷害,若不是鄭一念我有些本事,早就砍了我。嘿嘿,還好我遇著廷斌和志華兄,若不然,我可死的比眼前此人早得多了。」
說罷令道:「來人!將這賊的首級剁下,用木盒裝好了,回去獻給指揮使大人。」
他與周全斌親見鄭鴻奎的首級被親兵用大刀剁下,小心擦乾脖子上的血跡,裝在了木盒之中,施琅嘆道:「若是鄭芝龍的首級,大人便可以...
說罷令道:「來人!將這賊的首級剁下,用木盒裝好了,回去獻給指揮使大人。」
他與周全斌親見鄭鴻奎的首級被親兵用大刀剁下,小心擦乾脖子上的血跡,裝在了木盒之中,施琅嘆道:「若是鄭芝龍的首級,大人便可以...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圖謀澎湖
第二章 平定澎湖
第三章 招兵買馬
第四章 再得賢才
第五章 高山土著
第六章 遠征倭國
第七章 長崎之戰
第八章 長崎和談
第九章 長崎和約
第十章 高山騎兵
第十一章 農民起義
第十二章 反間之計
第十三章 偷襲遼東
第十四章 兵逼瀋陽
第十五章 盛京血戰
第二章 平定澎湖
第三章 招兵買馬
第四章 再得賢才
第五章 高山土著
第六章 遠征倭國
第七章 長崎之戰
第八章 長崎和談
第九章 長崎和約
第十章 高山騎兵
第十一章 農民起義
第十二章 反間之計
第十三章 偷襲遼東
第十四章 兵逼瀋陽
第十五章 盛京血戰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淡墨青杉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10 ISBN/ISSN:978986352032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武俠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