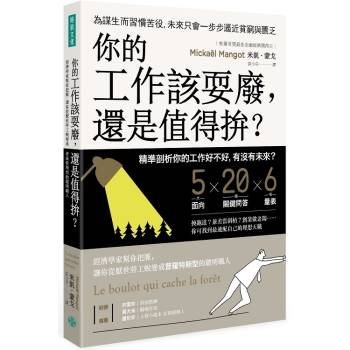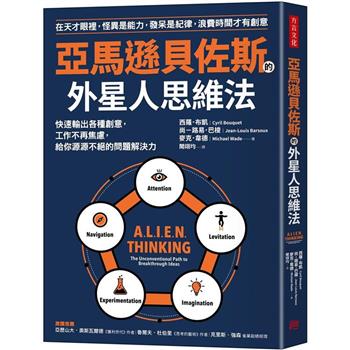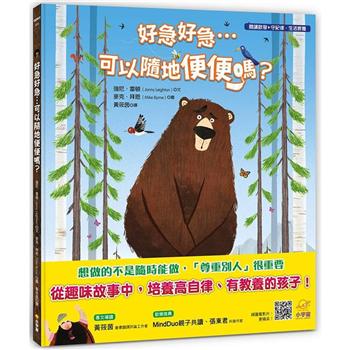張偉已縱騎接近城池,親眼目睹這一幕慘劇,只覺眼前鮮紅一片,盡是那些垂死掙扎卻不知道生路何在的百姓,看著他們如同沒頭蒼蠅般亂竄,卻不知道奪取武器,反抗殺戮,那武勇些的,只是四處亂竄,擠開比自己瘦弱的同胞,尋找安全的地方躲避,那些更加孱弱的,竟直接坐臥原地,不管是漢軍的火槍襲來,還是滿人的大刀臨頭,竟自端坐不動,就這麼全無反抗的默然死去,便是連慘叫聲,亦是那麼軟弱無力。
他眼角慢慢流下淚水,雙手將馬韁繩緊緊勒住,手心的指甲直刺入肉,幾滴殷紅的血珠慢慢流將下來,想了一會又緩緩搖頭,喃喃自語道:
「這不是天地不仁,這實在是咎由自取!關外之人號稱勇悍,實則早早歸順了異族,有奶便是娘。揚州屠城,八十萬漢人被屠,有幾個敢抗?都指望刀子落在別人頭上,便是眼見親朋兄長被殺,亦是不敢發一言,更別提衝上前去抗擊,待刀子落在自己頭上,又如何指望別人相助於己!如此這般,一直待全城被屠盡而終。到了後世,居然還有子孫後人指責是史可法反抗才導致屠城,當真是鮮廉寡恥之極!」
他靜靜騎於馬上,四周天色漸暗,城池內外卻仍是殺聲震天,被驅趕向前的漢人終究無法衝亂漢軍的陣腳,不但沒有衝至城外,反而已在漢軍的前衝下被逼開城角,此時不但整個城頭被漢軍占領,便是城角之下火槍和弓箭的射程之內,再也沒有滿人存身之處。那些殘餘僥倖未死的漢人因見身後滿人漸少,前方的黑衣攻城軍隊又十分凶狠,各人早就放棄了衝出城外逃生的打算,拚了命地向後方逃去,待夜色降臨,八旗兵已無法控制局面,只得放任所有的漢人逃出生天,護衛著滿人老弱,慢慢後撤。
上萬支火槍最後一次擊發,槍口迸發的亮光雖弱,卻匯聚成了一片片微弱的亮光,整個瀋陽西城方向,漢人早就逃得乾淨,便是滿人旗兵,亦是蹤影不見,槍聲漸漸稀落下去,各級將軍喝令軍士靠著城牆內外戒備,自晨至晚,戰事打了一天,漢軍在付出近三千士兵陣亡,重傷輕傷者八千餘人的代價之後,擊殺了過半正規的八旗駐軍,還有數千臨時徵召武裝的旗民亦陳屍於城下。瀋陽全城被破,也只是時間罷了。
張偉已登上城頭,那西門上的城門已被大炮轟塌,殘留了大半的空地,張偉踏著滿地的碎石而上,眺望遠方。
只是此時夜色已濃,他自是什麼也看不到,黑漆漆的夜色中看不到任何燈火,方圓十數里的瀋陽城此時正如同鬼域一般,令人感覺不到任何生氣的存在。
「大人,看一會兒便下來吧。此時戰線不穩,需防敵人拚命反撲。」
張傑、黃得功兩人身為最前線的指揮官,張偉駕臨前沿,萬一出了什麼岔子,兩人可是脫不了的干係。
「你們也小心過逾了,敵人此時已是疲敝之極,主力大半在這城頭被滅,又哪裡還有力量來反撲。」
他口中反駁兩人,卻是聽了兩人勸說,步下城頭,待行到城外,由親衛團團護住,見張黃二人緊隨在後,便問道:「此番攻城,咱們損傷過大,以你二人的見識,這城內之戰該當如何?」
張傑略一思忖,便揚眉答道:「大人想必是胸有成竹,這才考較咱們。依我的見識,夜晚與八旗巷戰危險,就是勝了亦是慘勝。漢軍死傷已超過預期,咱們承受不了更大的死傷了。」
張偉略一點頭,道:「不錯。若是現在命全軍入城搜剿八旗,到明日,哼,城內滿人此時一定在分頭集結,就等著我們大意衝入。我人數雖多,到底肉搏實力不如滿人,殺敵一萬自損八千的蠢事,我此番攻城時已幹了一次,再也不能犯這個錯了!」
目視張傑,道:「繼續說!」
「以屬下的見識,待明日天明,將火炮營的輕型火炮盡數推入城內,漢軍以火槍配火炮,逐街轟炸清除敵人,萬騎射手在後護衛,遇敵前衝則以火槍配合弓箭驅敵,決不能再和敵兵肉搏了。」
「這不成。你說的戰馬固然是對,可惜耗時太多。今早張瑞派人來報,已發現遼陽廣寧一帶有零星敵兵過來,可能是先期的偵騎。漢軍攻城損耗太大,野戰咱們固然不怕敵軍,只是又要多加死傷。按你的打法,沒有幾天時間瀋陽大局不定,我們不能早些後撤,這不成的!」
張傑咬牙道:「那麼……唯今之計,只能縱火焚城了!」
張偉眼皮一跳,卻是不露聲色,轉臉又問黃得功:「你說說看,該當如何?」
「末將贊同張傑將軍的意思,大人若是想少折損士兵,又能快速定城,只能先行縱火,用大火燒得城內敵人避無可避……只是這樣必然有大量百姓死難,太傷天和了。」
張偉輕輕咬一下嘴唇,道:「天大的罪過,我一個人來擔當。城內百姓當此亂世,唯有自求多福吧。」
說罷令道:「契力何必,你去準備桐油布條等燃火物品,製成火箭,現在是西北風向,你帶著萬騎去東門處點燃火箭,向城內射箭縱火!」
「是!」
「林興珠,顧振,曹變蛟,你們各帶著自己的本部兵馬,由南門、北門處用火把放火,不可深入,只需將火頭點起,任它燒!」
「末將等遵令!」
「張傑、黃得功,一會兒火起,將各城城門打開,百姓若是向外逃的,指定地點集結,不聽命令的,可當場擊殺,決不能讓滿人貴戚混在百姓中逃了。」
「末將遵令!」
他下完命令後,便騎馬回營休息,待他用完晚飯出得大帳,卻見周全斌等人立於帳外侍候,他先是不理會諸將。只放眼向城內看去,已可見瀋陽東門處火光沖天而起。
因是萬騎用火箭射出放火,是故東門處燃燒面積最大最早,再加上當時的民居大半是木板和麥草搭建而成,除了富貴人家,哪有那麼多青磚瓦房,這沾了桐油的火箭一落到那些普通民居之上,立時火借風勢,燃將起來。
開始時尚有不怕死的百姓拚死救火,待大火成片燒了起來,所有人皆知無法,那要財不要命的,便拚命衝進火場搶救財物,多有被大火燒死,或是被煙熏暈過去,不知不覺間死於大火之內。稍有些頭腦的,立時攜老扶幼,拚了命地向城門處跑,知道這大火必是攻城軍隊所放,哪裡還敢耽擱。
靠近城門處的眾百姓因起火較早,倒是跑出來不少,待張偉此時看到大火將夜空照亮,數十米高的火焰在空中衝騰翻滾,整個東門附近已經站不住人,趕往東門逃生的眾百姓無法,又只得原路折回,此時南門北門西門俱已起火,好在此時火勢不大,城內百姓尚是絡繹不絕的向城外逃生。
此時因城內動靜太大,張偉身處之地雖離城較遠,卻仍可聽到城內百姓亂紛紛逃難的腳步聲,哭喊聲,那大火燃燒木料時的劈哩啪啦聲,又彷彿可聽到無數人臨終時的咒罵……嘆一口氣,向周全斌道:「全斌,此事你覺得如何?」
周全斌淡然答道:「這也是沒法子的事。若是大人中規中矩的令漢軍入城尋敵巷戰,那全斌必然是要勸諫的。咱們是拖不起,也損失不起了。大人這般的舉措,全斌以為很對。」
「甚好,那咱們就靜待天明吧。」
一群南人將軍就這麼靜靜地站立於土坡之上,看著那城內情形。
這一夜間大火燒個不停,無數城內百姓死於火災,皇太極父子經營十數年的繁華盛京,便在這一場大火中煙消雲散。
待第二日正午,大火漸息,漢軍將城池團團圍住,除了留下必要人手看管城內僥倖逃出的眾百姓外,全軍由各城門魚貫而入,只見各處皆是殘垣斷壁,仍有零星的小火不住燃燒,偶有大難不死逃過火災的滿人,也是瞬息便被擊斃。一直待攻入後金汗宮附近,因此地甚少民居,大火早早便被隔斷,城內未死的滿人和八旗兵士盡皆逃難至此,待漢軍殺到,因地勢空曠,昨晚擋住了大火的宮城,正好便於火器犀利的漢軍強攻,那些滿人縱是拚命反抗,奈何根本無法近身。待漢軍的火炮推到,幾輪炮轟過後,滿人的有組織抵抗便告停歇,紛紛四散而逃。
待天明後,張偉下令收拾殘兵,接納流民,傳諭全營不得濫殺,將投降的滿人全數歸攏一處,不使生亂。總待將來回台灣時,將這些降人一併帶走,藉以削弱滿人實力。
濟爾哈朗的貝勒府離汗宮頗近,昨夜大火時,他便知道此番再無法阻擋漢軍入城,心灰意冷之下,立時回府屠盡了自己的妻兒老小,又一把火將貝勒府燒毀,這才帶著親兵入汗宮守備。
到得宮中之後,將心一橫,命令屬下親兵入得後宮,將躲藏在宮內的所有宮娥妃嬪盡數殺死,以防這些大汗的禁臠被他人染指。
他立於汗宮正殿十王亭外的大道之上,靜待入宮殺戮的親兵前來回報,他只穿了一件青色箭衣,背負弓箭,手持樸刀,只等著宮內事了,便親自帶兵抵擋漢軍的進攻。
「貝勒爺,宮內所有的人都殺光了,一個也沒有留下。」
他派去的擺牙喇親衛首領回來稟報,濟爾哈朗轉身一看,只看他殺得全身是血,頭上、辮髮上,亦是染滿了殷紅的鮮血,濟爾哈朗略一點頭,便待領著他前去汗宮之外抵敵。
卻聽那親兵首領又道:「貝勒爺,只是我四處搜尋,沒有找到宸妃和永福宮的莊妃。」
濟爾哈朗吃了一驚,問道:「她二人最得大汗的恩寵,怎地不肯死難,私自出宮逃跑了麼?」
「聽宮內人說,昨日大戰,宸妃親帶著宮內使喚人前往西門,幫著搬運箭矢等物,因宸妃娘娘甚得大汗愛重,宮內守衛並不敢阻攔。城破之後,原本是要護送宸妃和莊妃姑侄回宮,後來貝勒下令驅趕漢民,一時間混亂不堪,失了兩位娘娘的下落,如今,再也無法尋找了。」
濟爾哈朗點頭道:「是了,昨日我也曾看到宸妃在戰場上幫忙。唉,她一個女子,居然落到如此田地,實在是我的恥羞。是以我沒有前去問候,也沒有派人去保護她們,我真是該死。想來她們昨日已死在亂兵之中,為大汗盡忠盡節了。」慘笑兩聲,仰天長笑道:「婦人女子尚且如此,難道咱們反倒不如她們?走吧,只有戰死的滿人,沒有投降的滿人!」
待漢軍以火炮轟擊汗宮附近的滿人,濟爾哈朗、德格類、杜度等貝勒貝子皆都當場戰死,范文程、李永芳逃逸不知下落。城內所有的在籍八旗,除了前日戰死,或是死於火災的,亦是盡皆死難於汗宮附近。偶爾有逃竄至他處躲避的,亦被屠城的漢軍發現殺死,便是有不少漢民,死於殺紅了眼的漢軍槍下。
待傍晚時分,大局已定,城內漢軍諸將恭請張偉入城時,遍地的屍體和血跡阻塞了道路,張偉一邊前行,一邊待前面的開路漢軍打掃街面,此時的瀋陽城內,除了漢軍之外,再無人蹤可見。
張偉一路到得後金汗宮之外,想起去年來時此地一片繁盛景象,忍不住低頭嘆一口氣,戰爭的破壞當真是太大了。回想中國歷史,歷朝歷代均是大修宮殿,漢宮毀於董卓,到隋唐之際重修長安,那唐宮的後花園中,便留有漢朝的未央宮。待黃巢朱溫又毀長安,連同漢宮殘跡在內,整個繁華的長安城亦只能留存於史書之中。
中國人對焚毀前朝建築興趣濃厚之極,幾千年的歷史下來,只留存了北京故宮一座,當真是令人可嗟可嘆。只是張偉此番破壞,卻是情不得已,此番不但要在後金的財力物力,還有人力儲備上給予皇太極以致命重擊。還要在氣勢上給後金國一記重擊,令其在覬覦明朝內地財富時,心理上始終顧忌來自海上身後的襲擊。再加上盛京被毀,十餘年積累的財富大量流失,軍心士氣必然受到重創,就這一點而言,可比什麼都令皇太極難受吧。
他一路低頭想來,已是縱馬騎入十王亭官道,一直向上,那馬越過低矮的宮門台階,直入勤政殿大殿之內。此時的後金雖然禁令不嚴,多有貝勒騎馬入宮的,不像後世,縱是親王大臣,沒有受賞「紫禁城騎馬」的特權,是不可以騎馬入宮門半步的。縱使如此,像張偉這樣騎著高頭大馬橫衝直撞的情形,亦是對整個後金國帝國尊嚴的踐踏。
待入殿之後,張偉方醒悟過來,又掉轉馬頭,巡視一番,見有不少漢軍官兵提桶潑水救火,原來是守護汗宮的八旗兵眼見抵敵不住,便縱火焚燒汗宮,待漢軍衝入,大火即將燃起,幸得宮內水井甚多,漢軍拚力搶救,方將大火控制。
「張鼐,命他們不必救火了,只需將餘火防住,令其餘人等入宮搬運財物典籍,待東西搬出來後,再加上幾把火,把這汗宮燒毀。」
張鼐點頭應了,自去依張偉吩咐安排屬下分頭行事,數千名漢軍聽命入宮,將後金國十餘年來積累的財富搬運而出。金、銀、絲帛、東珠、玄狐皮、古董、圭、如意,乃至後金文書典籍,漢軍官兵不住地進出搜尋,將整個汗宮搜刮得如同水洗一般乾淨,方才住手。
張偉卻不管不顧,只是騎馬在這後金後宮中四處查看,見宮中女子全數被砍死在地,料想是旗兵臨敗前瘋狂殺戮,不使這些大汗的女人落入敵手,張偉心中不屑一顧,心道:「這些滿蒙女子,老子可是吃不消。」
此時的後金國尚且不允許與漢人聯姻,那滿蒙女人甚少洗澡,以當時的條件,便是入了宮也是無法與入關後相比,滿蒙之人又性喜喝馬奶、羊奶,身上皆有此類腥味,以張偉之尊榮,又怎能受得了這些。是以心中菲薄一番,對這宮內諸嬪妃一事漠不關心,準備再巡視一番,便可出宮離去。
他此時正在後宮一處小宮殿前盤桓,因見此處與其他後宮宮殿不同,雖是不大,佈置的卻是別致異常,諸多物件家俱,皆與內地豪富之家的內室相同,與其他後宮嬪妃居室的粗疏不同,可看出這宮中的主人心思十分細膩。
又見宮內暖閣內有一盤下到殘局的象棋,張偉素喜象棋,當年閒暇無事時便拖著何斌、陳永華等人對奕,這幾年他越發忙碌,棋亦沒空下了。此時偶見棋局在前,便坐將下來,研究一番。
那紅棋顯是位女子所執,佈局落子都極精巧,卻嫌其綿弱無力,張偉略看幾眼,便失了興趣,又去看那黑棋的佈子。黑棋卻是比紅棋凶橫許多,落子佈局大殺大伐,即便是要失子,也是一副魚死網破、與敵共亡的勁頭,只是黑棋顯是學棋的時間不長,雖是進攻凶猛,卻已有了數處漏洞,這棋若是下將下去,只怕是敗多勝少。
張偉心中默默算了半晌的棋路,終覺難以扳回,心中不樂,便抬手招來身邊親衛,問道:「這宮裏尚有活人麼?」
「回大人的話,旗兵俱已戰死,便是宮內女人們,也都讓他們給殺了。除了幾個命大沒死的蘇拉雜役,再也沒有活人了。便是那幾個沒死的,也都是出氣多,進氣少了。」
「快將人抬來!」
待親衛將那幾個快斷氣的蘇拉雜役抬來,張偉急聲問道:「你們說,這裏是誰的居處?」
「軍爺……饒命……」
「誰要你的命了,你快說,說了我命人給你醫治!」
有一蘇拉傷勢較輕,勉強抬起身子四處一看,卻又因起身動靜過大,忍不住咳了半天,方才向張偉答道:「軍爺,這是永福宮,是莊妃的居處。」
張偉唔了一聲,負手歪頭略想一想,便已知道這莊妃便是他身處現代之時,電視中形象美麗聰慧,先是扶幼子福臨即位,以感情籠絡住了一世梟雄多爾袞,後來又保幼孫康熙,在誅鰲拜、平三藩等大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被人尊稱為「兩朝興國太后」的莊妃,大玉兒。
因向身邊親兵吩咐道:「抬著這幾人,在宮內搜尋一下,看看有沒有莊妃的遺體。」
莊妃生於一六一三年,十三歲時便從科爾沁部出嫁,嫁給了姑父皇太極,待一六四三年皇太極病故,她也不過三十出頭,此時年方十六,若是在張偉的那個時代,只不過是個普通的女高中生。
當時後金為了與蒙古的科爾沁部加強聯盟關係,自努爾哈赤起,整個後金汗國不住地迎娶科部的公主,又將後金的格格下嫁給科部的台吉,這種政治聯姻只是為了政治利益,又哪裡管顧女人的心思。別說是十三歲,便是十一二歲,亦有出巡聯姻的。
想到此處,又想到家中那美麗聰慧的柳如是,張偉搖一搖頭,終究無法苟同古人的這種做法。
待搜尋的親兵回來,卻是四處也尋不到莊妃的屍體,便是那宸妃亦是蹤影不見,又得知這姑侄二人昨日曾上西門協守,張偉嘆一口氣,知道很難再找到這位歷史上呼風喚雨的女人,當下意興蕭索,騎馬離宮而去。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新大明王朝(4):威震南洋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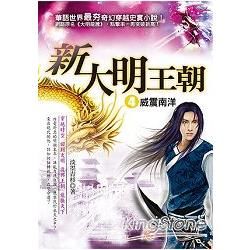 |
新大明王朝(04)威震南洋【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淡墨青杉 出版社: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1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288頁/15*21mcm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新大明王朝(4):威震南洋
一個成天只沉迷於電玩遊戲的現代宅男,怎會莫名其妙的跑到了明朝末年?
外星人也會凸槌?原是想去三國一展身手的說,沒想到竟陰錯陽差回到明末,這下可糗了,他該怎麼辦?
◎華語世界最夯奇幻穿越史實小說!網路原名《大明龍騰》,點擊率一再突破新高!
◎亂世天下,新人備出;扭轉乾坤,大明龍騰!紛亂不堪的明末王朝,正是他大展身手的最佳時機;百年不遇的天下之爭,更是他責無旁貸的最後使命!
◎打破傳統宮鬥劇新奇幻穿越小說以真實歷史為背景,明末台灣發展為主軸,穿插歷史人物為陪襯,輕鬆詼諧的對白,絕無冷場的劇情,一部讓你看了熱血沸騰的東方奇幻歷史小說!!
穿越時空 回到大明
復興王朝 龍騰天下
內憂外患的明朝末年,誰能力挽狂瀾,救黎民於水火之中?來自現代的他,該如何扭轉乾坤,改變命運?
大明末年,天下大亂。
農民起義軍在李自成的率領下攻城掠地,所向披靡。
與此同時,關外一代人傑皇太極親率十萬精銳八旗騎兵,隨時準備入關,奪取大明天下。
台灣在張偉的勵精圖治之下,竟然成為制度先進、建設完備之地;不僅讓人耳目一新,相較於當時明廷的百廢待舉、一蹶不振,此時的台灣彷如天堂,更成為賢臣名士避居的世外桃源。而張偉也決定大舉擴展自己的勢力,向皇太極發下戰帖……
章節試閱
張偉已縱騎接近城池,親眼目睹這一幕慘劇,只覺眼前鮮紅一片,盡是那些垂死掙扎卻不知道生路何在的百姓,看著他們如同沒頭蒼蠅般亂竄,卻不知道奪取武器,反抗殺戮,那武勇些的,只是四處亂竄,擠開比自己瘦弱的同胞,尋找安全的地方躲避,那些更加孱弱的,竟直接坐臥原地,不管是漢軍的火槍襲來,還是滿人的大刀臨頭,竟自端坐不動,就這麼全無反抗的默然死去,便是連慘叫聲,亦是那麼軟弱無力。
他眼角慢慢流下淚水,雙手將馬韁繩緊緊勒住,手心的指甲直刺入肉,幾滴殷紅的血珠慢慢流將下來,想了一會又緩緩搖頭,喃喃自語道:
「這不...
他眼角慢慢流下淚水,雙手將馬韁繩緊緊勒住,手心的指甲直刺入肉,幾滴殷紅的血珠慢慢流將下來,想了一會又緩緩搖頭,喃喃自語道:
「這不...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大破沉城
第二章 血腥屠殺
第三章 撤離遼東
第四章 返回台灣
第五章 滿清立國
第六章 朝堂之爭
第七章 圖謀呂宋
第八章 兵臨呂宋
第九章 占領呂宋
第十章 荷蘭來使
第十一章 爪哇之行
第十二章 南洋旺族
第十三章 再見伊人
第十四章 大婚之事
第十五章 興辦太學
第二章 血腥屠殺
第三章 撤離遼東
第四章 返回台灣
第五章 滿清立國
第六章 朝堂之爭
第七章 圖謀呂宋
第八章 兵臨呂宋
第九章 占領呂宋
第十章 荷蘭來使
第十一章 爪哇之行
第十二章 南洋旺族
第十三章 再見伊人
第十四章 大婚之事
第十五章 興辦太學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淡墨青杉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10 ISBN/ISSN:978986352033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歷史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