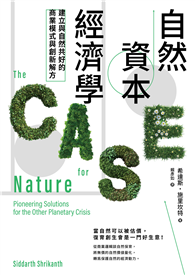◎溥儀三歲登基,三年退位,卻是全世界最為熟知的一位中國皇帝
他,是唯一為自己作傳的皇帝
他,是唯一在亡國後還能居住深宮的皇帝
他,是結束了中國四千餘年帝制的末代皇帝
他,是唯一為自己作傳的皇帝
他,是唯一在亡國後還能居住深宮的皇帝
他,是結束了中國四千餘年帝制的末代皇帝
◎著名歷史小說家高陽作序
◎獲九項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末代皇帝」原著
◎獲九項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末代皇帝」原著
◎2009年末代皇帝自傳(下)跟2014年末代皇帝自傳【新修版】(下)內容是相同的。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溥儀成為偽滿洲國的執政者,他不知道該對自己的命運高興,還是憂愁。他的思想既紊亂且矛盾。然而,他私心幻想,也許「執政」是一條通往「皇帝寶座」的階梯。為表示決心,他將居住樓命名為「緝熙」,係取自《詩經:大雅.文王》「於緝熙敬止」句。更根據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以「勤民」命名他的辦公樓。
從此,他每日早起,進辦公室「辦公」,直到天黑,才從「勤民樓」回到「緝熙樓」。
為了重新奪回曾經屬於自己的一切,溥儀一面聽從著關東軍的指揮,以求憑借,一面「宵衣旰食」,想把「元首」的職權使用起來。
然而,這樣的努力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為,溥儀根本無公事可辦,他的「執政」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並不在他手裏……
](https://img.findprice.com.tw/book/97898635204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