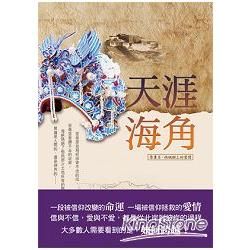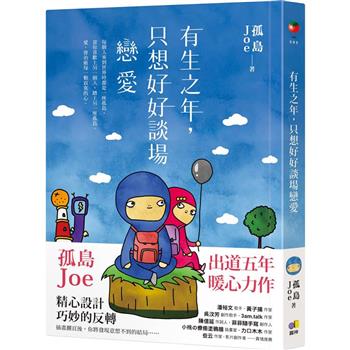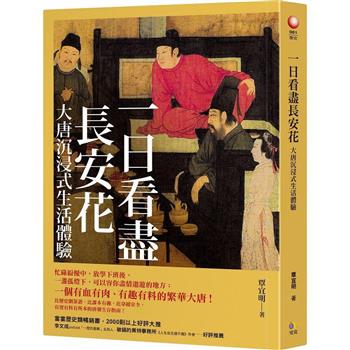一段被信仰改變的命運
一場被信仰拯救的愛情
愛情就是一場守望,就像雪山守望白雲,峽谷守望江水。
白雲有聚有散,江水有枯有漲,飄走的白雲終要回來,乾涸的江水終要豐滿。
因為愛情就是一筆高利貸,永遠都需要用生命去償還。
扎西嘉措是個走南闖北的行吟詩人,神界的傳說被他唱得活靈活現,大地上土司間的爭戰被他演繹得轟轟烈烈,天上飛過一隻鳥兒也會引來他的歌聲,山崗上凋零的花兒也會被他的歌滋潤得二度開放。更不用說人間恩恩怨怨的愛情,更被他唱得如泣如訴,催人淚下。
只是,如此無憂無慮的生活,卻在遇見央金瑪之後改變了。
他們相遇,相愛,卻又因為環境阻隔而分開。
而另一方面,格桑多吉這個半途殺出的男人,也在默默守護央金瑪……
我相信我還活在瑪麗亞的夢裏,儘管那邊的人們肯定都認為我死了,儘管有些時候我也認為自己死了。
我在夢裏的呼喚和懺悔,總是只有夢的影子回應。這個影子就像漂浮在大霧瀰漫中的河谷對岸的村莊,偶爾一閃現,就被濃霧嚴嚴實實地遮蓋起來了。這個村莊裏有我的家,有像瑪麗亞一樣溫暖的火塘。我要穿透這濃霧回家,不是像跨過一條河谷那麼簡單,而是要渡過一條台灣海峽。過去我們過瀾滄江峽谷,只要有一條橫跨兩岸的溜索就行了;現在台灣海峽又寬又深,兩岸還有上百萬的軍隊對峙。不要說我,就是一隻鷹,也不可能飛過去。鷹飛不過去,信也飛不過去。我給瑪麗亞寫了多少封信,已經記不清了。從印度的達普難民營,到台灣這個被海水包圍的海島,我都在寫一封封無法寄出的信。我的信有的長,有的短,有的不是信,是思念,是詩行,是夢話;
有的寫好後被我撕了,燒了。因為望著它們,就像望著歸不去的故鄉。
重點:
望著那些寫好卻寄不出的信,就像望著歸不去的故鄉。
海峽隔絕了他與那片土地所有的聯繫,無論是人間的,還是神界的……
一段被信仰改變的命運
一場被信仰拯救的愛情
信與不信,愛與不愛,都是從此岸到彼岸的過程。
大多數人需要看到的是:如何跨越!
在《天涯海角》中,作者試圖用文學的形式來詮釋一段被信仰改變的命運和被信仰拯救的愛情,以及在戰亂中對一場曠世愛情的堅貞守望和自我救贖。在時間跨度上從上世紀抗戰時期到本世紀初,空間跨度上展現了這段愛情在西藏、大陸和台灣所經歷的萬般磨難。
作者簡介:
范穩
著名作家。被譽為「大陸十大作家」之一,與賈平凹、易中天等人齊名。
為當前反映西南邊民生活著有盛名的作家。曾出版過長篇小說《清官海瑞》等,並在雜誌上發表多篇中、短篇小說。若干年來,一直從事滇、藏地區的文化研究,並嘗試著將其成果運用於文學創作,曾撰寫過記述地域文化的圖書《茫茫古道:揮之不去的歷史背影》、《高黎貢:人類的雙面書架》等著作、文章,以及近年掀起熱潮的《藏地三部曲》前兩部《百年靈域》、《大地心燈》。
章節試閱
他是一個俊朗清瘦的青年,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臉很長,像副馬臉,但跟他俊俏的五官、棕黃色的細膩皮膚相配起來看,你只會將他視為一匹草原上的駿馬;再加上他那雙彷彿會說話的濕潤的眼睛,若是看著仇家,仇人會被感動;若是望著情人,女人將被融化。不過按藏族人的觀相術看,這種人一生會經歷無數的苦難,尤其是愛情。眼睛濕潤,看上去秋波蕩漾,情意脈脈,但藏族人認為這是一雙淚眼,是終生貧困和愛情注定失敗的預兆。
一個權傾一方的土司和一個流浪藝人的因緣,來自於半年前的一次邂逅,這讓雙方的命運因此改變。那天瀾滄江峽谷下游的大土司康菩.仲薩路過阿墩子縣城的一家小酒館,聽見一陣悠揚的扎年琴聲飄出來,自小喜歡歌舞的康菩土司,還沒有聽見過如此流暢自如的琴聲,就信步進去要了碗酒,坐在一邊靜靜地聽。一碗酒喝完,康菩土司走到那個說唱藝人身邊說:
「收起你的琴,跟我走。我管你一個月的吃喝。」
說唱藝人眼睛都懶得擡一下,只是低頭調自己的琴弦,「我的吃喝,有我的歌聲管。」他滿不在乎地說。
康菩土司身後的管家次仁不輕不重地打了他一馬鞭,「黑骨頭賤人,擡起你的狗頭來!看看是誰在跟你說話,跪下!」
那個說唱藝人懶洋洋地擡起頭來,看見了他面前身著貴族服裝的土司老爺,他壯實得像一頭犛牛,威武得似一頭雄獅;說唱藝人同時還望見了酒館門口簇擁著一大群斜背長槍、手牽駿馬的衛隊。
「我是一名在大地上流浪的詩人,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是我的灌頂上師,愛情是我的人生詩行,姑娘們的眼光照亮我腳下的路。我的歌唱給雪山聽,唱給聖湖聽,唱給放牧人聽,唱給酒館裏只喝得起一碗酒的人聽,還唱給美麗的姑娘們聽,我不給貴族老爺唱歌。窮人有窮人的尊嚴,乞丐有乞丐的自由,而一個流浪詩人,大地上到處都有朋友和愛情。」
說唱藝人傲慢地說,次仁又舉起了馬鞭。
康菩土司擺擺手,對說唱藝人說:「把你的琴拿來,我唱一支歌給你聽。」
說唱藝人猶豫了一下,還是把手裏的六弦扎年琴遞給了康菩土司。土司那天不知是心情好,還是這個流浪漢的歌聲激起了他年輕時的美好回憶,他調撥了一下琴弦,唱了一首古老的情歌:
我和東邊的山說話,
西邊的山懷疑;
我和南邊的山說話,
北邊的山懷疑。
一座座多心的山啊,
叫我怎麼對付你。
「怎麼樣?」康菩土司把琴遞還給說唱藝人。這個傢伙沒想到一個土司也會唱這種歌謠,而且琴還彈得這樣好。他收起六弦琴、要錢的木碗、以及身邊的背囊,「嘿嘿,老爺身邊的姑娘太多了。」他的嘴依然討厭。
康菩土司自負地說:「比你的歌多一點。」
說唱藝人更自負,他說:「你要知道,我的每一支歌後面,都有一顆姑娘的心。」
康菩土司不當回事的說:「那就讓我們看看,有哪個姑娘會被你的歌聲征服。」
流浪詩人挑戰似的站了起來,「你永遠不會知道我在歌聲中傳達的愛情。」
就這樣,說唱藝人扎西嘉措來到了康菩土司的大宅。這個走南闖北的行吟詩人,去過聖城拉薩,到過後藏日喀則,夏天在藏北草原的牧場上與牧羊姑娘用歌聲調情,冬天在藏東溫暖的峽谷和打柴的少婦躲在灌木叢裏打滾。而春秋兩季,他要麼在某個姑娘溫柔的被窩裏做著愛情的美夢,要麼在朝聖的路上顛沛流離,邊走邊唱。神界的傳說被他唱得活靈活現,大地上土司間的爭戰被他演繹得轟轟烈烈,天上飛過一隻鳥兒也會引來他的歌聲,山崗上凋零的花兒也會被他的歌滋潤得二度開放。更不用說人間恩恩怨怨的愛情,更被他唱得如泣如訴,催人淚下。
他總是那麼機敏、俏皮,總是顯得那麼多情、聰慧。他有一個溫柔的靈魂,浪漫的心。主動委身在他身下的姑娘,他要看到天上的星星,才一個一個地想得起來。這讓他喜歡這種浪遊四方的生活,從不把富貴利祿放在眼裏。他還不到二十歲,除了隨處播撒的愛,什麼都不缺,什麼也不在乎。他本是一個劍膽琴心的行吟詩人,遊走在一個浪漫純真的時代,生活得怎麼樣並不重要,愛得如何才是關鍵。他相信,只要行走在大地,愛情就像山崗上到處生長的樹,就像牧場隨風飄揚的情歌,一個說唱神界傳說與人間萬象、歌頌生活與愛情的流浪詩人,總會與人生中的真愛不期而遇。姑娘們脈脈含情的眼光為他指引著愛情的方向。
就像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會在康菩土司森嚴的大宅裏,看到了他願意為之去守候一生的愛情。
這人就是康菩土司的小姨妹央金瑪,每當聽扎西嘉措說唱的時候,她便緊挨在她姐姐卓瑪拉初旁邊,像一隻依偎在母羊身邊溫順的小羊羔,而她的眼睛卻總像還深陷在夢的深處,在那個說唱藝人俊俏的臉上飄來飄去。她不像其他人那樣神情專注地聽扎西嘉措的唱詞、琴聲,時而開懷大笑,時而喟然長歎。她不知不覺就讓說唱藝人的歌聲如寒冬過後的第一縷春風,吹拂她寂寞了十七年的心;又似甜美的夢長上了翅膀,帶著她的心兒遨遊在愛情的樂園。這讓她常常聽得面紅耳赤,心神迷亂。有一天她甚至在那個傢伙越唱越露骨的唱詞中,眼睛不看他靈巧撥弦的手指,也不看他翻飛踢踏的舞步,而是飄進春夢深處,往他的褲襠那裏看。就像一個邪惡的神魔,人們總在傳說他的故事,說一回便心驚肉跳,但又忍不住想再說第二遍。
大約從聽到扎西嘉措的第一支歌後,央金瑪晚上就睡不好覺了。
十七歲的央金瑪那時並不知道,她一生的命運總是和錯位了的愛情分不開,這種愛情是最幸福的,但在人間卻總是不合時宜,它屬於天堂裏的愛。然而,情場高手扎西嘉措怎麼會不知道這個特殊聽眾的心思,又怎麼能輕易放過央金瑪的美?在他周遊雪域高原的歲月裏,他的琴聲飄到哪裏,姑娘們的眼波就跟到哪裏。他可以在一個姑娘看他的第一眼時起,就作出決定,今晚要不要鑽進她的帳篷。
但央金瑪可不一般,她的眼波像聖湖裏的波瀾,遙遠而神秘,深邃又迷濛。從第一眼看見她,扎西嘉措就在心裏驚呼:原來世界上雪山女神真的存在。她典雅、俏麗、清純、明澈,正是含苞欲放的雪蓮,冰凌尖閃耀七彩光芒的水珠,花蕊上晶瑩剔透的甘露。更讓這個多情浪子驚歎的是她的那雙總是迷迷濛濛的眼睛,彷彿她的夢遊並不僅屬於她自己,還要挑逗你跟隨她一同墜入甜美的愛之夢。
在扎西嘉措說唱表演時,他不用看她那邊,就知道哪段旋律會讓小姐芳心迷亂,哪段歌詞會深入少女的繾綣春夢。他在大地的舞臺上早已閱人無數,知道什麼樣的歌詞,會攪動起一池春水;什麼樣的曲調,會拉近兩顆年輕浪漫的心。這朵含苞欲放的花兒,必將在他愛的春風化雨中燦然開放。
因此,扎西嘉措縱然久經風月,也還是琴弦已亂,心如樹上的猴子了。
當初康菩土司說要管他一個月的吃喝時,他想:我扎西嘉措什麼人啊,大地就是我的家,天下到處都有美酒和姑娘,誰在乎你一個土司大宅,待上半個月算我看得起你。可是一個月過去了,他說唱的神界故事還沒完沒了;三個月過去了,雪域大地上還籠罩著黑暗;半年時間了,藏族人的祖先還沒有被創造出來。他唱開天闢地,任意加進去些神靈們的愛情故事;他唱神魔大戰,神靈和女魔竟然相愛成了一家,連蓮花生大師最後不是靠無上的法力收服了女魔,而是以愛情感化了她。土司家的聽眾開初還紛紛抗議,說這個仲巴唱的跟過去聽到的不一樣。可是他們又不得不承認他唱得動聽,唱得扣人心弦。最後就由了他胡謅,直到唱得火塘邊的康菩土司想睡覺了,吸口鼻煙打個噴嚏,演出便到此結束。
那天晚上他給土司一家人唱創世傳說,或者說,他心中只是唱給一個人聽。因此他唱著唱著就讓太陽和月亮相戀起來,但是他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太陽永遠也追逐不到月亮。他多情的心忽然就被一股固執的憂傷瀰漫了,那時他還不知道這種憂傷會陪伴他終生。土司家眷們的起哄和康菩土司那個噴嚏救了他的場,不然他真不知後面的唱詞該怎麼編排下去了。
散場了,人們各自回自己的臥房。扎西嘉措和下人們住在馬廄旁邊的一排小房子裏,康菩土司住大宅主樓的二層,剛才說唱的地方也在二層的大廳,央金瑪和幾個女眷住三層。扎西嘉措垂手躬身立在一邊,讓主子們先走。扎西嘉措知道,說唱歌謠的時候,他是客廳中的英雄,受眾人仰視,現在,他不過是土司家豢養的一條狗,也許連狗還不如呢。
他看見央金瑪在女僕德吉的陪伴下從他身邊昂頭而過。他在心裏說,我數到三,她一定會轉過頭來。
他才數到二,央金瑪忽然扭頭對身後的德吉說:「我的手爐呢?」她尚在夢遊的眼睛飛快地往扎西嘉措睃了一眼,像一根打過來的羊鞭,讓扎西嘉措的心頭微微一顫。
德吉舉舉手中那個精緻的手爐,討好地說:「在我手上呢,小姐。」
扎西嘉措看見央金瑪轉過頭去了,心中的感激還沒有歎完,那高貴的小姐又轉過身,衝著扎西嘉措說:「哎,你還沒有唱太陽什麼時候愛上月亮的呢?」
扎西嘉措一下慌了神,忙說:「從天神點燃了太陽的光芒那一天起……」
「是哪一天呢?」央金瑪認真地問,目光直逼扎西嘉措,這次扎過來的是兩把溫柔的刀子。
「是……是很早很早以前……」扎西嘉措感到自己受傷了。
「唉唷,走吧,睡覺去吧。」從她身後過來的大夫人卓瑪拉初推著央金瑪說,「別問啦,這個傢伙心裏有一匹沒有馴服的野馬,跑到哪兒唱到哪兒。明天你別再一會兒天上一會兒地下了,你得給我們唱藏族人從哪裏來的。」
「你最好唱最近的事兒,漢地那邊漢人和日本人打仗打得怎麼樣了?聽說洋人喇嘛又要過來傳他們的教了。這些事情你會唱嗎?」
康菩土司在客廳那頭說,他的身邊站著他的二夫人和三夫人。大夫人卓瑪拉初當然只有每天獨自上三樓了。
「是的,老爺。好的,夫人。」扎西嘉措回望康菩土司一眼,又轉過頭去追隨央金瑪的身影,但她們已經拐上了三樓的樓梯口。
回到馬廄旁的小屋,幾個馬倌要扎西嘉措給他們唱幾段,還把一罐青稞酒擺在屋子中央。他們是沒有資格到二層的廳堂聽歌的,但是今晚扎西嘉措再也無心思唱了。他推說不舒服,把他們的酒罐提到門外,轟他們走了。
他躺在火塘邊的卡墊上,回想這些日子以來央金瑪對他越來越露骨的表白。幾天前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央金瑪騎馬回來,見他蹲在門口用牛筋線縫補靴子。就問,你還會做這個啊?他快樂地說,一個不會補靴子的傢伙,當不成一個流浪漢。她站在那裏不走,似乎想和他暢談,又沒有一步跨進他房間的勇氣。她說,這麼破的靴子,扔掉算啦。他用歌詞一樣的話挑逗央金瑪,我的靴子是我的情人,白天它陪伴我遠行天涯,晚上我枕著它安然入睡。他看見小姐的脖子都紅了,臉轉一邊,問,扎西哥哥,你去過聖城拉薩嗎?他自豪地說,我在拉薩待過三年。三年?她驚訝的嘴像一朵豁然開放的花,眼睛裏全是夢中的幻象。你下次去拉薩帶上我啊?她竟然如此請求,讓扎西嘉措怦然心動。要是別的姑娘如此說,扎西嘉措收起琴、背上背囊就帶她走了。
有一年在藏北的牧場上,一個小頭人的女人為他的歌聲傾倒,像匹騷動的母馬一樣不斷向他釋放愛的氣息。一天晚上,這女人為他和頭人不斷斟酒,喝到後面他才發現自己碗裏的是水,而頭人碗裏卻是酒。到了晚上,頭人醉得酣然大睡,他妻子卻摸到扎西嘉措的羊毛氈裏。他們一直睡在一頂大帳篷裏,幾乎每個晚上扎西嘉措都能聽到帳篷那邊頭人女人的呻吟,現在這呻吟在他的身下真實地響起來了,讓他不斷地想自己到底醉還是沒醉。那個女人比他至少大十歲,但卻在黑暗中教會了他很多的花花活兒,把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折騰得精疲力竭。第二天女人就跟著他私奔了,說他真是一匹健壯的小公馬,她願意隨他走遍雪域大地。可是只走不到三站馬程,女人就反悔了,說一個女人的快樂不僅僅是躺在一個英俊男人的身下,還在於能擁有一大群牛羊。扎西嘉措當時告訴她,那你就跟自己的牛羊睡吧,願牠們能帶給你快樂。女人真誠地哭哭啼啼,問,那麼,你的快樂在哪裏呢?扎西嘉措回答道:在愛神那裏,我走到哪兒,愛神就跟到哪兒。愛神會引領著我自由的腳步。
扎西嘉措相信愛情是由愛神控制的,人不能抵禦愛神的眷顧。它翩然降臨,就像一片飄在你身上的雪花。那麼多的雪花從天上飄下來,為什麼獨獨這片雪花要飄向你?這就像世上好姑娘那麼多,為什麼獨獨這個姑娘要和你鑽同一頂帳篷一樣。藏族人的愛神,喇嘛們雖然不說,但扎西嘉措這樣的說唱藝人卻將他宣揚得魅力無窮,所向披靡。就像這個晚上,扎西嘉措相信一定是愛神讓他在半夜走出了自己的房間,來到了央金瑪小姐的窗戶下。他發現小姐的房間裏竟然還亮著燈,這讓他彷彿得到了某種啓示:
小姐在等我呢。
央金瑪房間的窗戶面對後院,那裏有一棵四人還合抱不住的大核桃樹,根深葉茂,年年都可以為土司家收下幾百斤核桃。據說它至少有兩百多歲了。扎西嘉措幾下就竄到了核桃樹上。那樹和小姐的窗戶大約有一丈多的距離,樹梢的一些樹葉已經掃著央金瑪的窗戶。但是窗戶上蒙著藏紙,他看不見裏面。他發現窗戶的上方好像有條縫隙,就再爬高一點,還是什麼都看不到。
他篤定窗戶裏的人在思念他,這是多年來的愛情直覺。可他該怎麼傳達給裏面他的等候呢?他拿出自己的六弦琴,一定是愛神在他出門時讓他帶上的。誰會在這夜深人靜的土司大宅聽他彈琴啊?
愛神會。
他趁著吹向窗戶的風,輕輕地彈撥了第一根弦,音符像一個飄在夜空中的精靈,悠悠蕩蕩地向央金瑪的窗戶飄去。
他側耳聽了一陣,窗戶裏沒有什麼反應。他又再溫柔地彈撥了第二根弦。他對自己說,撥完六根弦,小姐要是還不開窗,明天就走啦,離開這無情無義的土司大宅。
一般來說,能和扎西嘉措這樣的天涯浪子來一段或浪漫刺激、或淒婉纏綿的愛情,都是一些敢愛敢恨的女子。央金瑪似乎天生就是這種愛情的女主角。當年她隨自己的姐姐一同嫁到康菩家,還只是一個七歲的小姑娘,像一棵山谷裏的野杜鵑,孱弱、細小,青澀的葉子自然不能和如花似玉、正值當年的姐姐相比。十年過去,野杜鵑粲然開放,嫣紅了一條峽谷。但人們說她很野,不像貴族小姐,倒像個牧場上的姑娘。她剛會走路時就會騎馬,夏天她去高山牧場上玩耍時,草地上的花兒見了她的美也要彎腰,樹林裏的鳥兒也不敢鳴叫,因為她的歌兒也唱得著實好聽,但一般人是聽不到這驕傲的公主唱歌的。在她十五歲那年,她看見土司手下的一個頭人鞭打一個老婦人,就問頭人,她那麼大年紀了,你為什麼打她?頭人回答說,不打人我身上的骨頭老得快。央金瑪拿過鞭子,劈頭就給頭人幾鞭子,說,不打你我身上的骨頭還長不齊呢。
據說康菩土司曾經有過把這個迷人的小姨妹再娶過來做第四房老婆的想法,但眼下他還有更重要的生意,比多娶一房小妾更為重要。這年的秋天收完青稞後,瀾滄江上游的野貢土司家族就會派來迎親的隊伍,央金瑪將成為野貢土司的第三房妻子。瀾滄江峽谷的康菩土司和野貢土司兩大家族過去經常打仗,不是為草場,就是為經商。現在好了,兩家將成為親家,野貢土司承諾作為迎娶康菩家小姐的答謝,除了該送的金銀珠寶、綾羅綢緞、茶葉布疋等彩禮外,另再奉送三個草場,那是跑馬也要走一天的地盤,而且還控制著進出西藏的馬幫要道,但是野貢土司毫不吝惜。而扎西嘉措對這樁婚事卻不在意,貴族們為了利益而聯姻,跟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有什麼關係呢?
他是如此地固執堅定,又是如此地柔腸寸斷。如果央金瑪不開窗戶,他們的人生就不會這樣多災多難,他們的愛情也不會在今後漫長的守望中消耗一生。但是,央金瑪命中注定,不會去當一個土司的三姨太。
他是一個俊朗清瘦的青年,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臉很長,像副馬臉,但跟他俊俏的五官、棕黃色的細膩皮膚相配起來看,你只會將他視為一匹草原上的駿馬;再加上他那雙彷彿會說話的濕潤的眼睛,若是看著仇家,仇人會被感動;若是望著情人,女人將被融化。不過按藏族人的觀相術看,這種人一生會經歷無數的苦難,尤其是愛情。眼睛濕潤,看上去秋波蕩漾,情意脈脈,但藏族人認為這是一雙淚眼,是終生貧困和愛情注定失敗的預兆。
一個權傾一方的土司和一個流浪藝人的因緣,來自於半年前的一次邂逅,這讓雙方的命運因此改變。那天瀾滄江峽谷下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