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共同的感情與記憶(自序) 陳曉林
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從邃古時代到農業時代,從農業時代到工商時代,再從工商時代進入到如今的「後工業時代」或「資訊時代」,歲月迢遙,星移物換,人間大地已經不知變換了多少次面貌,曾經在人類歷史舞台上,迸發過光輝與熱力的無數英雄兒女、志士仁人,也都已經在滾滾而逝的歲月之流中,歸於寂靜。
然而,在茫無際涯的時間長流中,人間世一切的掙扎、吶喊、奮鬥、堅持,難道果真都沒有恆久而深長的意義可言?
穿越過時間的風暴,畢竟有許多個歷經淘煉的民族,從矇昧的遠古、漫長的中世,逐一踏入了多姿多采的現代社會,各自留下了它們在歲月之流中跋涉而過的軌跡與足印。而無論是否自覺,也無論是否自願,這些軌跡與足印,已經分別成為各大民族共同的感情與記憶,共同的眷戀與關懷。在繁忙而冷漠的現代社會中,這些共同的感情與記憶、眷戀與關懷,甚至已轉化為一個民族之中,人與人之間唯一主要的共通語言。試想:在知識分科與專業分工如此細密的現代社會裏,除了以人文情懷與人文價值來互相溝通之外,尚有何種別的途徑可循?而所謂「人文情懷」與「人文價值」,本就是奠基在人與人之間共同的感情與記憶、眷戀與關懷之上的。正因為擁有著共同的感情與記憶、眷戀與關懷,交互激濁揚清、誘引萌發的結果,現代人的心靈,才能在精確的科技成就之外,仍然不斷締造出嶄新的人文創作。
於是,當代各主要國家都極重視民族遺產的發揚,及歷史古蹟的維護。文學界對於經典作品的詮釋、史學界對於民族史實的強調、藝術界對於傳統風格的探究,以及民俗學界對於通俗資料的蒐羅,幾乎都到了鉅細靡遺的程度,足見現代人對自己民族的「根」,是何等的珍惜與重視。
這些對具體史蹟或文物所作的研究,重點在於抉發、並闡明自己民族資產中,所含藏或體現的「精緻文化」理念與價值。另一方面,由於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思想家如維科(Vico)、赫爾德(Herder)等人對「時代精神」、「民俗精神」的強調,以及二十世紀著名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對文學作品「深層結構」的挖掘,尤其心理學家容格(Jung)對「集體潛意識」的闡釋,現代人對於「通俗文化」的內涵與價值,也產生了莫大的興趣。甚至有人認為:默默流傳於鄉野民間,過去不太受到文人學者重視的「通俗文化」,才真正反映了一個民族在它多數民眾心靈中,汩汩流動著的共同的感情與記憶、共同的眷戀與關懷。
於是,在當代西方文學界,通俗文學的地位,大為提高,以往被視為不入學者之眼、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一經從新的角度重新「解讀」之後,卻可能發現其中含有不少與民族「集體潛意識」之中,多數人民的精神動向之認同或沉澱、嚮往或追慕有關的內涵。而這些內涵中,甚至不乏全人類所共通的普遍性人文情懷與人文價值,即使在二十世紀後期的如今看來,仍具有鮮明靈動的生命活力。
一個民族共同的感情與記憶,或者,一個民族的「集體潛意識」,經常表達、並保留在這個民族的神話、史詩、傳奇、述異、民謠、掌故、戲劇、舞蹈,乃至民俗行為之中。正式歷史所記載的,往往只是一個民族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思想等業績表現,是屬於「顯意識」的部分;神話、史詩與民間傳說之中,則反映了古遠歷史沉澱而成的「潛意識」,從而也恰好可以補充正式歷史的視域與層次。
一般而言,與希臘、印度及西方文明相形之下,中國較為缺少系統井然的神話與格局宏麗的史詩。然而,由於中國人的歷史意識特別明晰而強烈,所以,歷史作品常常成為承載中國人共同感情與記憶的最佳媒介。可惜的是,中國人的正史在反映民族「集體潛意識」方面,仍然有其局限。這是因為,其一:正史大抵皆出於官方修纂,較為注重體面的維護與具體的功績;其二:正史的文字大多古奧而雅馴,主要流通於博學的知識分子之間,不適合處理詼詭譎怪的民俗傳說;其三:兩千餘年以來,中國的正史累積了太多的冊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民間大眾即使想從正史中,感知中國人共同的感情與記憶,也往往有無從著手之苦。
除了司馬遷《史記》中生動的文字及活潑的思想,是一空前絕後的特例之外,中國的正史,無論如何精采,紀傳體如前後《漢書》、新舊《唐書》,編年體如《資治通鑑》、《遼金元實錄》,紀事本末體如《通鑑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著述體如《通志》、《通典》、《文獻通考》,所處理的範圍或課題大抵全是屬於中國人「顯意識」層次的事蹟,而難以深入掌握中國人「潛意識」心靈的脈動。
好在,遠溯先秦時代,中國即有長期私家撰著及稗官野史的傳統;自唐朝以後,民間講史與說書,更蔚為歷史不衰的風氣。而在這源遠流長的社會風潮中,諸如平話、講史、演義、說書與誌奇、述異等民俗文學,從口傳到筆錄、從粗獷到優美,形成了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大奇觀。這其中,尤其是以明朝羅貫中《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整個歷史演義系統,恰好在歷朝官修的正史之外,提供了一個平行對應的民間野史世界。
這些來自草野民間的文學人物,將中國人在帝王專制的重壓之下,所經歷的掙扎與吶喊,所表現的奮鬥與堅持,所懷持的嚮往與追慕,所體映的眷戀與關懷,以文學家的筆觸,吟遊者的聲調,悲愴而浪漫地傳述了下來,保留了中國人亙古以來共同的感情與記憶,也保留了中國民族的「集體潛意識」。這種歷史演義,形式上略近於西洋文學中的「浪漫傳奇」(romance)及「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el),但卻又有基本上的不同,因為中國的歷史演義,並不完全脫離歷史的事實,而自馳想像,只是往往從民間的立場,揭露了正史所掩蓋著的斑斑血淚與重重煙幕而已。
於是,誠如清代名學者俞曲園所言:「一部廿四史,衍成古今傳奇,英雄事業,兒女情懷,都付與紅牙檀板。」而在中國的鄉野民間,在中國的山陬水涯,尤其在中國的文學讀者群中,紅牙檀板所象徵的歷史演義,永遠是一種鮮活而真切的文學經驗,因為這是中國人共同感情與記憶的結晶,也因為中國人所遭遇的歷史考驗與生命愴楚,可以透過閱讀這些逼近歷史真相的文學作品,獲得一定程度的清滌與昇華。正如古希臘人可以在觀賞其悲劇名家如索福克利斯、尤里披底斯等人的悲劇傑作之時,或近代西方人可以在觀賞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演出之時,獲得清滌與昇華一樣。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上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街聽唱蔡中郎。」在古代中國,講史和說書,是一種專業技能,無論是手執紅牙檀板的演藝少女,或是胸羅千古憂苦的負鼓盲翁,其實,都是在述說著亙古以來,中國人共同的感情與記憶,中國人共同的眷戀與關懷……。
如今,雖然時代已進入二十世紀的尾聲,進入「後工業社會」的階段,極目四顧,紅牙檀板不再,負鼓盲翁已遠,可是,中國人的故事,卻仍將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去。
這些故事,刻畫了中國人在歲月之流中跋涉而過的軌跡與足印,也迴映了中國人在心靈意識中沉澱而成的情懷與價值。在萬古長空中,這樣深厚的一朝風月,可也當真咀嚼不盡。
若以司空圖《詩品》中的句子來表述,正是:「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百歲如流
周室東遷,諸侯崛起,中國歷史按月有了確鑿的記載,但也開始正式進入紛擾多事的混亂年代。
長達五百年的春秋戰國時期,一方面在學術文化上,由於周衰文弊,世官失所,而形成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壯觀局面。儒、道、墨三大顯學競爭的結果,至少在表面上,儒家具有明顯入世倫理色彩的仁義學說佔了上風,所以,重義輕利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在政治實現上,由於王室獨尊的結構趨於式微卻是一個列國傾軋、權力更迭的風雲時代,公卿世族、才智之士與軍事將領,成為活躍於歷史舞台的主角,其人格特徵與心理傾向,宛然可見。因此,民間文學作品對這個時代的刻畫,也開始從神話傳奇轉變為歷史寫實。
根據《左傳》、《史記》等史書不完整的統計,僅在春秋時代,中國境內即發生過三百七十八次戰爭,可見列國之間征戰與互併的激烈。到了戰國時代,由於具有強大軍事實力的政權,祗剩下所謂「七雄」,所以,戰爭的總數減少,但殘酷的程度卻相對遽增。秦趙之間的長平大戰,秦將白起一次坑殺所俘趙軍四十萬人眾,可見殺戮之慘烈。但列國軍事擴張的結果,也使中原民族的勢力逐漸伸展到淮河流域、長江流域,甚至珠江流域,為未來整個中國的疆域畫下了主要的輪廓,也為世界政治史上,極其罕見的秦漢「大一統」局面,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而從世界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英雄時代通常本應也都是史詩時代,希臘人與迦太基人長期爭戰,而有荷馬的《伊里亞德》;羅馬人削平南歐群雄,而有維吉爾的《伊尼以德》;法蘭克人歷經中古混戰,而有吟遊詩人集體創作的《羅蘭之歌》。然而,春秋戰國經緯萬端的英雄史蹟,不是一部史詩可以涵納的,而秦的強悍、楚的浪漫、齊的通博、魯的嚴謹、吳越的恩怨、燕趙的悲歌,事實上也難以在規格化的文學想像中融為一體。所以,這個時代的英雄傳奇與美女事蹟,往往透過各地民間的口語相傳,而零星流布來下結合著史書記載與民俗傳說,便形成了後代多種講述列國分合的歷史演義,而以《東周列國演義》為其中的翹楚。
五霸七雄的時代,中國境內風雲際會,人才極一時之盛。除了如城濮之戰、諸侯會盟、秦楚相爭、商鞅變法等政治大事之外,管仲與鮑叔牙的生死交情,重耳與介子推的離亂恩怨,屈原與楚懷王的悲劇結合,西施、夫差與勾踐、范蠡的多角關係;以及伍子胥單騎過關、苦心復國的耿耿志節,專諸捨身刺僚、一往無悔的亢直性格,豫讓紋身吞炭、以報知己的義烈行徑,荊軻白衣渡江、力搏暴君的壯士情懷,在在都說明了在古中國的蒼茫大地上,曾經演出過一幕又一幕令人目眩神搖的史詩情節。
然而,到了秦漢大一統時代,法家當令,專制成形,這一切深具生命的動態之感與悲劇之美的史蹟,都已成為明日黃花。正是:「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往,若為雄才?」
從矇昧邃遠的往古,到幽邈迢遙的未來,
時間的長流,
固然淹沒了無數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可是卻未必能夠淘盡
一切的民族業蹟與文化創造,
因為這是總體性的、客觀化的
人類生命之流,
在浩浩時間之流中的
一片拓影。
於是有了對死亡的恐懼,對青春的眷戀,
對永生的追求,對不朽的嚮往。
於是有了宗教的祈求、思想的啟發、
哲學的探索、文學的摹寫、藝術的創作,
面對那無垠無限的時間長流、
面對那飛馳不停的與情驅迫,
人類開始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作為這些英雄傳奇的共同背景的,
其實即是一整個民族
那遏抑不住
騰躍奔放的生命活力,正在其時到達了
波瀾壯瀾相激相盪的高潮時間,
所以英雄時代通常是
「力」的昂揚時代,
壯美絕倫,動人心魄。
在古中國的蒼茫大地上,
自睥睨王侯的豪雄英傑,到埋跡市井的狷介志士,
自狹技遨遊的知名劍手,到紋身吞炭的隱名刺客,
彈劍作歌,仰天長嘯,直道而行,仗義而鬥,
千里行而不裹糧,成大事而不留名,
種種鼓盪風雲的豪俠氣概與英雄行為,
曾經標示了民族的生命力,有一度到達了
何等酣暢淋漓的境界。
泛彼浩劫
遠古渾茫,史實難稽,在文學上是屬於神話時代。
中國雖然沒有如希臘的荷馬史詩《伊里亞德》、《奧迪賽》,印度的《羅摩耶那》、《摩訶羅多》,希伯來的《舊約.創世紀》,或北歐的《尼布龍之歌》之類雄奇瑰麗的大風格史詩與神話,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人拙於神話文學的表達方式。
事實上,詩經中的《商頌》與《周頌》,屈賦中的《天問》與《九歌》,都是結構鮮明、想像豐富的史詩型作品。更重要的是,在儒家的理性與入世精神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之後,像《山海經》、《穆天子傳》之類中國人的神話想像,仍然透過無數民間口傳創作的藝人,而在民俗文學中匯流與沉積。尤其,佛教中的神話文學,在魏晉之後大量湧入中國,更激盪了中國人的文學心靈中的神異色彩。
於是,透過神話原型與民俗傳說,配合宋元以來的講史和演義傳統,後代文學之士試圖為早期中國歷史刻畫出一個史詩式的造型,便產生了如《封神演義》之類作品。從民族「集體潛意識」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在想像文學上「尋根」的努力。正如一代才人王國維在其詠史詩中所指出:「回首西陲勢渺茫,東遷種族幾星霜?何當踏破雙芒屐,卻上崑崙望故鄉。」心靈上「尋根」的努力,促使歷史家深入考證中國遠古的文物與制度,也驅策著文學家盡情描摹中國遠古的帝王與英雄。
殷商的滅亡,姬周的崛起,以及周初的分封諸侯,是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於是,在民俗文學的想像中,便也充滿了波瀾壯闊的景觀。《尚書》武成篇與《史記》封禪書中的寥寥數語,到了元代居然可以鋪演為《武王伐紂書》之類的長篇平話作品,到了明代更蛻變成《封神演義》這部氣勢龐鉅的歷史奇幻小說,古意盎然,驚心動魄,或許,正反映了中國民俗文學的一大傾向,即是:試圖對於自己民族的起源、演變,與滄桑,給予一個在想像中可加以「合理化」解釋的文學造型。
紂王暴戾無道,所以火焚而亡;妲己殘忍狐媚,終於以身而殉,從現代人的觀點看來,難免有「泛道德主義」之嫌。然而,哪吒剔肉析骨,以償父母恩情,白藕青蓮,重還己身自由,這種在神話中典型的「叛逆英雄」形象,卻指述了中國文學在另一方向上的憧憬:嚮往精神上絕對自由。而哪吒終於與父母修好;退隱垂釣、絕意世事的賢臣姜子牙,終於加入武王伐紂的陣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終極的「和諧」觀念。不服正統體制的截教通天教主,統率旁門左道之士,與代表正統三教的闡教諸仙,殊死決勝,血流標杵,最後卻以子牙歸國封神、武王分封列國收尾,將正邪人神之死,悉數委之於「劫數」,而不忍更作追懲。也隱約反映了中國後代子民,對犯有過失的先人,仍不無基於「和諧」理想而生的恕道與善意。
這一幕幕縱想像的神話式歷史場景,若以司空圖《詩品》中的句子來表述,正是:「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窗然空蹤。」
一開始,文學就以
皎若霜雪之姿卓立於
太初生民的玄想間。
從原始的無盡荒寒,
到文明的無限擾攘,
從現代的漠漠紅塵,
到末世的莽莽風沙;
這種姿勢,迢遙而永恆。
古典是易逝的。
多少美人的翠袖,
空自隔著前代的煙霧招展,
多少英雄的白髮,
早已在歷史的寂寞中擱置;
詩人的袍角,酒客的金樽,歌者的嘆息……。
只有文學,像玉石上千百年來
緩緩凝成的紋理,
絲絲縷縷,把這些記錄下來,供你閱讀。
不必觀天象,
你的指掌自能屈算人事。
若有酒,何不空杯。
若有驛車,何不共進?
人生動如狡兔,靜如處子,
一旦場鑣分道,
若要相見,須問參商。
明月引潮生,綿綿蕩蕩,
在萬般夢境裏翻湧。
潮來期去,煞像是心情的起伏,
挑動無名的一根琴絃。
潮漲時如水晶屏風瑩然剔透,
潮落時如花如霧煙籠蒼茫,
此情此景,此生此世,
俱在原始渾沌的韻律當中。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吟罷江山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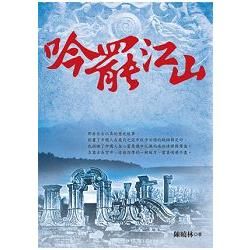 |
吟罷江山 作者:陳曉林 出版社: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5-1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吟罷江山
◎人類從遠古至今,歷經許多文明、戰爭及時代的變遷,這些改變,對一個民族的影響是什麼?所產生的文學作品是否亦沈澱了一代代人文的痕跡?身在其中的我們,在面對萬里江山的壯闊美景時,又會產生什麼樣思古之幽情?
◎本書為一短篇散文集,結合了歷史典故、優美詩詞,將地理風景與人文情懷充分融合,繪成一幅幅圖文並茂的文章,足可讓人發思古之情,更從古人遺跡中得到啟發。
吟罷江山氣不靈 萬千種話一燈青
忽然擱筆無言說 重禮天台七卷經
書中四十篇散文,每一篇都觸及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代,以及中國人在那個時代裏所遭遇的生命試煉,或所締造的文明業績。因此,串連起來,這些文字試圖將四千年來中國人所經歷的掙扎與吶喊,所表現的奮揚與沉哀,所懷持的嚮往與追慕,所體映的眷戀與關懷,以集中輻輳的形式,呈現在當代人的眼前。微意所在,無非是希望引起當代人對自己民族的歷史,能萌生一些同情的了解,或品嘗一些感性的回味。
作者簡介:
陳曉林,一九四九年生。臺灣大學電機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碩士。曾先後任教於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民生報》及《聯合報》總主筆。現任風雲時代出版公司發行人。其創作文類以論述及散文為主,以精深的理工學識轉向文學、歷史與哲學的探究,專攻近代中西思想史,深入關懷人文理性與人性價值。他的散文,文字雄健恣縱,思路深湛明爽,筆鋒常帶感情,充滿知識分子對國家對社會深沉的反省與思考。著有《吟罷江山》、《劍氣簫心》、《壯歲旌旗》等文集。並曾獲國家文藝獎。
章節試閱
中國人共同的感情與記憶(自序) 陳曉林
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從邃古時代到農業時代,從農業時代到工商時代,再從工商時代進入到如今的「後工業時代」或「資訊時代」,歲月迢遙,星移物換,人間大地已經不知變換了多少次面貌,曾經在人類歷史舞台上,迸發過光輝與熱力的無數英雄兒女、志士仁人,也都已經在滾滾而逝的歲月之流中,歸於寂靜。
然而,在茫無際涯的時間長流中,人間世一切的掙扎、吶喊、奮鬥、堅持,難道果真都沒有恆久而深長的意義可言?
穿越過時間的風暴,畢竟有許多個歷經淘煉的民族,從矇昧的遠古、漫長的中世,逐...
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從邃古時代到農業時代,從農業時代到工商時代,再從工商時代進入到如今的「後工業時代」或「資訊時代」,歲月迢遙,星移物換,人間大地已經不知變換了多少次面貌,曾經在人類歷史舞台上,迸發過光輝與熱力的無數英雄兒女、志士仁人,也都已經在滾滾而逝的歲月之流中,歸於寂靜。
然而,在茫無際涯的時間長流中,人間世一切的掙扎、吶喊、奮鬥、堅持,難道果真都沒有恆久而深長的意義可言?
穿越過時間的風暴,畢竟有許多個歷經淘煉的民族,從矇昧的遠古、漫長的中世,逐...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古愁之葉:百歲如流、泛彼浩劫、明月前身、返虛入渾、壯士拂劍
浪莽之葉:水理漩伏、華頂之雲、風雲變態、碧苔芳暉、南山峨峨
綺麗之葉:明漪絕底、妙造自然、濃盡必枯、吞吐大荒、如瞻歲新
迴旋之葉:曜足扶桑、如覓水影、清露未晞、脫帽看詩、杳靄流玉
悲情之葉:妙契同塵、古鏡照神、海山蒼蒼、如見道心、人聞清鐘
豪野之葉:之子遠行、大風捲水、行氣如虹、幽鳥相逐、意象欲生
落絮之葉:與古為新、落花無言、遠引若至、生者百歲、風日水濱
激湍之葉:天地與立、海風碧雲、得其環中、萬取一收、悠悠天鈞
後記
古愁之葉:百歲如流、泛彼浩劫、明月前身、返虛入渾、壯士拂劍
浪莽之葉:水理漩伏、華頂之雲、風雲變態、碧苔芳暉、南山峨峨
綺麗之葉:明漪絕底、妙造自然、濃盡必枯、吞吐大荒、如瞻歲新
迴旋之葉:曜足扶桑、如覓水影、清露未晞、脫帽看詩、杳靄流玉
悲情之葉:妙契同塵、古鏡照神、海山蒼蒼、如見道心、人聞清鐘
豪野之葉:之子遠行、大風捲水、行氣如虹、幽鳥相逐、意象欲生
落絮之葉:與古為新、落花無言、遠引若至、生者百歲、風日水濱
激湍之葉:天地與立、海風碧雲、得其環中、萬取一收、悠悠天鈞
後記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曉林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5-12 ISBN/ISSN:978986352155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