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廣陵,睜開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實交代,這是些什麼臭狗屎!」
審訊者「啪」地把一包用雨布包著的東西扔到桌子上,裏面發出金屬撞擊的窸窣聲。趙廣陵右眼皮跳了一下——最近以來右眼皮一直都在跳,看來又該「還債」了。
審訊者是監獄農場工宣隊的饒隊長,過去是鑄造車間的澆鑄工,還有兩個市裏來串聯的紅極一時的造反派,一個是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楊司令,鬍鬚剛剛冒出來的小後生;一個是鋼鐵廠的戰鬥隊大隊長。他們現在已經奪了法官、檢察官和員警的權,砸爛公檢法就像打碎一個茶碗那樣易如反掌。他們沒有象徵國家司法權力的制服和徽章,但他們左胳膊上有一個紅袖箍就足以橫掃全國所有的牛鬼蛇神。趙廣陵這樣的監獄留隊人員,在他們眼裏,簡直就是骯髒惡臭的渣滓,早該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了。
饒隊長用玩弄籠中之鼠的鄙夷口吻問:「趙廣陵,知道這裏面是什麼東西嗎?」
「知道。」
「那就老實交代。」
「國民政府頒發的四等雲麾勳章一枚,抗戰勝利勳章一枚,大約還有一枚青天白日勳章,一枚軍校的學員證章。」
趙廣陵如實回答。他不明白的是,這包早在多年前就被深埋在院子裏「明梅」樹下的東西,是怎麼被翻出來的?即便是抄家,也不會去挖一棵古樹吧?唉,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曾經的榮耀就是今天的罪證,如果生命是輪迴的,苦難也註定是輪迴的。
「哼,看你的口氣,好光榮哦。」
「井岡山兵團」的楊司令嘲諷道,然後他打開了那個已經褪色了的雨布布包。這塊雨布是從美式軍用雨衣上剪下來的,多年以後依然防潮,不爛不縷。要是這個紅衛兵司令知道這也是舊時代美帝國主義的玩意兒,趙廣陵豈不又罪加一等?那雨布包顯然已經被人翻弄過了,不是趙廣陵和舒淑文十多年前埋藏時包的仔細規整的樣子。趙廣陵還記得妻子用麻線纏了好幾圈。舒淑文似乎說過這樣的話:留這些東西有啥意思呢?說不定會招禍的。當時趙廣陵是怎樣回答的,他已經想不起來了。
「這是一個人的歷史。」現在,趙廣陵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作答。
「反革命歷史!」工宣隊饒隊長喝道。
「報告饒隊長,雲麾勳章是我參加抗日遠征軍在滇西松山戰場上打日本鬼子時,用鮮血和命掙來的,抗戰勝利勳章是當時的政府對我們這些參加過抗戰的軍人的褒獎。這段歷史是為國家民族而戰的歷史,不是反革命歷史。」
「胡扯!」那個紅衛兵司令一拍桌子,「你們國民黨打什麼日本人?你們只會投降、逃跑,大片的國土都拱手送給日本人了。只有我們毛主席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堅持了八年敵後抗戰,才最終打敗了日本鬼子。日本投降了,你們才來摘桃子。你想歪曲歷史嗎?」
「我不想歪曲歷史。滇西的日本鬼子的確是被遠征軍打敗的。騰沖戰役全殲日軍一個聯隊,松山戰役也是全殲鬼子一千多人。小同志,抗戰時要圍殲鬼子成建制的一個聯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龍陵、芒市戰役一直將日本鬼子趕出畹町國門,殲滅日軍一萬多人。我們死了多少人啊,小同志,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們這些國民黨反動派為什麼不全死光。」紅衛兵司令站起身,解開了腰間的軍用皮帶。
趙廣陵從一九五○開始接受審查,先是人民管制,然後是服刑勞動改造,他挨過罵,受過呵斥侮辱,站在台上被批判,但還沒有挨過一次打。他不知道紅衛兵皮帶的厲害,他們用它上可抽元帥將軍,下可抽自己的老師,就更可以抽趙廣陵這樣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了。這個只比他兒子豆芽大不了多少的紅衛兵司令,一皮帶就把他抽得眼冒金星。然後好像那另外兩個人都上來了,拳打腳踢外加他們擁有的語言權威和唾沫星子。趙廣陵蜷縮在地上,多想有一雙手護著自己的頭,但他的雙手被綁在身後……
他們打累了,重新把趙廣陵按到椅子上。趙廣陵只感到自己的頭腫得有籃球大,眼睛都睜不開了,腦子裏飛舞的全是些到處亂竄的星星,像是被轟散的一群螢火蟲。他過去在戰場上負重傷時,有過這樣的感受。但那時他相信自己能活下來,現在他不敢相信了。他面前站著的就像來自地獄的手拿勾魂簿的三個小鬼。
「趙廣陵,老實交代,你這些反動獎章是怎麼得到的?」
「參加遠征軍……打日本鬼……」
「什麼遠征軍近征軍,都是偽軍!」
也許因為剛才的毆打深深傷害了趙廣陵的自尊,也許因為在他的心目中有一處最神聖的地方不能輕易受人詆毀和污蔑。趙廣陵就像有神魂附體一般,忽然挺直了腰,儘量睜開血肉模糊的雙眼,高聲抗辯道:
「這位紅衛兵小將,遠征軍不是偽軍。當年漢奸的隊伍才是偽軍。我們的遠征軍是打日本鬼子的,是在為我們的國家民族打仗啊!」
「啪!」紅衛兵小將拍了一下桌子,「胡扯!」然後他又不說話了。似乎在想「偽」這個詞究竟該怎麼說才更雄辯霸氣、擊倒對方。那兩個工人造反派沒有什麼文化,更想不出反駁的理由。審訊室寂靜了兩分鐘,紅衛兵小將畢竟是高中生,知道一些推理,於是他才冷冷地問:
「國民黨是反動政權,你承不承認?」
「是。」
「遠征軍是國民黨的軍隊嗎?」
「是。」
「那它是不是反動的呢?」
這還真把趙廣陵問倒了,他忍著全身的疼痛想了半天才說:「我承認國民黨政府是個反動、獨裁、專制的政權,我那時也很討厭甚至憎恨他們。可我參加國民黨軍隊,是因為日本人已經打到我的家鄉了。況且,當時國民黨軍隊是抗日的,共產黨軍隊也是抗日的,大敵當前,國共都在合作抗日。我們遠征軍打日本人,應該沒有什麼錯吧?當年我們遠征軍在滇西取得勝利,延安的十八集團軍朱德總司令、毛澤東主席都發來過賀電。這不會錯吧?」
「你胡說八道!毛主席會給你們國民黨反動軍隊發賀電?你這是污蔑偉大領袖!」鋼鐵廠的那個戰鬥隊隊長衝了過來,一拳又把趙廣陵又打倒了。然後他又抓著趙廣陵的衣襟把他拎起來:「說,遠征軍是不是偽軍?」
「不是。」趙廣陵大口喘著粗氣,倔強地說。
「這些反動獎章,是你抓了多少地下黨,殺了多少革命者才得來的?」
「是殺日本鬼子換來的!你有本事,你殺幾個鬼子給老子看看!難道你們非要我承認殺日本鬼子是我的罪行嗎?難道中國人整中國人,就是你們的革命嗎?」趙廣陵徹底被激怒了,他打算和他們抗爭到死。當年為什麼不死在抗日戰場上?這一輩子活得多窩囊啊!他早就想爆發、想吶喊了。那麼,就像聞一多先生那樣做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吧。
出乎趙廣陵意料的是,他們不打他了,竟然都呆呆地望著他,就像望著威武不屈的手下敗將。對有些被打倒了再爬起來,再打倒再爬起來的人,打人者即便是流氓無賴,也會感到無趣。再強大的革命理由,再強悍的鬥爭哲學,再堅如磐石的階級立場,只要他還是個人,只要他還能分辨出日本侵略者和中國人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他都應該在這個抗戰老兵面前感到羞愧。
三個審訊者似乎都感到審不下去了。追問歷史,往往會追問到自己身上。他們抓趙廣陵,本來是想通過對那幾枚勳章來歷的追查,挖出趙廣陵隱藏得更深的反革命歷史來。按照他們的邏輯推理,能得到國民黨反動政權勳章的人,一定雙手沾滿了革命者的鮮血。但誰能料到這些勳章跟打日本鬼子有關呢?歷史太容易被遮斷了,他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百分之百地相信當年國民黨是「假抗日、真投降」,二十多年前發生在自己家鄉的那場抗擊侵略者的戰爭,他們的父輩祖輩不敢說,課本裏告訴他們的是另一套說辭,這個反革命分子趙廣陵說的那些話,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最後還是工宣隊的饒隊長老道一些,他說:
「趙廣陵,你只要承認遠征軍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偽軍,這些獎章是反動的,就算認罪了,我們會寬大處理你。你認還是不認?」
「不認。」趙廣陵彷彿不假思索就回答了這個性命攸關的問題,就像絕不會承認一加一等於三一樣。
「我們必須再次告訴你我們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堅持自己的反動立場,是要再進牢房的。」紅衛兵小將用法官的口吻冷峻地說。
趙廣陵沉默了。他滿臉血污,疤痕又抽搐起來,扯得面部神經刺痛難忍,膝上的雙手手指也在微微顫抖。他不是在擔心如果頑抗到底的話,會有幾年的刑期,而是在想剛剛恢復了沒幾年的正常家庭生活,又將面臨怎樣的破碎、哀怨、冷清、清貧,以及孩子們對他的失望乃至厭惡。
沒有比從精神上擊垮犯人更令審訊者有成就感的事情了。饒隊長再次追問:
「承認不承認?」
「不。」
「真是個又臭又硬的國民黨反動頑固派。先關起來再說。」
趙廣陵又重新回到牢房裏了,只不過不是當年十二人一間的大號子,而是只關一個人的禁閉室,其實就是黑牢的代名詞。它約有三平方米大小,一米五高,裏面只有一張八十公分長、四十公分寬的木床,人睡覺只能蜷縮著,想站立時也必須保持低頭向人民認罪姿勢。與其說它是一間「室」,不如說它是一個「窟」,或者一座「穴」。狹小、逼仄、潮濕、悶熱等,都還不算最折磨人的,無垠的黑暗才是奪人魂魄的冷血殺手。按那個天體物理學家劉麒麟的說法,時間被「黑洞」捕捉了,吞噬了。那時趙廣陵怎麼也理解不了時間如何被逮住、被一口吃掉。這個只有具備外星人的頭腦才能理解的深奧理論,只要把你關進禁閉室,你馬上就明白了。對一個接受改造的犯人來說,限制你的自由只是第一步,囚禁你的光明是第二步,再剝奪你的時間,那可真是觸及靈魂的革命。
送水送飯的窗口只有巴掌大小,平常是被封閉起來的。當每天一束光線像鞭子一樣抽打進來時,便是送飯的時間。那光線會灼得他眼睛生疼,但他比渴望一點發餿的食物更渴望一絲光明;比渴望光明更渴望政府給他一個說法。他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想:我既不是當權派,也不是造反派,我有歷史舊債,但我已經坐過牢了,改造好了,還立功受獎提前釋放了。我現在只是一個認真勞動的木匠,勳章是國民黨發的,但那是為國家為民族抗擊入侵者用鮮血和拚老命掙來的。中國歷史上的哪個朝代,不視抵抗外侮的人為英雄?
可是在深淵一般的黑牢裏,他的時空再度被扭曲,他已經徹底喪失了方位感、時間感。他現在如何能保護自己的家?他只祈願這再一次的磨難不要又給家庭帶來什麼災難。他已經失去兩個孩子了,他不能再在亂世中又添喪子之痛。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吾血吾土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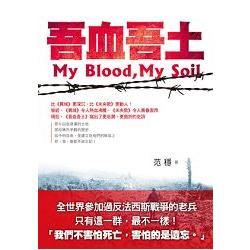 |
吾血吾土【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范穩 出版社: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0-2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512頁/15*21mcm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48 |
中國歷史小說 |
$ 348 |
中文現代文學 |
$ 387 |
歷史小說 |
$ 396 |
華文歷史小說 |
$ 39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吾血吾土
*本書入圍2015年茅盾文學獎
全世界參加過反法西斯戰爭的老兵,只有這一群,最不一樣!
「我們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遺忘。」
那片以血澆灌的土地
那段慘烈辛酸的歷史
如今的自由,是建立在他們的鮮血上
你,我,誰都不該忘記!
比《異域》更深沉,比《未央歌》更動人!
曾經,《異域》令人熱血沸騰,《未央歌》令人青春激昂
現在,《吾血吾土》寫出了更壯濶、更曲折的史詩
滇緬抗日、西南聯大、國共內戰,時代流漓,宿命對決……
名作家范穩的《吾血吾土》,採訪二十餘位抗戰老兵的真實史實,以文學的迷人魅力引你進入七十年生死兩茫茫的歷史畫卷!
他,是迎春劇藝社的話劇導演趙迅、是共產黨眼中的國民黨反動軍官趙廣陵、是抗日戰火中燒壞一張臉的廖志弘、是被誤為陣亡於畹町的上尉連長趙岑、是軍統特務龍忠義……
他不斷變換自己的名字、身分,試圖隱藏自己那段不容於世的過去,卻還是被剝繭抽絲般的解剖出來。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有一段血淚的故事。
當身為西南聯大優秀學子的他,為了民族大義,毅然投筆從戎,投考黃埔軍校,參加遠征軍時,他的一生,就註定了轟轟烈烈。只是誰也沒料到,當初滿腔熱血的愛國心,卻在後半生成為不容分說的罪孽,幾乎在監獄裏度過了下半生。
他曾與迎春劇藝社的台柱舒菲菲相戀,卻因戰火而分隔兩地,最後娶了舒菲菲的妹妹為妻,育有四子。只是,在文革期間不斷反覆鬥爭的結果,他偽裝的身分不斷被揭穿,妻兒也因此飽受苦難。當他以還債之心坐完牢,終於與妻兒共度了一段好日子,卻又遭人挖出深埋在梅樹下的國民黨勳章,再次將他送進歷史深淵!且最最令人不堪的是,那以勳章揭發他的人,竟是他一心想入紅衛兵的大兒子!
四十年後,一切歸於平淡。
他遇到了當年親手俘虜的日軍秋吉夫三,兩個立場敵對的老兵,共同回憶了那一段各自驕傲的歲月,也讓他憶起戰友的沉重付託。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他決心要將故友的骨骸帶回家鄉,即便骨已化成灰;
即便故友戰死的那塊地,已被劃為緬甸國土,他也要將染有故友鮮血的土,帶回故鄉……
作者簡介:
范穩
華文世界極受矚目的名作家,1986年開始發表作品,已出版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15部,近500萬字,多部作品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等文字。
歷時十年創作的「藏地三部曲」,蜚聲文壇,2013年被十月雜誌社評為「35週年最具影響力作品」。2006年海峽兩岸圖書博覽會上,被台灣四家出版社和網路機構評為「最受台灣讀者喜愛的十大大陸作家」之一。
曾獲當代長篇小說優秀獎、全國優秀圖書獎、十月文學獎、《當代》雜誌「五年五佳」作品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等獎項,並連續兩屆入圍茅盾文學獎。「藏地三部曲」台灣版亦為風雲時代出版公司所出,即《百年靈域》、《大地心燈》、《天涯海角》。
TOP
章節試閱
「趙廣陵,睜開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實交代,這是些什麼臭狗屎!」
審訊者「啪」地把一包用雨布包著的東西扔到桌子上,裏面發出金屬撞擊的窸窣聲。趙廣陵右眼皮跳了一下——最近以來右眼皮一直都在跳,看來又該「還債」了。
審訊者是監獄農場工宣隊的饒隊長,過去是鑄造車間的澆鑄工,還有兩個市裏來串聯的紅極一時的造反派,一個是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楊司令,鬍鬚剛剛冒出來的小後生;一個是鋼鐵廠的戰鬥隊大隊長。他們現在已經奪了法官、檢察官和員警的權,砸爛公檢法就像打碎一個茶碗那樣易如反掌。他們沒有象徵國家司法權力的制服和...
審訊者「啪」地把一包用雨布包著的東西扔到桌子上,裏面發出金屬撞擊的窸窣聲。趙廣陵右眼皮跳了一下——最近以來右眼皮一直都在跳,看來又該「還債」了。
審訊者是監獄農場工宣隊的饒隊長,過去是鑄造車間的澆鑄工,還有兩個市裏來串聯的紅極一時的造反派,一個是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楊司令,鬍鬚剛剛冒出來的小後生;一個是鋼鐵廠的戰鬥隊大隊長。他們現在已經奪了法官、檢察官和員警的權,砸爛公檢法就像打碎一個茶碗那樣易如反掌。他們沒有象徵國家司法權力的制服和...
»看全部
TOP
目錄
◎卷宗一
1950:第一次交代——以迎春花之名
1•迎春劇藝社
2•思想彙報
3•思想改造
4•寒梅會(交代資料之一)
5•人民管制
◎卷宗二
1957:第二次交代——以魯班之名
6•魯班現形記
7•山東戰場(交代資料之二)
8•哀榮無定在
9•在大師身邊(交代資料之三)
10•湖堤上的辯證法
11•槍口下的大師
12•告密者
13•留隊人員
◎卷宗三
1967:第三次交代——以遠征軍之名
14•二進宮
15•雲麾勳章(交代資料之四)
16•松山之囚
17•松山之役——黑暗中的傾訴
◎卷宗四
1975:第四次交代——以特赦之名
18•回家...
1950:第一次交代——以迎春花之名
1•迎春劇藝社
2•思想彙報
3•思想改造
4•寒梅會(交代資料之一)
5•人民管制
◎卷宗二
1957:第二次交代——以魯班之名
6•魯班現形記
7•山東戰場(交代資料之二)
8•哀榮無定在
9•在大師身邊(交代資料之三)
10•湖堤上的辯證法
11•槍口下的大師
12•告密者
13•留隊人員
◎卷宗三
1967:第三次交代——以遠征軍之名
14•二進宮
15•雲麾勳章(交代資料之四)
16•松山之囚
17•松山之役——黑暗中的傾訴
◎卷宗四
1975:第四次交代——以特赦之名
18•回家...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范穩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0-21 ISBN/ISSN:978986352248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12頁 開數:正25K-15x21cm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歷史小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