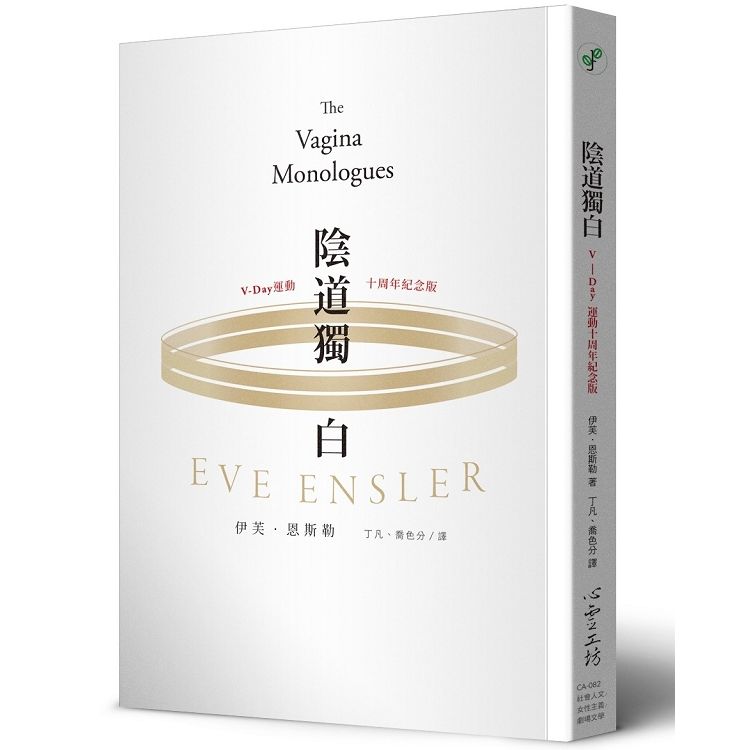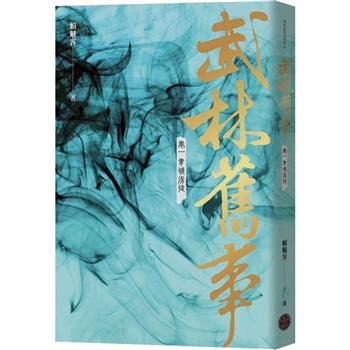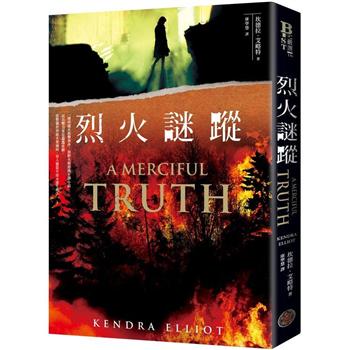「各位觀眾,這將會是你聽到最多次『陰道』的夜晚!」
1994年,伊芙.恩斯勒發表了轟動國際的劇作《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es)。這齣戲劇以她對兩百多位女性的訪談而寫成,這些不同年齡、職業、性傾向、種族的女性生命故事,榮耀了女性的身體與性,展現其複雜與神祕,使本劇被視為新一代女性的聖經。全劇突破禁忌,機智風趣,充滿同理心與人生智慧,贏得多項大獎(包括1997年的歐比獎[Obie Award,外百老匯優秀劇目年度獎]),讓女性內心最深處的幻想和恐懼有了高唱的管道。看過之後,你永遠不會再用舊有眼光看待女體與性。
《陰道獨白》的成功,促使伊芙在1998年發起「V-Day運動」,目標是「終止全球對女性的暴力」。她們組織世界各地的婦女團體在自己的國家演出《陰道獨白》,並募款援助受暴婦女。
2008年,適逢V-Day運動十周年,特別出版了《陰道獨白》十周年紀念版,包括五個未發表過的獨白、伊芙撰寫的全新前言,以及別具意義的十年舞台歷史——從紐約市的HERE藝術中心(HERE Arts Center)到全球各地,伊芙.恩斯勒邀請你一同見證社會運動與劇場藝術的輝煌一頁。
名人推薦
1. 李昂 作家,著有《殺夫》、《北港香爐人人插》等
2. 胡因夢 身心靈療癒導師
3. 紀惠容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4. 畢恆達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5. 蘇芊玲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創會理事長
近十年來討論社會議題的劇本中最重要的作品。──《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陰道獨白》超越一般熱門戲劇,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這可不是你母親那一代的女性主義。——專欄作家毛莉.艾文斯(Molly Ivins)
時而沉痛,時而狂歡……作者充滿了激情與機智。——《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太傑出了……這是關於女性本質的精彩狂想曲。——《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引人入勝、詼諧有趣,感動得令人難以承受……這不只是一部戲,也是文化藝術史上一個犀利的片段。——《綜藝》雜誌(Var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