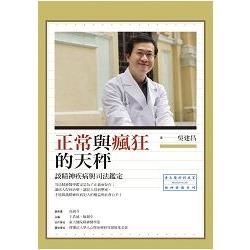◎臺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的專業權威,提供正確的相關知識,以深入淺出方式,針對患者的常見疑惑,完整加以解說。宛若醫師親自在你面前,娓娓為你解惑,是實用可親的居家必備健康叢書。
◎臺灣司法鑑定權威醫師吳建昌,是多起重大刑案的精神鑑定醫師,具備深厚法學素養。吳醫師在書中現身說法,從學理與實務兩方下手,講解我國司法鑑定的基本準則、精神醫學界與法界的見解折衝,並列舉多項國內外案例與時事輔佐說明,是可以迅速了解司法精神鑑定的好書。
司法精神醫學鑑定是為了正義而存在;
讓病人得到治療、讓犯人得到懲戒,
才能維護精神疾病犯人的權益與社會公平!
●失智症患者拿走鄰居的東西,他犯了竊盜罪嗎?
●躁症發作時買了豪宅,付不出錢可以反悔嗎?
●自稱因幻覺而殺人,會被判刑嗎?
犯罪的人必須負起刑事責任,但精神異常者犯罪時,該不該負起刑責?
這時,司法精神鑑定就扮演了關鍵角色。
隨著近年國內發生多起令人驚駭的重大犯罪案件,司法精神鑑定成為媒體及大眾談論的焦點。本書作者吳建昌醫師,為國內司法鑑定之權威。吳醫師列舉國內外許多經典案例,從精神醫學與法律兩種角度,剖析兩者如何看待診斷與精神狀態,以及澄清精神疾病與犯罪關係。在書中,吳醫師也詳述了司法精神鑑定的原則、判斷關鍵,並釐清大眾的誤解。
司法精神醫學一直在臺灣司法系統中扮演著沉默的橋樑角色,鑑定醫師們努力將精神病理學事實翻譯為法律事實,協助法院達成司法正義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司法精神鑑定與每個人都有切身關係,充實這個領域的知識,刻不容緩。
作者簡介:
吳建昌,臺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主任,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暨主治醫師(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研究所副教授。專長生命倫理(含醫事倫理)及科技倫理的研究、司法精神醫學(含性侵害加害人、家暴加害人之診療)、醫事法及政策、公共衛生法、精神衛生法與政策 (法律、經濟與倫理分析)等。
吳醫師參與司法精神鑑定工作多年,參與國內諸多重大案件的鑑定工作,是國內此領域的權威醫師,他具有深厚的法律、倫理與精神醫學的學養,其教學及研究活動跨越領域,擅長以淺白語言講解司法精神醫學的要旨,長期著力於司法及精神專業人員的教育訓練。本書是吳醫師講述司法精神鑑定與大眾切身關係的第一次嘗試。
章節試閱
前言
法學與精神醫學的橋樑
【灰狗巴士上的分屍案】
在夜色中,一輛灰狗巴士以穩定速度緩緩行進。車上三十七名乘客正安靜地觀賞著電影,二十二歲的普林頓(化名)閉目養神,戴著耳機、聽著音樂,四十歲的萊維斯(化名)就坐在他身邊。車上氣氛祥和安靜,引擎聲呼呼作響著。
毫無任何預警,萊維斯沒有出聲,突然舉起手上的藍波刀,猛力刺向身旁的普林頓。萊維斯殺紅了眼,連砍六十刀,沒有喘息,他砍斷普林頓的頸部,割下血流滿面的頭顱,高舉示眾。
乘客們被這突然的殺人舉動嚇得尖叫,慌亂地擠在狹小的車廂內。司機立刻緊急停車,開門讓乘客逃離。停車之後,萊維斯當場肢解普林頓的身軀,將屍塊丟在巴士各個角落,還有乘客目睹萊維斯吃下部分屍塊,就在他試圖開走巴士之際,警察抵達現場,成功阻止萊維斯逃亡。
萊維斯被控二級謀殺罪,法院裁定對萊維斯進行司法精神醫學鑑定。萊維斯在接受精神鑑定時,向精神科醫師透露,在上車之前,他聽到上帝的聲音,上帝命令他坐在普林頓旁邊;上帝告訴他,普林頓是一個大邪魔,這個大邪魔正準備要處決他,因此萊維斯認為自己有必要先行採取行動以保護自己。在砍下普林頓腦袋之後,他擔心大邪魔再度復活,遂決定肢解普林頓的身體,然後有如進行儀式般,將屍塊散置巴士各處。
精神科醫師最後鑑定萊維斯罹患有思覺失調症(舊名精神分裂症),受幻覺、幻聽所苦,萊維斯認為上帝隨時可能取走自己的性命。在殺死普林頓的當下,他並不知道自己殺死的是無辜者,而且在犯案的當下,萊維斯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誤的。
最後法官採信精神科醫師的論點,裁定萊維斯不須對其行為負刑事責任。
(文本參考2008年8月中央社記者張若霆、中廣新聞網報導)
這則發生在西方國家的真實案例,是司法精神鑑定案件經常看到的典型情境——有一個人做了觸犯法律的行為,而他又有類似精神疾病的症狀,此時他是否會在法庭上被定罪?在法律的裁判過程中,就會牽涉到法院(司法)與精神科醫師(精神醫學)兩方。
此處必須強調的是,所謂「典型案例」並不是指犯罪嚴重到殺人致死。此處所說的典型,是指該案所牽涉的層面與需要考量的內容是很典型的,例如犯罪者知不知道自己做了錯事?在犯案當下他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這些行為是不是與精神疾病有關係?每當碰到這種情況,法院常常會需要精神科醫師的協助。
一、司法精神鑑定不是辦案影集
在電視劇或電影中,犯罪案件永遠是最吸引人的題材,尤其是精神異常者所犯下的案件,有時情節多殘酷、怪異、脫離常態,超出一般人的生活經驗,因此成為戲劇節目編劇時的最佳素材。
然而,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事件不是只有在電視劇、電影中才看得到,在我們自身、周圍親朋好友、鄰居乃至同事,都可能在家庭、社區、工作環境中,遭遇因相關精神疾病所促發的刑事或民事糾紛,如何確實了解精神醫學與法律的關係,以避免法律問題,這關乎個人以及親朋好友的法律權益。
國家法律一般以正常人為基礎及對象,臺灣刑法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除了以重刑彰顯殺人的嚴重錯誤性,這種規定的用途和目的也在於正常人能夠理解處罰的嚴重性,出於理性反應,通常不會去做犯法之事;然而,對所謂的非正常人(如精神病患者)來說,他們卻不一定有辦法這樣思考。
的確,有些做壞事(指法律不認可之事)的人,可能真的是壞,但有些做壞事的人卻可能並不是壞人,而是他們的身心存在著一些因素,導致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探討兩個問題:「這人是壞人嗎?」以及「他所做出的行為是壞的嗎?」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關鍵在於「壞事」(指該行為及/或所導致的結果是壞的)是法律不認可的行為,但做這件事的人卻不見得是壞人。所以,有些做壞事的人真的是壞人,但有些人並非真的是壞人。那麼,法律對這樣的人施用嚴重刑罰來處罰,到底適不適合呢?尤其當法律的運作遇到不正常的精神狀態時,其適用性及正當性就會發生一些疑義,這時精神醫學鑑定就扮演了關鍵角色。
司法精神醫學鑑定跟電視影集描述的工作是不一樣的。精神科醫師只負責鑑定犯案者的精神狀態,製作成鑑定報告書,提供給法官做為形成心證的證據之一。也就是說,只有法官才有權力決定有罪或無罪,精神科醫師沒有裁判的權力;精神醫學的重點僅在協助法院處理「非一般人」的精神狀態下,所觸犯法律或產生法律糾紛的事情。
二、正常與瘋狂的天秤
司法精神鑑定要處理的不是只有疑似精神疾病的犯罪行為,它的範疇非常廣泛,也包括強制住院、民事能力的判定、勞工失能鑑定、身心障礙鑑定、性侵害加害人強制診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強制勒戒、家暴處遇等等,只要可能牽涉到精神狀況的案件,都屬於廣義的司法精神鑑定的範疇。
本書的主題是「正常與瘋狂的天秤」,我之所以使用「天秤」一詞,目的在於一方面強調法律看的是證據,刑事天秤的一邊是有罪的證據,另一邊是無罪的證據;另一方面,刑事法庭也處理嫌犯的瘋狂狀態是否到達法律上認為的「刑事責任的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的程度。民事與刑事法庭各有不同的砝碼標準;民事法庭看的是哪一邊的證據比較重,由法院決定訴訟或事件的某一方比較有道理,同時決定當事人的瘋狂是否達到民事能力欠缺或顯有不能的程度。這個法律上的「能力」是一種門檻的概念,不只是是否瘋狂而已,而是他到底有多瘋狂,且瘋狂到何種程度(是輕躁症還是嚴重妄想)、跨越了法律的何種界限,才會被認為法律上的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例如在民事糾紛中,輕躁症患者過度樂觀,預購許多房屋,但因他在購買房屋時仍具有理解買賣行為及其效果的能力,就會被法院判定具有購買房屋的民事能力,不能悔約。又如刑事案件中,常常受到聽幻覺碎念干擾的人,做出與聽幻覺內容無關的犯罪行為時,即使有「瘋狂」的現象,其瘋狂程度仍未到達刑事責任能力顯著減低的程度。因此在刑事案件中,法院會請司法精神鑑定人員來協助鑑定犯案者,在犯罪當下的精神狀態是如何的,至於天秤最後會偏向哪一邊?有罪或無罪?能力有無欠缺?端賴法院的裁斷。而在民事案件或事件中,當事人何方有道理?能力有無欠缺?同樣亦需由法院進行判斷。
近年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醫學人才投入這領域,我欣見司法精神醫學的未來發展。司法精神鑑定,做為司法精神醫學的一種實作,乃是法學與精神醫學的橋樑,扮演類似天秤的角色,協助法院透過精神醫學的凝視,合乎正義地度量法律關注的正常與瘋狂的心智事實。本書出版的目的,並非進行法學概念的分析,也不會特別強調法學分析的步驟,而在說明精神醫學可以在法律事務上提供怎樣的協助,幫助讀者理解司法精神鑑定的主要原理與操作。
精神鑑定與生活法律
婚姻關係之存續
民法第996條(結婚之撤銷——精神不健全)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得於常態回復後六個月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中文的「婚」,是部首「女」旁加上「昏」字,這個字很有意思。不管男女,許多讀者應該都有類似的想法:我們往往都是等到結了婚之後,才感嘆自己當年是不是「昏了頭」,以致於步入婚姻。雖然這是開玩笑,但在法律上,假設因為覺得「昏了頭」而後悔、想撤銷婚姻關係的話,可不是這麼容易。
在買賣契約或婚姻關係等案件中,會出現民法第75及第996條的「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的問題。這是什麼意思呢?
舉例來說,你在結婚時,正處在精神疾病發作狀態中,以為老公是來自天上的神仙,開心地出嫁,等到精神疾病發作過後,「醒來」發現老公也是凡人,你結婚當時是在疾病發作狀態中出嫁的,顯然你是在「精神錯亂」的狀態中,因此在「醒來」後的六個月內得以訴請撤銷婚姻。
根據前述民法第996條的規定,只有兩個理由可以撤銷婚姻,其中一個就是當事人一方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的情況下結婚;另一個則是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結婚。依法「婚後精神狀態回復常態後六個月內」都有機會訴請撤銷婚姻。倘若在婚後精神狀態回復常態六個月後才主張結婚時「無意識或精神錯亂」,已經來不及訴請「撤銷婚姻」,就只能選擇「離婚」一途。而且,根據民法第998條,婚姻撤銷之效力不溯及既往,亦即在常態回復後六個月內撤銷婚姻,可是在撤銷前的婚姻仍屬有效,這段時間中的夫妻行為仍屬合法。
另外一種可以消滅婚姻關係的情況是,夫妻之一方罹患重大不治的精神疾病,此時,他方依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8款,可以向法院請求離婚。所謂「重大不治」的意思,必須是該精神疾病症狀非常嚴重,而且依據現今精神醫學的治療水準,即使結合良善的藥物與生理治療、心理治療及其他治療方式,也難以改善患者的症狀。精神科醫師在這當中可以著力之處,就在協助判斷被鑑定人是重大不治、還是重大難治、或是雖不治卻不重大的類型。然而,「不治」與「難治」到底如何劃分,除了精神醫學的知識之外,應該也有法律政策的考量在內,因此較佳的做法是,司法精神鑑定醫師頂多會描述被鑑定人的精神疾病「重大難治」,並說明其難治的細節情形,再由法官依據法律政策判斷該「重大難治」是否已達「重大不治」的程度。但是,法官常常希望司法鑑定醫師直接表明是否「重大不治」,再由法官審酌其論述是否有理,最後決定是否接受鑑定醫師的結論。
詐病
詐病,通常有顯著外在利益誘因
新聞曾經報導過一名男子詐病成認知功能障礙,智商測驗不到五十分,成功騙過精神科醫師,取得中度身心障礙手冊,獲得高額保險金。保險公司後來懷疑內情不單純,遂向法院聲請對該男子進行精神鑑定。
這位男子在住院鑑定的期間,不僅生活能夠自理,與病友有說有笑,還打電話給友人簽注六合彩。男子詐病的事實被醫院識破,因為一個智商只有四十多分的人,一般而言自理能力會有減損的狀況,更不可能打電話簽賭。該名男子最後被以詐欺提起公訴,重判九年有期徒刑,並須歸還保險公司高額保險理賠金。
還有一則新聞報導的鑑定案例:一位二十歲年輕人與友人互毆,為了獲得更高的賠償金額,年輕人故意詐病對友人提出告訴,醫院檢查不出任何腦部異狀,但是這個年輕人呈現出「失智」的現象,法院遂安排住院鑑定(法律術語稱為「鑑定留置」)。醫院觀察年輕人的病情良久,發現年輕人其實尚有反應,也能夠與家人祕密互動,因此故意對他不理不睬,年輕人在欠缺他人協助處理自身需求(例如上廁所)的情況下,難以持續處在「失智」狀態,撐不了多久,年輕人自己大喊受不了了,主動承認自己詐病。
詐病的動機通常有明確的外來誘因,如詐領保險金、逃避兵役、獲得社福補助、規避刑罰、獲得藥物等。詐病者會故意假裝有身體或精神方面的疾病,採用的模式包括沒有病卻裝成有病、有輕微的症狀卻裝成很嚴重的症狀、有A病裝成B病等。也有些人不是自己裝病,而是將自己的子女弄成病人,如餵小孩吃瀉藥,或故意讓小孩長期受到感染等。
精神科醫師有必要了解詐病的行為,因為若是被鑑定人利用假裝的精神症狀規避責任或取得法律上的利益,將會破壞法律正義的實現。姑且不論詐病者裝成何種精神疾病,因為詐病行為本身動機判斷困難,有時候會被誤判為人為障礙症(動機在於扮演病人,就算沒有其他利益,甚至導致實質的傷害,亦然)、解離障礙症(例如解離性失憶或解離性身份障礙症,在第四章將有更詳細的解釋)或轉化症(自主運動或感覺功能的改變,但找不到生理上的支持證據,也沒有明顯的外在利益誘因或純為扮演病人的動機)。詐病的基本特質是有意識地製造假的或顯然誇大身體或心理症狀,且有明顯外在利益誘因。
為了犯罪而偽裝成精神病患者的案例,因為研究方法受限之故,並沒有現實社會發生機率的可靠統計,但或許沒有像在電影情節裡那麼戲劇化與普遍。要提醒讀者的是,精神疾病患者也會偽裝成沒病,因為擔心會被認為有病或失能,而受歧視、喪失工作機會、被剝奪法律上的能力或者遭到其他的損失。
需要提防詐病的情況有哪些?
在刑事責任能力的鑑定過程中,為了確定被鑑定人涉案時的精神狀態,醫師會先確定有無詐病的情形。要分辨出是裝病,還是真的生病,有經驗的鑑定醫師會發展出自己的經驗直覺,不會那麼容易受騙上當,畢竟要裝得像也並不容易。碰到下列的情形(但不限於此),醫師通常會考量有詐病的可能性:
‧牽涉到醫學與法律的情境(如法院、檢察官或律師轉介來檢查時);
‧個案主觀宣稱的壓力或失能,與客觀觀察到的症狀有明顯的差異(如傷害賠償、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勞保失能給付等等);
‧不配合診斷檢查且不遵從醫囑;
‧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
一般人都以為詐病不常見,其實並非如此。目前尚未有足夠的研究資料證實詐病有穩定的發生率,但臨床經驗顯示,男性的發生率高於女性,這可能與男性為逃避兵役、逃避刑罰或職業災害比率較高有關。
如果被鑑定人對醫師有欺騙的行為,就一定是詐病嗎?如果發現被鑑定人詐病的證據,能夠立刻斷定這病是裝的嗎?答案是不一定,因為證據跟詐病之間還有一段距離,需要推理、求證。詐病雖然不難被發現,卻也不容易被完全確認出來,除非裝不下去。不過話說回來,詐病者主動向醫師承認自己是假裝的機率並不高。
我在臨床真的遇過這樣的事情,在鑑定時我詢問被鑑定人為何要偷東西,他說:「我在便利商店突然看到關公騎著赤兔馬、眼裡冒著金光,手拿青龍偃月刀,對我大喝一聲:『偷!』我就偷了。」我很直接告訴他:「我作鑑定長達十幾年了,還沒聽過這麼離譜的描述。」他愣了一下,就改口說自己是在開玩笑。
如何知道是裝病?
1. 詐病有跡象可循
詐病的行為,不管「演」得如何維妙維肖,很多時候終究會有跡象可循,可以讓鑑定醫師從中找出矛盾點,揭穿詐病的企圖。
一般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知識,多來自於小說、電視、電影等通俗的刻板情節,鑑定時有時會遇見被鑑定人模仿戲劇節目的情節,將精神疾病的言行「演」得令人啼笑皆非。
其實,裝病有跡可循,每一種精神疾病都有其病程發展的典型情形,有些常態性的症狀表現,醫師根據臨床專業經驗(心中的那一把尺),可以判斷出被鑑定人所描述及表現的症狀是不是假裝的。
除非詐病者本身是精神科的醫療人員,長期觀察過各類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狀行為,否則不太可能會知道要裝到什麼樣的程度(不太誇張也不太輕微)才像真的,所以,「良好的」詐病其實並不容易。
一般來說,抑鬱、緘默、記憶缺損,最容易假裝;失智、幻覺及妄想,則不太容易;躁狂興奮狀態、意識障礙、僵直狀態,則最難裝得出來。
詐病者描述自己的疾病,常常主觀又模糊,抱怨頭暈、頭痛、脖子痛、下背痛、胸口不適、焦慮、憂鬱、記憶喪失等,當醫師追問沒有注意到的細節時,為了構思回答,反應速度常常因此變慢
(非精神疾病所致);而且有些詐病者報告的症狀與其客觀的舉止互相矛盾,或者自稱有幻覺或其他精神症狀,但事實上其描述的內容並非這些症狀的展現,嚴格而言也不是精神病理現象。也有人模仿家中其他人的精神疾病症狀,辯稱自己有家族病史,自己也有這種病,把病情描述得很嚴重,但是檢查時卻沒有發現該疾病所特有的生理現象。
醫師不會只憑被鑑定人的主觀口述就下定論。臨床上經常聽到被鑑定人指稱癲癇發作,導致作出犯罪行為,但是透過實驗室檢查卻又找不出任何異常,此時不排除有可能是想利用疾病來脫罪。
2.「我忘記了」常被當成理由
一個人若想說謊,最會說也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忘記了」。在面臨刑事責任能力的認定時,法官必須去釐清加害者是因為「不想說實話」,還是因為精神疾病而造成了失憶情況——一個人可以很輕易地說出「我忘記了」,但,是什麼原因導致「忘記了」,就必須區分出來。
臨床常見犯案嫌疑人以「記憶缺損」(失憶)做為聲請交付鑑定的理由,想以失憶來逃避刑責,以為靠一句「忘記了」就足以卸責。所幸從事司法鑑定的精神科醫師有判斷事實真相的理論依據,得以觀察、判斷出真假之間的線索。但是,根據心智科學對於人的記憶的研究,我們對於記憶有許多迷思,有時候客觀的情境證據更具有參考價值,而司法精神鑑定醫師也必須注意,不要讓自己落入同樣的迷思之中。
換一個比較輕鬆的說法來解釋,也就是如何判斷眼前的被鑑定人,是真的精神異常還是假的精神異常?精神科醫師練就一套內在武功祕笈,不是光憑對方一句「忘記了」就可以輕易被唬弄過去。精神科醫師會去了解「你是怎麼忘記的?」如果忘記的理由或過程太超乎常理,我們就會採取較為懷疑的態度。
記憶缺損(失憶)的現象確實是有可能存在,酒精或藥物也會造成記憶缺損,精神科醫師必須去查證,釐清是「當時哪個情境特別記不清楚」,還是「其他情境也有類似的反應模式」。而且,若目睹犯罪過程的證人之證言或其他影音證據顯示,犯案者雖然有酒醉,但是言行仍反應出對於周遭情境的理解與行為控制力,則必須懷疑其失憶有詐病的可能。
此外,在發生記憶缺損的情況之下,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受影響的程度有多少,以及在記憶缺損的情況之下,犯罪嫌疑人有無自由意思,均是調查的重點。上述使用酒精或藥物所造成的記憶缺損,也可能是犯案後記憶提取困難所造成,並非代表犯案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是此種情況已經不是詐病了,而是記憶缺損與刑事責任能力程度之間的議題了。
前言
法學與精神醫學的橋樑
【灰狗巴士上的分屍案】
在夜色中,一輛灰狗巴士以穩定速度緩緩行進。車上三十七名乘客正安靜地觀賞著電影,二十二歲的普林頓(化名)閉目養神,戴著耳機、聽著音樂,四十歲的萊維斯(化名)就坐在他身邊。車上氣氛祥和安靜,引擎聲呼呼作響著。
毫無任何預警,萊維斯沒有出聲,突然舉起手上的藍波刀,猛力刺向身旁的普林頓。萊維斯殺紅了眼,連砍六十刀,沒有喘息,他砍斷普林頓的頸部,割下血流滿面的頭顱,高舉示眾。
乘客們被這突然的殺人舉動嚇得尖叫,慌亂地擠在狹小的車廂內。司機立刻緊急停車,開...
目錄
【總序】視病如親的具體實踐 高淑芬
【主編序】本土專業書籍的新里程 王浩威、陳錫中
【自序】釐清迷思,尋求理解因應之道 吳建昌
【前言】法學與精神醫學的橋樑
司法精神鑑定不是辦案影集
正常與瘋狂的天秤
【第一章】司法精神鑑定的發展
這個行業是如何興起的?
司法精神鑑定的理論基礎
司法精神鑑定的倫理
司法精神鑑定醫師需具備的資格
【第二章】精神鑑定與生活法律
精神鑑定與刑事事項
精神鑑定與民事及行政法事項
【第三章】當精神醫學遇上司法
法律與醫學如何看待診斷與精神狀態
以醫師診斷為標準
是病人,還是壞人?
詐病
【第四章】精神疾病與犯罪的關係
思考障礙
情感障礙
知覺障礙
意志障礙
解離狀態
【第五章】刑事責任能力的鑑定
精神鑑定與法官心證
辨識能力
控制能力
原因自由行為
【第六章】民法意思能力的鑑定
行為能力
意思能力
臺灣成人監護制度
成人監護的評估項目
【結語】為了正義的緣故
【附錄】 延伸閱讀
【總序】視病如親的具體實踐 高淑芬
【主編序】本土專業書籍的新里程 王浩威、陳錫中
【自序】釐清迷思,尋求理解因應之道 吳建昌
【前言】法學與精神醫學的橋樑
司法精神鑑定不是辦案影集
正常與瘋狂的天秤
【第一章】司法精神鑑定的發展
這個行業是如何興起的?
司法精神鑑定的理論基礎
司法精神鑑定的倫理
司法精神鑑定醫師需具備的資格
【第二章】精神鑑定與生活法律
精神鑑定與刑事事項
精神鑑定與民事及行政法事項
【第三章】當精神醫學遇上司法
法律與醫學如何看待診斷與精神狀態
以醫師診斷為標準
是病人,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