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名稱:暗夜星光:告別躁鬱的十年
期待漆黑夜晚中,愈來愈多的故事被看見,彷彿布滿星光
拼湊出溫柔力量,明亮夜晚的恐懼
我不是想結束生命,我只想結束感覺不到痛苦的痛苦,感覺不到明天的絕望。
而我只剩生命可以結束。
高中時,躁鬱症不請自來,青春天翻地覆。
國內第一本青少年病人誌《親愛的我,你好嗎:十九歲少女的躁鬱日記》的作者思瑀,和躁鬱拔河十年了。在三十而立之前,思瑀回望過去,這十年的故事,好難說,也說不盡。
少女已長大,思瑀終於接受躁鬱強行參與她的人生,至今彷彿變為友伴。此刻,她希望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告訴社會,精神疾病僅是疾病的一種,如同感冒一樣平凡。
在本書中,她談到躁鬱患者常見的失眠、幻聽、自傷、自殺意念:
幻覺如此自然而真實,真實得讓我想開槍轟掉大腦,期待開槍後能偷得片刻安寧……
關於住院的日子,她說:
病友其實不可怕,她們都好想回家,好想「不像瘋子」。
關於工作,她說:
進入職場後,生病不再能夠蹺課,依然得拖著幾日沒睡的身體,繼續工作……
其實病友都想穩定工作,拚命地在病情與社會生活中取得平衡。
不管疾病如何攪擾,他們還是走過來了。不能說是勇敢,而是妥協、不願放棄、捨不得離去所愛。
期待這份書寫與手繪創作圖,能像黑夜中的星光,帶來點點希望:移除大眾對躁鬱症錯誤的刻板印象,從日常社交、家庭乃至工作職場,降低傷害,甚至成為病友的幫助。
飛吧!不管再怎麼疲憊,一定要繼續飛翔。沿途有美麗的日出,有落日的餘暉,有星夜的璀璨,有雨後的彩虹。努力飛吧,有一天一定能夠飛到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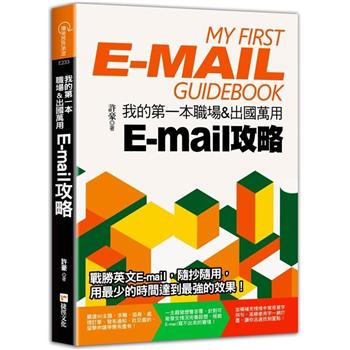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