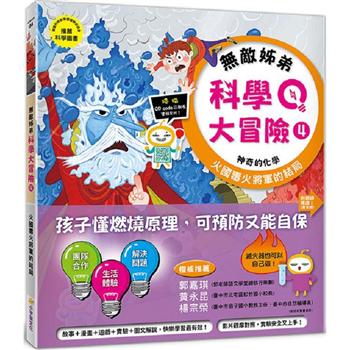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體驗的世界:精神分析的哲學和臨床雙維度的圖書 |
 |
體驗的世界:精神分析的哲學和臨床雙維度 作者:羅伯.史托羅洛、喬治.艾特伍、唐娜.奧蘭治 / 譯者:吳佳佳 出版社: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2-2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7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94 |
經典學派/大師思想 |
$ 332 |
Books |
$ 332 |
Books |
$ 332 |
Books |
$ 332 |
當代思潮 |
$ 370 |
中文書 |
$ 370 |
心理學理論 |
$ 378 |
精神分析 |
$ 378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420 |
心理諮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後佛洛伊德時代重量級精神分析著作
互為主體性學派是當代自體心理學和關係學派精神分析的重要基礎,也是推動當代精神分析理論研究的重要力量。該學派的基石性著作《體驗的世界》,則清晰地表達了互為主體性學派在西方哲學維度與臨床精神分析維度上的立場與觀點。
本書作者們在反思古典臨床心理學、自我心理學的局限後,借助了胡塞爾等人的現象學思想和寇哈特自體心理學的發展,針對所謂孤立心靈等概念,對西方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開足了批評的火力。他們認為,所有的心理過程,都源於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相互關係,而非孤立的心靈內在產物。孤獨的心靈並不是真實存在的。實際的人類生活及臨床精神分析過程,總是兩個主體甚至更多的系統一起交叉影響後的發展,這種發展以體驗的方式持續流動著。
這些思考將帶領臨床工作者以更開放的態度去傾聽案主的語言以及來自自己的聲音,而無論哪一方的視角,都會受到交互關係的影響,形成微妙的「共振」,進入同一個存在維度。採用互為主體的觀點,以精神分析方法嘗試理解並治療思覺失調、解離等嚴重精神病性狀態,因此成為可能。
這本後佛洛伊德時代的重要精神分析著作,是三十年合作研究的結晶,對學者與助人工作者而言,想了解當代的精神分析如何藉由與哲學的對話,重新審視人類心靈的深度與複雜性,並落實於臨床應用,本書是不可錯過的經典。
「現象學與精神分析都逼近了人類經驗的原初地帶。不論對於喜好歐陸哲學或心理治療、心理諮商的讀者來說,本書提供的是在人類經驗的根本處討論療癒的種種模式。」—李維倫
本書特色
★後佛洛伊德時代的重要精神分析著作,對精神分析以及當代哲學有興趣者,本書將是必讀作品。
★探討互為主體性理論在臨床精神分析中的應用,也是該領域第一本在台面世的著作。
作者簡介
羅伯.史托羅洛(Robert D. Stolorow)
精神分析學者,是美國洛杉磯當代精神分析學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Los Angeles)的創始成員,也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醫學院的精神醫學臨床教授,以互為主體性理論、後笛卡兒主義精神分析以及情感創傷等領域的研究聞名,並於2012年在國際精神分析教育論壇上獲頒漢斯‧勒瓦德紀念獎(Hans W. Loewald Memorial Award)。主要作品有《世界、情感、創傷:海德格和後笛卡兒主義精神分析》(World, Affectivity, Trauma: Heidegger and Post-Cartesian Psychoanalysis)、《創傷和人類存有:自傳式、精神分析式,以及哲學式的反思》(Trauma and Human Existence: Autobiographical, Psychoanalytic,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以及與人合著的八本著作。
喬治‧艾特伍(George E. Atwood)
紐澤西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心理學榮譽教授,也是美國紐約主體性精神分析研究學院(Institute for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ubjectivity, New York)的創始成員,著有《瘋狂的深淵》(The Abyss of Madness)以及七本與人合著作品。他與史托羅洛博士在將近五十年的學術生涯中聯手合作,致力於以現象學式探問的形式重新思索精神分析。
唐娜‧奧蘭治(Donna M. Orange)
精神分析師和哲學家,於紐約大學博士後研究計畫以及主體性精神分析研究學院擔任教職,著有《給臨床人員的讀本:當代精神分析和人文主義心理治療的哲學資源》(Thinking for Clinicians: Philosophical Resources for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Humanistic Psychotherapies)、《受苦的陌生人》(The Suffering Stranger)、《滋養臨床專家和人道主義者的內在生活》(Nourishing the Inner Life of Clinicians and Humanitarians)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吳佳佳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精神分析研究取向碩士,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心理學博士,德國海德堡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心理治療整合、精神分析與家族治療比較、心理創傷與心理韌性等。同時也是心理諮商師、譯者,參與中德家族治療等系列培訓專案的翻譯,出版譯著《精神分析複雜性理論》、《犯罪心理分析》等;發表學術論文《文化情境主義下的心理創傷與心理彈性研究進展》、《德國家庭治療師史第爾林論家庭治療的藝術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