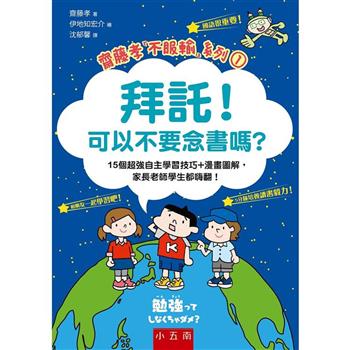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一直想對你說的圖書 |
 |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8):一直想對你說 作者:艾莉絲•孟若 / 譯者:王敏雯 出版社: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2-0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8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14 |
文學小說 |
$ 253 |
美國現代文學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英美文學 |
$ 288 |
文學作品 |
$ 332 |
大眾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一直想對你說
隱隱帶著嫉妒的愛,
總是最難以啟齒。
——令約翰‧厄普代克也懾服的短篇小說集
因為愛,有些話沒辦法說出口。有些則是錯過了時間,再也難以解釋或表白——無論是對母親、丈夫、兒女,長輩晚輩……或僅僅是只有一面之緣的陌生人。
在她第二部知名短篇小說集中收錄了十三篇故事,艾莉絲•孟若展現了精確的觀察、直截了當的散文風格、精湛的技巧,連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這樣挑剔的評論家也拿她與契訶夫相比較。在所有的故事中,在這些女性自己的過去與現在,以及可見的未來中,姊妹們、母親和女兒、姑姑、奶奶、朋友之間,同時散發著希望與愛、憤怒及和解。
作者簡介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
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文罕鎮(Wingham),就讀西安大略大學,《城堡岩海景》是她的第12本小說——同樣是短篇故事集。在她傑出的寫作生涯中獲獎無數,包括三座總督文學獎、兩座吉勒文學獎、Rea短篇小說獎(Rea Award for the Short Story)、萊南文學獎(Lannan Literary Award)、英國W. H. 史密斯書獎、美國國家書評人獎,及曼布克國際文學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她的文章散見於《紐約客》、《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格蘭塔》(Granta)等其他刊物,其作品亦已翻譯於13餘國語言。
譯者簡介
王敏雯
專職譯者,目前於台師大翻譯研究所進修中。酷愛翻譯,享受閱讀,同時認為翻譯是最美妙的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