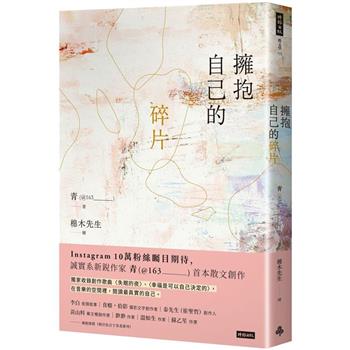在巫術仍盛行的中世紀,
唯有博學多聞、相信科學的劊子手能屢破奇案!
唯有博學多聞、相信科學的劊子手能屢破奇案!
面對疾病時,他們仰賴醫學;
但面對惡魔時,究竟該用刀劍阻擋?或以信仰為盾?
又或者,只有劊子手的屠刀能拯救他們?
為了還願,劊子手的女兒瑪德蓮娜和西蒙一同前往安德希斯朝聖,在當地修道院遇見孤僻的教士維吉留斯,並在他的實驗室見識到驚人景象――斗室之中,有一名美麗的女子。她一頭金髮,嘴脣豔紅如血,但口中說出的卻非人類語言,而是叮叮噹噹的鐘琴聲。「她」並非人類,是由齒輪和金屬組成的機器人。
同時,鎮上無端爆發傳染病,不管是鎮民或朝聖者皆一一倒下;而且,由修道院保管的聖體也在節慶前夕神秘消失!這些插曲使瑪德蓮娜與西蒙隱隱覺得,安德希斯沒有想像中單純。最糟的是,在他們拜訪教士後不久,他的實驗室就遭人闖入,教士助手被詭異的火焰燒死,維吉留斯失蹤,那具女機器人也不知去向。雖然不願做此揣想,但他們仍不免懷疑:難道,這起謀殺真的像鎮民所說,機器人獲得了生命,殺害助手、綁架它的創造者後畏罪潛逃?
黑暗的地窖中,衣裝華麗的「她」滾著裙下的滑輪,體內響起齒輪的嘎吱聲,嘴脣一張一闔,吐出惡魔的話語:
「為了獲得能拿來消磨時間的玩具,我已經等了好久、好久……」
名人推薦
推理小說評論者 曲辰
推理作家 呂仁
《開膛史》作者,心臟外科醫師 蘇上豪――共同推薦
一六六六年,笛卡爾已然去世,牛頓正坐在蘋果樹下,伏爾泰還未出世。那是啟蒙剛開始,但愚昧與迷信仍然統治歐洲的一年。奧利佛.普茨準確捕捉了那樣的氛圍,堆疊大量的細節成就一個科學與巫術還難分難解的世界,他將死亡擰成一條細線,將歷史吊在懸疑的邊境,你越讀就越心驚膽戰,直到偵探帶我們衝破了時代的桎梏,感受到那道名為理性的光芒,這才鬆了一口氣,捨得放下書回應夢的召喚。――推理小說評論者 曲辰
《機械魔女》維持本系列作的一貫風格,由三人組成的劊子手家族偵探團在十七世紀的巴伐利亞各城市裡涉險犯難,他們通常要對抗的是階級歧視、宗教壓力與偏執人心,這次還多了神祕的機械魔女!科學、宗教、推理的結合,讓人讀來欲罷不能!――推理作家 呂仁
奧利佛•普茨的作品融合瘋狂的快節奏、分量充足的冒險、睿智的內容,外加十七世紀諸多歷史細節。令人沉醉不已――《圖書館週刊》
作者讓那令人暈眩的氣味與感受變得栩栩如生,將我們從未見過的過往時空的真實面貌搬上檯面。――《火的祕密》作者,暢銷作家凱瑟琳•納薇禮
在這個被一絲不苟地塑造出來的精湛故事中,一字一句都可能是關鍵線索,而每個角色都非常有魅力。不深陷其中、忍不住想幫他們解開謎團,真是不可能的任務。――歐普拉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