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非正規反抗:池袋西口公園8的圖書 |
 |
池袋西口公園(8):非正規反抗 作者:石田衣良 / 譯者:江裕真 出版社: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10-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非正規反抗:池袋西口公園8
我們的世界完全分成了兩半,
有安全網的人與沒安全網的人;
掉落下去的人只能設法自己保護自己了……
任務1:獨力扶養小孩、連睡覺時間都沒有的單親媽媽小由,因為一次疏於照顧就成了全民公敵——無人憐憫無人伸援,還成為色情產業獵人物色的目標。同樣身為單親媽,阿誠接到老媽的委託,非得拉小由一把不可。
任務2:企業家之子號召成立「池袋清潔隊」,邀請志工上池袋街頭撿垃圾、做環保,然而他的身分自然不會不引來小混混的覬覦;阿誠接到和文父親的委託,從綁匪手上救回兒子——但綁票案背後卻出人意料地不單純。
任務3:透過G少女,阿誠接到來自小遙的委託:前男友拿她的SM照片勒索,威脅要寄給她的警官老爸。但才答應下來,阿誠下一刻卻被熊一樣的前警官襲擊。有了前柔道冠軍當搭檔,這次事件應該能輕鬆解決吧?
任務4:阿誠從來不曉得,日本的派遣員工竟過著如此非人的生活:遭派遣公司層層剝削,反抗者甚至遭到人身攻擊!穿著法式女僕裝的東京打工族工會代表萌枝,委託阿誠找出襲擊事件背後的真凶,阿誠再次深入虎穴——但結局出人意料地再度大轉彎,萌枝對抗的邪惡組織竟是……
看似拯救M型社會底層小人物的4篇故事,實則瀰漫濃濃親情——石田衣良信手捻來新世代對老一輩的反抗,所有夾雜著毀滅的新生,正是希望的嫩芽能出頭的機會之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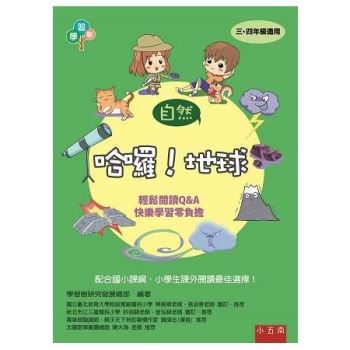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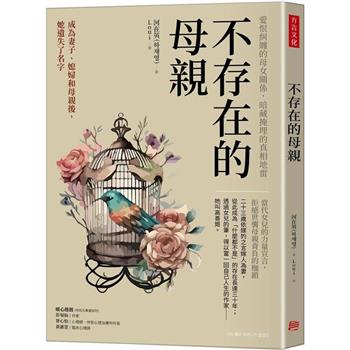






![圖解 適齡教養 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暢銷修訂版] 圖解 適齡教養 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暢銷修訂版]](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6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