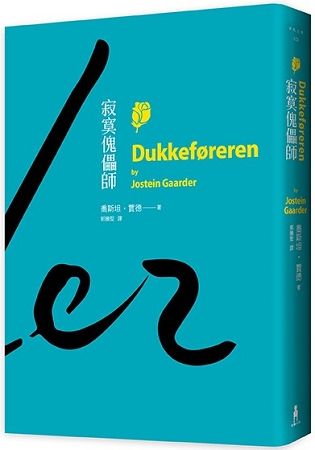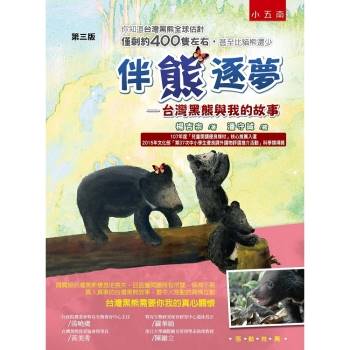哥特蘭島,二○一三年五月
親愛的亞格奈絲,我是要寫信給妳的。妳記得嗎?或者說,我總該試著寫信給妳。
我正坐在波羅的海的一座小島上,眼前是張小書桌,筆記型電腦擺在桌上。我在筆電的右邊擺了個大雪茄盒,裡面裝著協助我增強記憶所需的一切。
旅館房間夠大,讓我能夠在思索該如何開始敘述之際從椅子上起身,在松木毛地板上踱步。我只需要穿過一套沙發與茶几組;我時而經過位於桌面邊緣與兩張紅色手扶椅之間那張狹長的柚木桌,時而穿越桌子與紅色沙發之間那道同樣狹窄、宛如細長走廊的空間。
他們給我位於轉角的房間,能從兩個方向眺望戶外景色。從其中一面向北的窗口,我能俯望建於漢薩同盟時期的老鎮上橋梁密布的街道;從另一面向西的窗口,我能直直朝下俯看榆樹谷,視野直探海面。天氣很熱,我讓兩面窗戶都敞開著。
我已經站了半個小時,俯望著經過我下方街道的人群;大多數人身穿洋裝、短褲或寬鬆的短袖上衣。典型五旬節的觀光客。許多人樂於手牽著手、兩兩並肩而行;然而,也有幾群人數較多、嘈雜喧鬧的遊客。
我倒是可以破除關於青少年比我所屬年齡層的人更會吵架的迷思。只要中老年人成群結夥地出現、或是心裡有點不爽,他們會像青少年一樣煩人。
或者說,他們的本性和青少年一模一樣:看過來!聽我的!現在我們大家不是玩得很嗨嗎?
我們身上的人性,並不會隨著年齡漸增而消失;我們和它一同成長,它在我們身上只會更加明顯。
我對位於自己下方一層樓半街景的視角,很是喜歡;它是如此之近,我已非常接近那些路人。某些氣味向我撲來;人體也是會散發氣味的,無風的夏日,人潮洶湧的狹窄街道上,尤其明顯。此外,還有人拿著點燃的香菸;我感到香菸釋出的煙霧,直鑽進鼻子裡。不過,同時我離橋面的高度恰到好處,被我偷窺的人不會向上瞄,進而發現我。我站在一道藍色簾幕後面,半掩著身子;三不五時,一陣風突然襲來,窗簾被吹出窗口,搖曳著。
觀察別人,而不被別人觀察;我得以在離地面一層樓半的高度,享受這份特權。
我凝視著遠方閃亮水面的帆船;來自這扇窗,柔和的鼻息,偶而會使街窗的窗簾隨之飄動。
最近半小時以來,我已經留意到三艘帆船。即使只吹著微風,有時甚至幾乎寂靜無風,今天的天氣仍然燦爛;只不過,這並不是那種可以揚帆出海的天氣。
今天可不只是五旬節而已;今天可是五月十七日,國慶日。一想到這點,我就覺得有點憂鬱;這幾乎就像是在陌生人當中過生日。沒人祝你生日快樂,也沒人為你唱生日快樂歌。
這裡也沒人唱國歌。我連一面挪威國旗都沒看到。不過,我倒是記得:旅館床上,覆蓋著一塊布幔。它和積雪的格利特峰一樣,都是白色的。我是說:紅色的房間、白色的床單,以及淺藍色的窗簾。這是為了標示挪威國旗。
為了標示日期,我同時註明:我振筆疾書之際,距我們在艾蘭道爾見面,已過了一個月。
另外,幾小時後,妳會去找派勒。我得說:你們真是一拍即合。
在此之前,我們只見過一次面;那是一年多前,二○一一年聖誕夜的前一、兩天。我試圖在這裡說明的,就是第一次見面的來龍去脈。妳要我為我的所作所為給個說法。我會盡己所能,回答這個問題。我也認為,趁現在反問妳一個問題,正是時候:
我是很孩子氣,但妳也留住我,不讓我掙脫、離開。至今,這仍是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小謎團;那天下午,使人大吃一驚的,可不只有我而已。
我相信,圍桌而坐的所有人都可以簽字、證明這點;也許,許多人和我想的一樣:妳為什麼要阻止我?為什麼不讓我走?
可是,我該怎麼開始呢?
我可以按照時間先後順序,描述我在哈林達爾(Hallingdal)的成長,介紹我如何隨著時間成為今天的自己;或者,我可以反其道而行:我可以從一、兩件自己就在今天下午、在島上所體驗到的異象開始¬¬¬¬——畢竟,它們必須被包括在我的敘述裡——往前連結到我們一個月前在艾蘭道爾(Arendal)的會面,而敘事軸則要先拉回一年多前、那個天翻地覆的下午。亞格奈絲,那是你人生中最沉重的日子之一。然後,我會將敘事軸完全帶回艾瑞克‧路德因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葬禮。這樣的倒敘法,最後將歸結到對我孩提時代經驗的描述;這也許能開啟一絲理解,甚至能在書寫完畢後,得到諒解。
我們該怎麼做,才能最輕易地了解人生旅程呢?是應該從頭做總結,還是該從記憶最深刻、清晰的今天說起,然後再憶及一切的開端?第二種方式的弱點在於,人生中各環節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必然導致某些情境的原因。我們始終面對某些關鍵的抉擇;因此,從影響回推到原因是不可行的。
要想證明一個人怎麼會成為現在的樣子,是不可能的。許多人偏偏嘗試做到這一點,但充其量只是在自己的人性底下,多畫上兩條橫線罷了。
我又駐足窗前。風平浪靜,那三條帆船還在原地閒晃。我知道這是個很詭異的比喻,但是它們讓我想到我們三個人——想到妳和我,還有派勒,一定會提到他的。
這很窘,不過一首主日學校老歌,開始從我腦海深處哼唱起來:我的船是如此渺小,而大海是如此寬廣……
我做出決定,要從這趟航程的中途開始說起。我要從我在艾瑞克‧路德因葬禮上遇見妳表哥開始說起。從這裡,我將跟隨幾條脈絡,它們將直接把我牽往約十年後、我們的第一次相遇。我在哈林達爾受到的創傷,就只能在另一條脈絡來談了。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寂寞傀儡師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寂寞傀儡師
《蘇菲的世界》《紙牌的祕密》《庇里牛斯山的城堡》作者最新作品
我們來說一個關於語言、說故事的力量,與努力不要寂寞的故事
這是一位傀儡師,寫給一名陌生女子的長信。
天亮之後,當她讀完這封奇妙的告解信,她能否了解一個寂寞的獨身男人為何熱中於語言學,而他最知心、博學的朋友,則是一具偶人?
艾瑞克‧路德因教授的告別式,並不是雅各參加的第一場陌生人的葬禮。事實上他有一整個抽屜的雪茄盒,拿來收藏他參加過的訃聞剪報。
然而這場葬禮之所以特別,是他在葬禮上認識了路德因一家人,並因此曝光了他悉心保守的秘密——
他喜歡參加大型告別式。他喜歡混雜在人群中,感受大家族彼此支援的深情實意;而在這樣的場合中,只要稍微運用蒐集資料的能力,你能表演得頗有那麼回事,彷彿與死者共享著某種秘密連結……
熟稔斯堪的那維亞語言、哲學、神學和文學的賈德,這次透過一個著迷於日耳曼語系的高中講師——雅各,與他的傀儡搭檔派勒,哥倆好常常巡迴參加各種講座,與有興趣的聽眾分享北歐神話、語言,與日耳曼語系的深刻關聯——談論人們對歸屬、對話、親族之愛的渴望,這份渴望促使書中主角雅各不斷參加陌生人的告別式,編織一個又一個關於愛與理解的故事。
但這樣的欺騙總有遭揭穿的一天;但當這一天到來,卻也讓他有機會一吐自己的一生。
作者簡介:
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
喬斯坦‧賈德,生於1952年8月8日,挪威的世界級作家。就讀奧斯陸大學時期,主修斯堪的那維亞語言、哲學、神學和文學,曾任文學與哲學教師。於1986年出版第一本創作《賈德談人生》,如今已是當代最重要的北歐作家。
賈德擅長以對話形式述說故事,能將高深的哲理以簡潔、明快的筆調融入小說情境。他於1991年成為全職作家,同年發表的小說《蘇菲的世界》享譽全球,被翻譯為五十多種語言,全球銷售量超過三千萬本。他的作品動人心弦,啟發無數讀者對於個人生命、於歷史中的定位以及浩瀚宇宙的探討。其他作品包括《沒有肚臍的小孩》、《青蛙城堡》、《紙牌的祕密》、《依麗莎白的秘密》、《西西莉亞的世界》、《我從外星來》、《瑪雅》、《主教的情人》、《馬戲團的女兒》、《橘子少女》、《庇里牛斯山的城堡》等。
賈德除致力於文學創作,啟發讀者對於生命的省思外,對於公益事業亦不遺餘力。他於1997年創立「蘇菲基金會」,每年頒發十萬美金的「蘇菲獎」,鼓勵能以創新方式對環境發展提出另類方案或將之付諸實行的個人或機構。
譯者簡介:
郭騰堅
1986年出生於臺中市,臺灣大學英國文學學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翻譯學碩士,瑞典商務院認證譯者,現居斯德哥爾摩。譯有《永不拭淚三部曲》(三采出版)、《我,跟自己拚了!》(三采出版)、《四百歲的睡鯊與深藍色的節奏》(大塊出版)等書。
TOP
章節試閱
哥特蘭島,二○一三年五月
親愛的亞格奈絲,我是要寫信給妳的。妳記得嗎?或者說,我總該試著寫信給妳。
我正坐在波羅的海的一座小島上,眼前是張小書桌,筆記型電腦擺在桌上。我在筆電的右邊擺了個大雪茄盒,裡面裝著協助我增強記憶所需的一切。
旅館房間夠大,讓我能夠在思索該如何開始敘述之際從椅子上起身,在松木毛地板上踱步。我只需要穿過一套沙發與茶几組;我時而經過位於桌面邊緣與兩張紅色手扶椅之間那張狹長的柚木桌,時而穿越桌子與紅色沙發之間那道同樣狹窄、宛如細長走廊的空間。
他們給我位於轉角的房間,能從兩個方向...
親愛的亞格奈絲,我是要寫信給妳的。妳記得嗎?或者說,我總該試著寫信給妳。
我正坐在波羅的海的一座小島上,眼前是張小書桌,筆記型電腦擺在桌上。我在筆電的右邊擺了個大雪茄盒,裡面裝著協助我增強記憶所需的一切。
旅館房間夠大,讓我能夠在思索該如何開始敘述之際從椅子上起身,在松木毛地板上踱步。我只需要穿過一套沙發與茶几組;我時而經過位於桌面邊緣與兩張紅色手扶椅之間那張狹長的柚木桌,時而穿越桌子與紅色沙發之間那道同樣狹窄、宛如細長走廊的空間。
他們給我位於轉角的房間,能從兩個方向...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喬斯坦‧賈德 譯者: 郭騰堅
- 出版社: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1-04 ISBN/ISSN:978986359490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開數:15*21cm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世界文學> 其他各國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