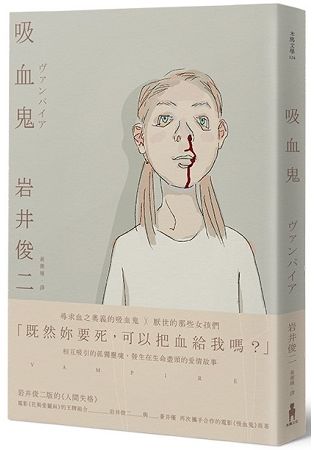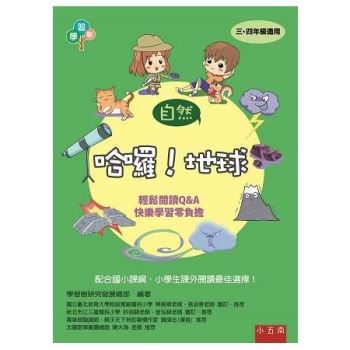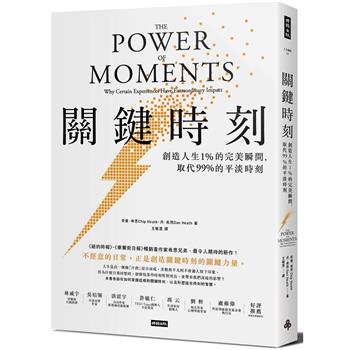我遇見打算自殺的女子。她是一位體態十分豐腴的年輕女孩。女孩茫然望著橋下。我心想:啊啊,她一定打算尋死吧。那樣的體態有辦法跳下去嗎?不對,依她的體型來看,只要稍微把身子探出橋外,她反而會因為站不穩而順著身體的重量一路向下。
我戰戰兢兢地試著主動開口。
「妳知道這座橋的名字嗎?它叫鋼鐵工人紀念第二海峽橋,於一九五八年興建過程中發生坍塌意外,奪走二十七名工人的性命。據說橋的名稱就是來自於那場意外。原本的橋名是第二海峽橋,後來為了悼念死亡的工人,因此改成鋼鐵工人紀念第二海峽橋這個好長的名字……妳想尋死嗎?」
女孩回過頭來,以空洞的眼神看著我。
「妳想尋死嗎?」我再問了一次。
女孩點頭。
「是嗎?原來妳想尋死啊……這樣啊。」
大型拖車從我們旁邊開過,突然捲起一陣風吹上我們兩人。我們如果是單薄的紙片,早就被吹下橋去,在空中飛舞了吧;可惜我們是血液、骨頭與肉構成的笨重生物,跌下橋也只會順著萬有引力定律變成垂直落下的自由落體,不會受到大氣太多的影響。雖然橋下是水,卻也無法存活。
女孩抓著橋樑欄杆避免跌下去。咦?不是想死嗎?看樣子女孩雖然想死,但是那副血肉之軀還在頑強抗拒死亡嗎?可是,不好意思,那些血是我的。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這樣說:
「如果妳要死的話,可以把血給我嗎?」
「咦?」
「我是吸血鬼。」
她愕然注視著我的臉好一會兒,表情寫著:「現在在我眼前的是什麼人?」她想了半天卻沒有線索,想開口說話卻欲言又止。
我繼續說:
「嘿嘿,我可以協助妳死去。嘿,至於代價,啊哈,我想要妳的血。呵,不行嗎?嘿嘿!」
我很緊張,卻在不該笑的時候控制不住一直笑;我不曉得為什麼無法阻止自己發出「嘿」或「呵」等無意義的笑聲。我明明很認真。我擔心這樣下去她只會當我是在開玩笑。可是,她卻沒有這麼認為。
「你是死神?來帶我走的?」
「不是,欸,嘿嘿……不是死神……哈……我是吸血鬼。」
結果事到如今我仍不清楚她當時是如何解讀,總之她同意了我的提議。
「你想要血?那麼就給你吧。我已經不需要了。」
她的說法聽來就像是要送我某個她已經用不到的家具。
「妳真的聽懂我的意思了嗎?我說的可是妳的血,鮮血。」
「我懂。我要怎麼做?」
我亢奮過了頭感到暈眩。我弄到血了!此時我才發現在此之前的我是蛹。蛹夢見的是蛹,不會夢見自己變成蝴蝶;一旦變成蝴蝶,便再也記不起蛹的過往了;蝴蝶做的是蝴蝶的夢。這是大自然的真理。
「說得也是。妳可以等我一個星期嗎?我要做不少準備。妳家呢?有家人嗎?妳一個人住?總之要做不少準備。我會打電話給妳。告訴我妳的電話號碼。不……」
我從口袋抽出手機,交給她。
「妳拿著這個。我會打電話到這支手機,響一聲就切掉,連續三次以上,這樣子妳就知道打電話的是我。下次碰面時再還給我就好。」
把手機交給對方,這是多麼衝動的行為啊。
可是在那當下,想要說服她相信我,唯有這個辦法了。
我叫她上車,開車送她回家。隔天,我買了剛上市的iPhone。我用新買的iPhone打電話到我交給她的手機,不停地響一聲就掛斷。她終於接起電話。
「欸,是我。妳叫什麼名字?」
「我?何必知道名字呢。」
「欸,好吧。下星期天有事嗎?」
「沒事。我已經沒有什麼事要做了。除了跟你的約定之外。」
「這樣啊。妳在等我嗎?那麼我得加快腳步才行。」
「也不用那麼趕。」
「是嘛、是嘛。欸,不過我會在下週之前做好準備。問題是地點。可以用妳家嗎?」
「不行。家人都在。不過我知道一處好地方,那是我公司閒置的空間,不會有人來,很安全。」
「這樣啊。那麼就選在那裡吧。」
居然拜託犧牲者找地點,我現在想來才覺得這計畫未免太過粗糙。沒辦法,這是我的第一個任務。
星期天早上。
我開著自己的車去她家接她。
她住的那棟房子宛如溫哥華肖尼希區的豪宅。從建築物出來的她稍微打扮了一番,就像待會兒要去約會的模樣。
半路上她說想喝咖啡,於是我們去了一趟星巴克,但我留在車上。我不想被人看到我們兩人在一起。過不了多久,她兩手拿著咖啡與紙袋回來。她從紙袋裡拿出甜甜圈,在重新繫上安全帶時已經吃光,很快地又從紙袋中拿出第二個,在我發動車子之前已經吃完。怪不得會胖。
「妳喜歡吃東西?」
「喜歡。」
「欸,反正是最後機會,要不要吃些喜歡的食物?有沒有什麼想吃的?」
「你不是不希望被人看到嗎?」
「也是。不如我們假裝不認識,各自在不同的座位上吃飯吧?雖然這樣有點孤單。」
「不要緊,我這個人吃東西時只想著吃這件事。你請自便。嘿,既然都要吃了,要不要去中國城?」
我們改變路線一路直奔中國城。她選了一家沒有醒目裝潢的寒酸中餐廳。聽說那一家最好吃。然後根據她的說法,中國菜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料理。我說有些中國菜有怪味,她說那會讓人上癮。
我們分別進入餐廳。她先進去,我晚了五分鐘才進去。我戴著毛線帽與扮裝用的眼鏡在餐廳裡四處張望,假裝不認識她。中國人服務生過來問我是一個人嗎?我點頭。很不巧店裡客人很多,結果我被迫與她併桌。我們只能面面相覷,露出苦笑。服務生拉著飲茶推車一車接著一車來到桌前。她沒有自己選菜,只讓服務生把一道接著一道的推薦菜放在桌上。
她將小餃子一顆接著一顆放進嘴裡,說:
「這種點心不管有多少我都吃得下。」
「哪一道菜好吃?」
「全部都好吃。」
於是中國人女服務生也用帶有濃濃中國腔的英文說:「全部都好吃噢。」並且把蒸籠一個接著一個擺在桌上。
「妳好,我叫賽門。」我始終假裝與她是第一次見面,主動與她握手。她有些困惑地說:
「你好,我叫瑪特露西卡。」
瑪特露西卡就是俄羅斯套疊娃娃;一個娃娃內嵌入好幾個同樣形狀的胖女孩娃娃。
看到中國人服務生走開,我小聲問她:
「為什麼叫瑪特露西卡?」
「因為我看來就像瑪特露西卡。」
她從包包裡扯出照片排列在我面前。那是七張連續照片。第一張是骨瘦如柴,或許不到三十公斤的模樣。第二張是稍微偏瘦,像模特兒那樣勻稱,很適合穿迷你裙。第三張是中等身材的健康模樣。第四張也許有點偏胖,腹部與腰部一帶稍有肉。第五張是現在的她吧。第六張更胖。第七張大概超過一百公斤,超級胖。她說這是在短短一年之內的變化,就像月圓月缺一樣週期循環。我試探地問她這就是她想死的原因嗎?她說她自己也不清楚原因,她說有一股肉眼看不見的神祕力量讓她忽胖忽瘦,讓她想著要自殺……。
「你覺得我這女人很會吃吧。」
「是啊。我覺得很感動、很佩服。」
「我聽說鵝肝醬是讓鵝吃下大量飼料養成的。」
「我記得鵝肝醬是肝臟,沒錯吧?」
「沒錯,是肝臟。我想我的肝臟一定也很美味。你想吃的話請儘管動手。」
「叫我動手……意思是叫我吃嗎?」
「反正我都死了,隨便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我對肝臟沒興趣。」
瑪特露西卡工作的運輸公司有幾間倉庫。她選擇其中一間當作我們倆進行儀式的場所,也就是她要死去的地方。
她搖晃成串的鑰匙,發出金屬撞擊聲,以熟練的手勢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她說她為了今天,私自打了備用鑰匙。她說:「這地方很隱密吧?」沒錯,這空間的確隱密,令人有些不舒服。她說這間倉庫偶爾有庫存貨物進出,不過幾乎不會有人出入。她的公司有好幾處這樣的倉庫,她的同事也都說,就算殺了人放在這裡也絕對不會被發現。這兒就是這樣的地方。
「也許真的有屍體呢。」瑪特露西卡竊笑。
這種地方的確很可能有屍體。牆邊有一台白色的臥式冷凍櫃,裡面是空的。
「你不覺得這看起來像白色棺材,很可愛嗎?」
那看來的確像白色棺材。雖然我不覺得可愛,倒也覺得很美。
「我死了之後,可以把我放在這裡面嗎?這樣可以死得很美吧?」
我讓她躺在冷凍櫃的上蓋上試試。這樣一躺,就像躺在手術台上,雖然方便動手,可是等她死了之後,我必須把她挪開、打開冷凍櫃上蓋,才能夠將她重新安置;沒什麼力氣的我扛得起體型這麼龐大的女孩嗎?問題是冷凍櫃內很深,如果先讓她躺在裡面,又不方便動手。我和她一起試了幾次,邊笑邊嘗試。
「妳可以讓我扛扛看嗎?」
我嘗試實際扛起她。好重……不過能夠支撐二十秒左右。最後我將她翻了一圈放回冷凍櫃上。我氣喘吁吁,花了一分鐘時間才恢復呼吸。
「嗯,不過,船到橋頭自然直。」
我回頭,發現她看我看得出神。
「怎麼了?」
「你或許是死神,不過對我來說是白馬王子。」
錯了……我不是死神,我是吸血鬼。
我啟動手機的錄影功能,想留下她最後的身影當作紀念。
「請說說妳的遺言。」
「遺言?也是……我沒有要說的。你叫我說說遺言,我想不出來要說什麼。我在家裡留下遺書才過來的。我寫了爸爸、媽媽,對不起。你們好不容易生下我,我卻比你們兩人早死,這樣很不孝吧?我雖然也想要活得更久……也想結婚……我也想穿婚紗,想去南方島嶼度蜜月。比方說新喀里多尼亞之類的地方……」
明明說過想不出來要說什麼,結果她的遺言足足說了二十分鐘。
儀式十分簡單。我割開她的手腕,讓鮮血流進燒杯裡。靜脈被割斷,鮮血由深及動脈的傷口大量湧出。
「不痛嗎?」
我摸了摸她的頭髮。
「吻我。」她說。
我吻了她。我察覺她嘴唇的溫度逐漸變冷;不是因為倉庫的冷空氣,而是失血造成。
「好冷……好難受……」
說完,顫抖了幾下後,瑪特露西卡就嚥氣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目睹一個人的死。
我從她身上取得三公升的血液,分裝在一公升容量的瓶子裡。
血。從她身上採得的,她的生命。血即是生命。這是生命的具體模樣。
我喝了一點試試。
……好喝!好喝!真好喝!
一旦喝了就停不下來。她的生命融入我的體內這件事讓我渾身酥麻。紅血球的壽命極短,一百二十天就會死去,所以血液最好趁新鮮喝下。我一眨眼就喝完一瓶,緊接著抓起第二瓶。味道如何不重要,我的全身細胞、血紅素、粒線體都在亢奮顫抖。事實上我的身體顫抖了無數次。這是我期待已久的東西,而它也沒有背叛我。血即是生命。她的生命在此刻正式由我繼承。妳從今天起和我一同活著──我有驚人的判斷力,能夠接受這個價值觀。我彷彿在這瞬間獲得了啟示。可是我不能太悠哉。我按照練習的流程把她塞進冷凍櫃裡,卻發生意想不到的情況。噢,天啊。瑪特露西卡漏出屎尿了,而且是一口氣兩者都漏了出來,分量非比尋常,遲遲沒有停止的跡象。雖說這是死後正常的生理現象,但我無法忍受。臭到受不了。
我連忙關上冷凍櫃的上蓋。生理現象仍在裡面持續進行吧。即使死了,人類還是有許多要做的事;接下來必須腐爛,必須被蟲蛀蝕。瑪特露西卡在這部分有幾分幸運,因為沒有人會打擾她。屎尿也一併冷凍的話,也不會有人介意那股味道了吧。
瑪特露西卡永遠安息了。
我止不住亢奮,收拾東西,帶著她的包包離開。儘管外頭烏雲滿天,或許是一直待在昏暗的倉庫裡,我感覺戶外的光線刺眼到讓我甚至睜不開眼。
我發動車子。尚未停止顫抖。我開車蛇行,差點就要開上對向車道了。好危險。我先把車停下。顫抖還沒能夠平息,甚至比剛才更嚴重了。這是喝血引起的反應嗎?我還在驚訝,突然一股吐意湧上,我奔出車外,一口氣跑向面前的海邊,跑下沙灘,跳進大海,將腰部以下泡在海裡,同時激烈嘔吐。剛喝下的血原原本本都吐了出來。
啊啊,怎麼會這樣。好不容易喝到的血。
我搖搖晃晃走向海浪與沙灘的交界,勉強回到岸邊,途中差點溺水。我的身體仍在顫抖。我終於察覺這個顫抖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殺了人。
殺人。
被害人是瑪特露西卡,本名瑪莎.路金司基。她的遺體被警方發現,已是六年之後的事。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吸血鬼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47 |
日本文學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36 |
日韓文學 |
$ 237 |
日本現代文學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日本文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吸血鬼
★電影是由日本、美國、加拿大合作,岩井俊二包辦了原作、腳本、導演、音樂、攝影、編輯與製作人。
★日本讀者譽此書為「岩井俊二版的《人間失格》」!
血即是生命。
而生命,只是寄生蟲的另一種說法吧。
(相互吸引的孤獨靈魂,發生在生命盡頭的愛情故事)
「既然妳要死,可以把血給我嗎?」
看似普通、人畜無害的高中老師賽門.威廉斯,照顧著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母親,但其實他是位吸血鬼。從他有記憶以來,他就渴望鮮血、想喝血,而且他只喝年輕女性的血。吸血的衝動像性慾,又像是潛伏在他心中的病毒,當他對血的慾望高漲到難以壓抑時,唯有喝下血才能解除。
賽門流連在經常有人自殺的橋上與自殺網站,為了尋找想結束生命的年輕女子,他幫助她們結束生命,代價就是把血給他。
他陪著想自殺的女孩度過她們人生的最後一天,吃她喜歡的美食、跳最後一支舞、拍下最後遺言……然後割開她們的手腕,讓鮮紅的血靜靜流入燒杯中……
交換生命與血的最終交易所交織出人與人的奇妙關係,在人類極限狀態下所萌生的愛苗,岩井俊二結合古老傳說的角色「吸血鬼」與現代社會才有的產物「自殺網站」,創造出一個唯美又幽暗的世界。
岩井俊二以個人獨特的美學與世界觀魅惑讀者,將病態物哀的日本美學發揮到淋漓盡致!
★日本讀者心得:
「此作品可說是岩井俊二版的《人間失格》。」
「與一般的吸血鬼不一樣,非常有趣。」
「平鋪直敘的文字,卻充滿想像力。」
「不是驚悚的恐怖小說,而是深刻描寫孤獨之人的犯罪心理。」
作者簡介:
岩井俊二(Iwai Shunji)
1963年1月24日出生於日本仙台市。橫濱國立大學畢業。
主要電影作品包括《情書》《燕尾蝶》《四月物語》《青春電幻物語》《花與愛麗絲》《吸血鬼》《花與愛麗絲殺人事件》《被遺忘的新娘》,紀錄片作品《市川崑物語》、《少年們想從側面看煙花》等。
曾以《If如果:升空的煙花,是從下面看、還是從側面看?》獲得日本電影導演協會新人獎,時隔24年,故事再度於2017年改編成動畫電影「煙花」。
近期小說作品《庭守之犬》、《被遺忘的新娘》將陸續由木馬文化譯介出版。
譯者簡介:
黃薇嬪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大一開始接稿做翻譯,到2018年正好滿20年。
兢兢業業經營譯者路,期許每本譯作都能夠讓讀者流暢閱讀,主打低調路線的日文譯者是也。
TOP
章節試閱
我遇見打算自殺的女子。她是一位體態十分豐腴的年輕女孩。女孩茫然望著橋下。我心想:啊啊,她一定打算尋死吧。那樣的體態有辦法跳下去嗎?不對,依她的體型來看,只要稍微把身子探出橋外,她反而會因為站不穩而順著身體的重量一路向下。
我戰戰兢兢地試著主動開口。
「妳知道這座橋的名字嗎?它叫鋼鐵工人紀念第二海峽橋,於一九五八年興建過程中發生坍塌意外,奪走二十七名工人的性命。據說橋的名稱就是來自於那場意外。原本的橋名是第二海峽橋,後來為了悼念死亡的工人,因此改成鋼鐵工人紀念第二海峽橋這個好長的名字……妳想尋死嗎...
我戰戰兢兢地試著主動開口。
「妳知道這座橋的名字嗎?它叫鋼鐵工人紀念第二海峽橋,於一九五八年興建過程中發生坍塌意外,奪走二十七名工人的性命。據說橋的名稱就是來自於那場意外。原本的橋名是第二海峽橋,後來為了悼念死亡的工人,因此改成鋼鐵工人紀念第二海峽橋這個好長的名字……妳想尋死嗎...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章 記憶
第一章 路嘉
第二章 海倫
第三章 艾瑪
第四章 瑪特露西卡
第五章 海佳
第六章 娜莎莉
第七章 水母
第八章 雷恩菲爾德
第九章 蘿拉.金
第十章 神野美娜
第十一章 瓢蟲
第十二章 生命
第十三章 吸血鬼
第一章 路嘉
第二章 海倫
第三章 艾瑪
第四章 瑪特露西卡
第五章 海佳
第六章 娜莎莉
第七章 水母
第八章 雷恩菲爾德
第九章 蘿拉.金
第十章 神野美娜
第十一章 瓢蟲
第十二章 生命
第十三章 吸血鬼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岩井俊二 譯者: 黃薇嬪
- 出版社: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3-14 ISBN/ISSN:978986359504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開數:15*21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