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請林水福教授重新翻譯,華文世界最新譯本
※ 英國衛報評選為死前必讀小說之一
三島由紀夫──
書中男主角為小說家,對小說與模特兒的關係、小說與人生的糾葛等,點綴著類似文學理論的地方,這在川端的其他作品中是不易見到的。……由於這部小說,讓我明瞭川端文學的許多祕密。
明明聽佛寺108響的除夕鐘聲是為了消憂解愁,送走舊的、迎接新的,
鐘聲卻勾起了他們的往日回憶,與愛的美麗與哀愁。
已有家室的作家大木年雄與十六歲的上野音子有段戀情,音子懷孕,小孩因早產而過世。音子大受打擊,服安眠藥自殺未遂、精神異常而住進精神病院。這段苦戀無疾而終,音子的媽媽帶著音子移居京都;大木將他與音子的戀情寫成小說《十六、七的少女》,這本小說成了大木最受歡迎、最長銷的著作。
二十年來,兩人音信全無,偶然大木在雜誌上看到音子成為小有名氣的京都氣質畫家,他興起了想跟音子一起聽京都除夕鐘聲的念頭,他以為會和音子單獨見面,結果來迎接他的是音子的弟子、也是戀人的年輕美女圭子……
時間沒有沖淡愛戀,音子對大木的愛未曾消失,圭子因嫉妒而想幫音子復仇,縱使音子阻止她,圭子仍勾引大木的兒子太一郎,甚至與大木年雄一起投宿江之島的飯店……
外遇、同性愛、復仇……川端康成完美調和多重主題,一部描寫愛情糾葛和愛僧交織的作品,也是最能展現川端康成的中心思想、寫作技巧與窺視其內心陰暗面的小說。
日本讀者書評
‧比起川端康成的其他作品,我認為這部才是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精隨之作。
‧沒有幾個作家能超越川端康成將性愛描寫得如此絕美,而他描寫風景的優美一貫地細緻又高雅。
‧此作品彷彿是用深沉的哀傷與憎恨替美麗的京都重新塗上色彩,讓我想讀更多川端康成的作品。
‧我認為寫出這種小說的川端康成是個變態的天才。
‧此部是川端康成將病態的殘忍發出到淋漓盡致的作品。
‧充滿背德的哀傷,獨特的世界觀綻放出獨特的光芒,用京都的美麗風景沖淡主角們交錯複雜的關係,是川端康成藝術性的展現。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美麗與哀愁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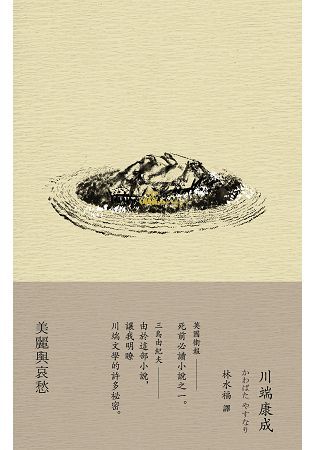 |
美麗與哀愁(二版) 作者:川端康成 / 譯者:林水福 出版社: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5-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211 |
日本文學 |
$ 253 |
日本古典 |
$ 253 |
日本古典 |
$ 253 |
日本文學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2 |
中文書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美麗與哀愁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川端康成
1899年6月11日生於大阪,幼時父母相繼過逝,靠祖父川端三八郎扶養成人。川端小時候因祖父、父親皆為漢醫,在耳濡目染之下,川端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算是相當深遠,他喜好自然,嚮往「禪」境。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化背景的痕跡。川端大學畢業之後,擔任《文藝春秋》編輯委員,1926年連載他的成名著作《伊豆的舞孃》。1949發表《千羽鶴》,此文使他獲得「藝術院獎」。1934年開始陸續發表《南方之火》、《淺草祭》、《雪國》等作品,1956年,他的作品《雪國》被譯為英文,在美國發行,《千羽鶴》被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1968年川端康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川端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人,在亞洲是第二人。前印度詩人泰戈爾為亞洲第一人,好在泰戈爾能用英文寫作,易為西方評審接受,川端康成則只用日文寫作,能夠獲此殊榮,意義確實不凡。
譯者簡介
林水福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台北文化中心首任主任、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副教授、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長、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台灣文學協會理事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副校長、外語學院院長等職。現任南臺科技大學教授、台灣石川啄木學會會長、台灣芥川龍之介學會會長。
著有《讚岐典侍日記之研究》(日文)、《他山之石》、《日本現代文學掃描》、《日本文學導遊》﹙聯合文學﹚、《源氏物語的女性》﹙三民書局﹚《中外文學交流》(合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源氏物語是什麼》(合著),譯有遠藤周作《母親》、《我拋棄了的女人》、《海與毒藥》、《醜聞》、《武士》、《沉默》、《深河》、《深河創作日記》、《對我而言神是什麼》、《遠藤周作怪其小說集》(以上立緒出版);新渡戶稻造《武士道》、谷崎潤一郎《細雪》﹙上下﹚、《痴人之愛》、《夢浮橋》、《少將滋幹之母》、《瘋癲老人日記》(以上聯合文學出版),《萬字》、《鑰匙》(木馬文化)。井上靖《蒼狼》。大江健三郎《飼育》﹙合譯、聯文﹚。與是永駿教授、三木直大教授編多本詩集;評論、散文、專欄散見各大報刊、雜誌。
研究範疇以日本文學與日本文學翻譯為主,並將觸角延伸到台灣文學研究及散文創作。
川端康成
1899年6月11日生於大阪,幼時父母相繼過逝,靠祖父川端三八郎扶養成人。川端小時候因祖父、父親皆為漢醫,在耳濡目染之下,川端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算是相當深遠,他喜好自然,嚮往「禪」境。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化背景的痕跡。川端大學畢業之後,擔任《文藝春秋》編輯委員,1926年連載他的成名著作《伊豆的舞孃》。1949發表《千羽鶴》,此文使他獲得「藝術院獎」。1934年開始陸續發表《南方之火》、《淺草祭》、《雪國》等作品,1956年,他的作品《雪國》被譯為英文,在美國發行,《千羽鶴》被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1968年川端康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川端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人,在亞洲是第二人。前印度詩人泰戈爾為亞洲第一人,好在泰戈爾能用英文寫作,易為西方評審接受,川端康成則只用日文寫作,能夠獲此殊榮,意義確實不凡。
譯者簡介
林水福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台北文化中心首任主任、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副教授、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長、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台灣文學協會理事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副校長、外語學院院長等職。現任南臺科技大學教授、台灣石川啄木學會會長、台灣芥川龍之介學會會長。
著有《讚岐典侍日記之研究》(日文)、《他山之石》、《日本現代文學掃描》、《日本文學導遊》﹙聯合文學﹚、《源氏物語的女性》﹙三民書局﹚《中外文學交流》(合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源氏物語是什麼》(合著),譯有遠藤周作《母親》、《我拋棄了的女人》、《海與毒藥》、《醜聞》、《武士》、《沉默》、《深河》、《深河創作日記》、《對我而言神是什麼》、《遠藤周作怪其小說集》(以上立緒出版);新渡戶稻造《武士道》、谷崎潤一郎《細雪》﹙上下﹚、《痴人之愛》、《夢浮橋》、《少將滋幹之母》、《瘋癲老人日記》(以上聯合文學出版),《萬字》、《鑰匙》(木馬文化)。井上靖《蒼狼》。大江健三郎《飼育》﹙合譯、聯文﹚。與是永駿教授、三木直大教授編多本詩集;評論、散文、專欄散見各大報刊、雜誌。
研究範疇以日本文學與日本文學翻譯為主,並將觸角延伸到台灣文學研究及散文創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