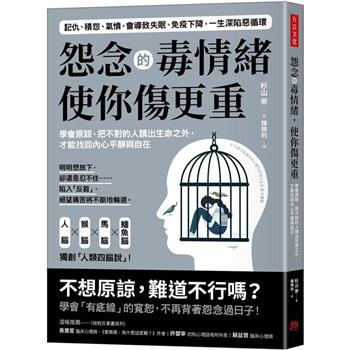★ 特別收錄菲立普.克婁代2017來台專訪
住在蘇拉威西島上的托拉雅人,
生活與死亡同奏。
他們花數星期、數月
甚至數年的時間準備葬禮。
蘇拉威西島(Sulawesi)的西南方住著托拉雅族(Toraja),以盛大的樹葬習俗聞名於世。托拉雅人認為葬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交場合,因此充滿繁複的儀式;當地人相信死亡即是重生——
「靠近林中托拉雅人村落的地方,有棵十分特別的大樹。醒目且雄偉,就在房舍幾百公尺的下方。那是幾個月大早夭嬰兒的墳場。樹幹上,滿是穴洞,放著包裹屍布的幼弱屍身。穴洞外覆以樹葉纖維,隨時間流逝,穴洞會慢慢癒合、將嬰兒的身軀包覆其中,就在新長出來的樹皮下,隨著大樹生長,慢慢接近天空。」
——當「我」從印尼的蘇拉威西島參觀完當地盛大的樹葬、回到巴黎後,「我」的製作人歐傑在電話答錄機裡留言,告訴「我」他得了癌症。
年過半百的電影導演,一夕間發現他的製片人,也是他唯一、最好的朋友,罹患了癌症,即將不久於人世;而處在前一部片宣傳完畢、下一部片尚未開拍之間的空檔,他也擺盪在兩個女人之間——儘管離婚卻固定會見面的前妻,以及年紀幾乎小他一半的年輕女友愛蓮娜。
當時他去找愛蓮娜諮商,想解開心裡的疑問:為什麼好端端的一個人會突然得癌症?為什麼看似健康的身體會突然背棄我們的照顧、保養與信任,突然間朝衰敗死亡奔去?
如果要像托拉雅人那般歡送亡者,我們才能從痛失摯愛中走出來,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對死亡避而不談,直到重擊迎面而來,一輩子只能痛不欲生?
透過過去的回憶與當下的事件交織,主角一面仍在好友的墓園裡向他傾訴生活瑣事,同時在書頁上寫下對好友的記憶以作道別……每一部他(們)看過的老電影、合作過的老演員、聽過的老歌,每一本朋友告訴他「我想你會喜歡」的好書,他們分享的每一則祕密或每一段人生,都像是托拉雅人村落裡的那棵大樹,它們包裹住亡者,但不腐敗、不掩埋,隨著時間過去,樹愈長愈高——你只需抬起頭、看向天空,就會發現屬於你們的過往在生命中一直閃耀。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托拉雅之樹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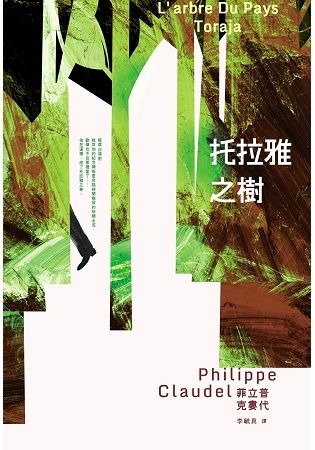 |
托拉雅之樹 作者:菲立普・克婁代 / 譯者:李毓真 出版社: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6-1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25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法國文學 |
$ 205 |
現代翻譯文學 |
$ 205 |
文學作品 |
$ 221 |
小說/文學 |
$ 229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托拉雅之樹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
1962年生於法國洛林區Dombasle-sur-Meurthe,身兼大學講師、作家和劇作家,為法國備受矚目的中生代作家,已出版過14本小說。曾以《莫斯忘記了》獲法國廣播金獎(Prix Radio-France-la Feuille d’or)、《千百悔恨中的一些》獲馬塞巴紐爾獎(Prix Marcel Pagnol)、《我放棄》獲法國電視獎。2003年以短篇小說集《小機械》獲龔固爾短篇小說獎,同年另以《灰色的靈魂》一書獲荷諾多文學獎,並登上法國暢銷排行榜。
克婁代擅長以平實卻富詩意與韻律感的文字,描畫生命複雜的情境。繼《灰色的靈魂》之後,2005年再以《林先生的小孫女》登上排行榜長達半年。2007年底推出全新力作《波戴克報告》,獲得高中生龔固爾文學獎,並入圍龔固爾文學獎決選。
2008年克婁代首度跨足電影領域,自編自導電影《我一直深愛著你》,榮獲英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法國凱薩獎最佳影片、入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於2008年台北金馬影展受邀來台放映,深受觀眾好評。
譯者簡介
李毓真
自由譯者,法國勃根第大學文學、語言及文化博士班肄業。曾於法國從事藝術經紀與口譯工作;喜愛時尚、文學、戲劇和傳統戲曲。譯有《吃到飽飲食瘦身法》、《HOME:搶救家園計畫》、《大鯨魚瑪莉蓮》、《路易威登:傳奇旅行箱100》、《魔法歐克莎》、《孩子的第一本海洋小百科》等。聯絡方式:ychen.lee@gmail.com
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
1962年生於法國洛林區Dombasle-sur-Meurthe,身兼大學講師、作家和劇作家,為法國備受矚目的中生代作家,已出版過14本小說。曾以《莫斯忘記了》獲法國廣播金獎(Prix Radio-France-la Feuille d’or)、《千百悔恨中的一些》獲馬塞巴紐爾獎(Prix Marcel Pagnol)、《我放棄》獲法國電視獎。2003年以短篇小說集《小機械》獲龔固爾短篇小說獎,同年另以《灰色的靈魂》一書獲荷諾多文學獎,並登上法國暢銷排行榜。
克婁代擅長以平實卻富詩意與韻律感的文字,描畫生命複雜的情境。繼《灰色的靈魂》之後,2005年再以《林先生的小孫女》登上排行榜長達半年。2007年底推出全新力作《波戴克報告》,獲得高中生龔固爾文學獎,並入圍龔固爾文學獎決選。
2008年克婁代首度跨足電影領域,自編自導電影《我一直深愛著你》,榮獲英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法國凱薩獎最佳影片、入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於2008年台北金馬影展受邀來台放映,深受觀眾好評。
譯者簡介
李毓真
自由譯者,法國勃根第大學文學、語言及文化博士班肄業。曾於法國從事藝術經紀與口譯工作;喜愛時尚、文學、戲劇和傳統戲曲。譯有《吃到飽飲食瘦身法》、《HOME:搶救家園計畫》、《大鯨魚瑪莉蓮》、《路易威登:傳奇旅行箱100》、《魔法歐克莎》、《孩子的第一本海洋小百科》等。聯絡方式:ychen.le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