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為的大人戀愛,其實都來自你愛過的他。
一部由音樂和奇異旅程交織而成的異境小說
———愈是鍾愛的回憶,它就愈鮮明,也愈奇妙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找他。
想起他,和去追尋他的下落,是兩回事。
雪塊開始從路樹上涮涮地發出疑似山崩聲的同時,
我輕輕把他的身體,從地板移到了柔軟的沙發上。
我看著晨光斜照著他舒服的模樣,覺得真的要離開了,
離開其實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的這個典雅古城。
然後,跟他回去那個一直扣在心頭的老老的小鎮,
並且把只有我與校長才知道的祕密任務完成。
我想,如果是他的話,我們要如何對話?
他會說什麼?
還是,該若無其事地問候:
「最近過得好嗎?」
遙遠的小鎮、廢棄旅館、移動列車、故鄉,還有永恆的音樂———
你以為早遺失的過去,卻在某日成了乍響的旋律。
橫跨台北、沖繩、杭州……作家筆下五段奇幻又溫柔的重逢。
宛如一場幸福的公路電影,在晨光般的明亮鄉愁下,
透著少年少女記憶中霧一般的風景。
至高的幸福即是,對愛的堅信。
作家的文字有著海浪般時而歡愉、時而低迴的節奏。
陪伴世界再度交融的人們,身體力行實踐著從未忘懷的愛。
本書特色
1 這本書似乎擁有魔法,你以為再也見不到的人,聽說都能在此相遇。
2 原以為的大人戀愛,卻讓人想起側背著書包的少年少女。
3 特別收錄:扉頁以美術紙全彩精美印刷作家親筆手繪圖。
各界推薦
王聰威 小說家
伊格言 小說家
吳妮民 醫師、作家
高翊峰 小說家 ————溫柔推薦
「自在、慵懶,卻節奏精巧、充滿奇想的小說,
一如五首老練的爵士樂曲。」——吳妮民
「你可能需要懂得夜半獨飲威士忌(駒之岳)的挫傷,才會懂得這本小說的美好。不知道幸或不幸,只有陳輝龍能寫到這種地步。」——王聰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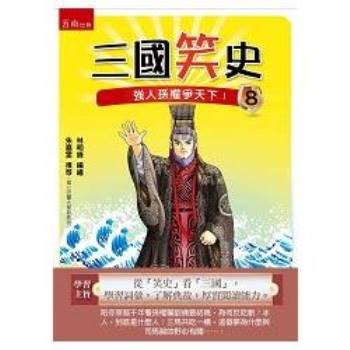










零星在雜誌上看到刊出的幾篇,就想什麼時候出版,畢竟這是老書迷的一個大期待,因為覺得已經不再書寫的小說家竟又在雜誌刊出新作品。 幾年前看到"ˊ69號線的離開"在聯合文學分兩次連載時,就很激動,讀了幾次才罷休。現在買了這本,真的只能說,像五篇連在一塊的不同故事的長篇。尤其是類似主角人物的設定。 一下子就看完後,再讀又有新的畫面,很耐讀。並且,節奏性跟以前比起來,好像比較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