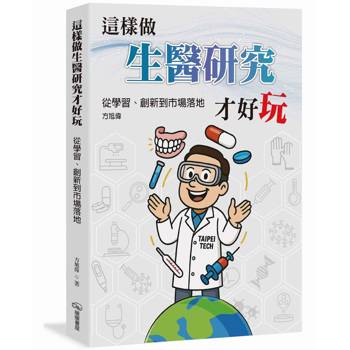圖書名稱:夢外之悲
究竟一個人的死亡,是否能藉由書寫,來進行告別與悼念?
「這是我們祖父母、父母都會經歷的潰敗,也許漢德克和我們都難免。」──廖偉棠專文導讀。
「預示了厭世代之必然,無法界定那究竟是焦慮恐懼還是悲傷」──郭強生
1971年,書中「我」的母親服安眠藥自殺了。儘管當天傍晚,她仍和往常一樣,到隔壁的女兒家吃晚飯。
死前,她以快捷寄出了多封掛號信,並附上了遺書,其中一封給「我」的信上是這樣寫:「但繼續活著是不可能的。」
書中「我」的母親即是作者漢德克的母親。身為一個經歷過納粹時期、戰爭,以及戰後經濟蕭條年代的女人,她總是設法從困境中找到平衡,只不過這一次,她自己就是困境。
葬禮上,漢德克強烈地渴望書寫他母親。幾個月後,這部具自傳色彩的半虛構小說誕生了。
「有時我依然會在夜裡猛然驚醒,彷彿我的體內有什麼把我輕輕一推,從夢裡推出來,我體驗到自己如何因恐懼而屏住呼吸,身體則一秒一秒地腐爛。黑暗中的空氣凝止了,我感到萬物失去重心、四處飄散。它們無聲地在我四周進行無重力的飄移,彷彿隨時就要墜落,從任何一個方向使我窒息……」
作者簡介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
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出生於奧地利,著名小說家、劇作家。1961年曾於格拉茨大學攻讀法律,1965年退學。24歲即發表著名劇本《冒犯觀眾》,引起廣大迴響。他是當代德語文學重量級的作家之一,曾於1973年獲畢希納文學獎,2009年獲卡夫卡文學獎,2014年獲國際易卜生獎,被譽為「活著的經典」。作品風格以實驗性的語言著稱。
作品產量眾多,小說有《夢外之悲》、《守門員的焦慮》、《左撇子女人》、《在漆黑的夜晚,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及《水果賊》(暫譯)等,其中多部曾改編成電影,如《守門員的焦慮》為與文‧溫德斯合作改編;《左撇子女人》則由漢德克本人執導,並獲坎城影展最佳影片提名。
譯者簡介
彤雅立
著有詩集《邊地微光》、《月照無眠》、《夢遊地》。德語譯作包括《馬克思:愛情與資本論》、《分裂的天空》、《我戴著黃星星》、《卡夫卡中短篇全集》等。柏林自由大學電影學博士,現任教於輔仁大學德語系。2015年獲邀參與柏林文學學會舉辦之中德翻譯工作坊,2017 年與 2019 年獲羅伯特‧博世基金會與德國翻譯基金之翻譯駐村獎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