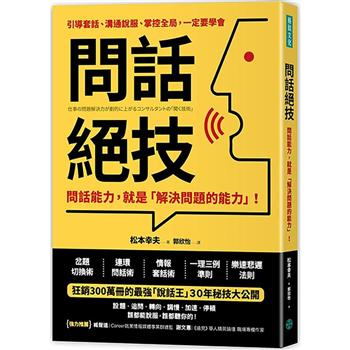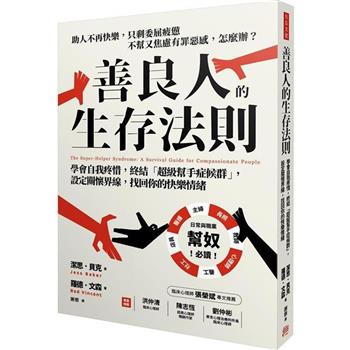西蒙.波娃被埋藏近50年的作品
「如果你活夠久,就會發現每個勝利都將變成失敗。」──西蒙.波娃
西蒙.波娃,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家及女權主義者,其哲學論述與文學創作皆被視為現代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這位不平凡時代中的傑出女性,不僅是女性主義的雄辯者及先驅,也是法國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政治活動與社會理論方面皆有活躍表現。
波娃與沙特於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間數度造訪蘇聯,《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便是波娃以這段經歷為基礎進行的創作,可謂揉合其畢生關注議題的代表性作品,透過男女主角的見聞,將個人歷史和集體歷史緊密扣連在一起:一對暮年夫妻因為一趟莫斯科之旅,招致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理想幻滅,並觸發夫妻失和,作者透過兩性觀點的交互辯證,試圖為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尋找和解的契機,同時也見證了一九六○年代蘇聯社會與文化界的真實樣貌及批判性。
《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寫於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間,為中篇小說創作,原預定收錄於《破碎的女人》(La Femme rompue)小說選集,最後卻捨棄,以致本作品就此塵封三十年,直到一九九二年才首次公開,刊登於《小說20-50》雜誌(Roman 20-50)。本書是唯一法文直譯的中文全譯本,於華文世界首度出版,並收錄數幀相關資料照片,是喜愛波娃的讀者不可多得的重要參考,彌足珍貴。
作者簡介: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出生於巴黎的中產階級家庭,後進入天主教學校就讀,十四歲時突然失去信仰,認為人不免一死,而神是不存在的;十五歲時立志寫作;二十一歲畢業於索邦大學哲學系後取得哲學教師資格,同時在這一年認識了終身伴侶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在愛情、哲學、文學、政治、社會運動等各個篇章中奮不顧身,寫下她一生的絢爛傳奇。
波娃著作等身,卷繁浩帙,類型括及小說、評論、傳記、散文,著有小說《女客》(L'Invitée)、《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人皆有一死》(Les Hommes sont Mortels)、《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自傳《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Tout compte fait);哲學散文《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隨筆《特權》(Privilèges)、《長征》(La Longue Marche)、《老年》(La Vieillesse)、等
譯者簡介:
張穎綺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法國巴黎第二大學法蘭西新聞傳播學院碩士。譯有《女巫》、《在巴黎街上遇見雨果》、《狗:狗與人之間的社會學》(以上為立緒出版)、《謝利》、《觀鳥大年》等書。
章節試閱
她從書頁中抬起目光。這些關於缺乏溝通的陳腔爛調多煩人!如果一個人想溝通,他或多或少辦得到。好吧,當然不是和所有人,但起碼和兩三個人溝通不成問題。隔鄰的安德烈正在閱讀一本偵探小說。她把一些心情、懊悔、芝麻蒜皮的煩惱保留給自己,對他絕口不提,他無疑也有自己的小祕密,不過,大致來說,他們很了解彼此。她望向舷窗外頭:綿延無盡的黝暗森林和淺色草原。他們一同出遊了多少回,多少回在火車、飛機、船上捧書閱讀、比肩而坐?他們未來還會有許多次機會,這樣沉默地並肩而坐,穿行過海洋、大地和穹蒼。這一個瞬間帶有回憶的甜美滋味、承諾的光明燦爛。他們現在是三十歲還是六十歲?安德烈的頭髮白得相當早:突顯他古銅煥發膚色的這頭雪白華髮曾經看來高雅入時。這頭白髮仍然高雅入時。他的皮膚已如老舊皮革一般又乾又皺,但嘴脣和眼裡的笑意始終讓他的臉龐散發光采。雖然相簿裡的照片忠實呈現昔日樣貌,現在的他倒較年輕時更富魅力。妮可看不出他的真實年齡,或許因為他似乎沒把年齡當回事。他過去如此熱愛慢跑、游泳、登山和照鏡子,他毫不在意自己的六十四歲年紀。他們已活了很長的一段人生,有過歡笑、淚水、怒氣、擁抱、告白、沉默、衝動,而有時候,時光彷彿不曾流逝。未來依然往前延展到無窮遠處。
「謝謝。」
妮可從籃子裡拿起一顆糖果,女空服員的肥胖身軀和嚴酷目光令她悚然一驚,一如三年前,那些餐館女服務員和旅館房務員也曾讓她心生畏懼。你敏銳地意識到她們有權在身,只能接受她們強勢的指揮,在她們面前,你會不由自主覺得自己有錯,或者至少是懷疑自己犯了錯。
「飛機要降落了。」她說道。
看著土地越來越接近,她有點不安。未來無限遼闊,但隨時可能在下一刻化為碎片。她熟知這種驟然的情緒波動,恬然安穩的心在轉眼間被恐懼所支配: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安德烈被診斷出肺癌——一天抽兩包菸太多了,過多了;或者是,飛機就要墜毀。這倒是結束生命的絕佳方式:兩個人一起,毫不拖泥帶水,毫不複雜;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太早了。感覺到機輪輪胎撞擊地面的震動,她心想:「又一次平安降落。」乘客起身穿上大衣,取下手提行李。他們在原地等候,等了好一陣子。
「妳可聞到樺樹的氣味?」安德烈說。
天氣非常涼,幾乎是寒冷:根據空服員的廣播,氣溫攝氏十六度。
飛行時間不過是三個半小時,巴黎離這裡如此近,但巴黎今早迎來入夏的第一波熱浪,空氣裡聞得到馬路瀝青味、雷雨欲來的氣味,那樣的巴黎又顯得何等遙遠:她離菲利普多麼近,又多麼遙遠……他們搭上接駁車穿越機場——和他們一九六三年前來的時候相比,占地面積已遼闊了許多——抵達一幢蘑菇形狀的玻璃帷幕建築,他們在那裡通過入境查驗。瑪夏已在出口處等候。看到她,妮可再次驚詫於克萊爾及安德烈極為迥異的五官特色在這張臉上多麼和諧地相融。瑪夏的身材纖瘦,舉止優雅,只有那頭「過度鬈曲」的髮型像典型的莫斯科女人。
「飛航順利嗎?您好嗎?你好嗎?」
她對父親說你,對妮可用敬語。再正常不過,卻也有些古怪。
「我來幫您拿行李。」
這也是正常不過的事。然而,一個男人替妳拿行李,是因為妳是女人;一個女人替妳拿行李,是因為她年紀比妳輕,妳會覺得自己老了。
「把行李條給我,您去那兒坐著。」瑪夏口氣透著威嚴。妮可聽話照辦。她老了。跟安德烈在一起時,她經常會忘記這個事實,每每在自尊心被輕微刺痛時才又想起。見到瑪夏時,她心裡想:「美麗的年輕女人。」她記起自己三十歲的時候,聽見繼父這樣形容一位四十來歲的女人,當時她不由失笑。現在,她也來到這樣的年紀了,大多數人在她眼裡都是年輕人。她老了。她難以坦然接受這個事實(因之而生的驚愕與悲傷,正是她絕口不向安德烈吐露的寥寥數件事之一)。她思忖:「年紀大還是有些有利之處。」處於退休狀態,聽起來有點像一個人已經報廢。但想出門度假的時候隨時可以成行,無異是一大樂事;更確切地說,她隨時都在度假。她以前的同事正在悶熱的教室裡汗流浹背,開始做起出門度假的美夢,而她已經動身離開。她用目光搜尋安德烈的身影,他站在瑪夏身旁,處身於嘈雜的人群裡。在巴黎的時候,太多人有求於他,而他來者不拒。西班牙政治犯,被拘留的葡萄牙人,受迫害的以色列人,剛果、安哥拉、喀麥隆反抗軍,委內瑞拉、祕魯、哥倫比亞游擊隊員。還有她想不起的其他形形色色人物。他總是樂意竭盡所能助他們一臂之力。參與會議、起草宣言、召開集會、散發傳單、出任代表——他答應各種各樣的任務。他隸屬於許多的團體、組織。到了這裡,不再會有央求他幫忙的人。瑪夏是他們唯一認識的人。除了一同觀光遊覽,他們沒有其他事要做:她喜歡跟他一起探索未知、一起發現事物,這樣一來,通常在日常例行作息的幸福裡停滯的時間,得以再次流動,帶來源源不絕的新鮮經驗。她站起身。她多希望已經身處街頭,站在克里姆林宮城牆下。她已經忘了在這個國家的等待時間可能會多麼漫長。
「行李到了嗎?」
「它們終究會到。」安德烈說。
三個半小時,他思忖。莫斯科如此近,又何等遙遠!才不過三個半小時飛行時間的距離,他竟然罕得和瑪夏見上一面?(但是有這麼多障礙存在,尤其是旅費問題)。
「三年的時間很長。我肯定看起來蒼老了。」他說。
「才不。你沒有變。」
「妳比以前更美了。」
他一臉喜悅地看著她。你本以為生命裡再也不會發生任何事,你已經將就接受(那不是容易的事,雖然他沒有顯現出來),接著,一份全新的情感降臨,照亮你的生活。他過去對那個膽怯的小女孩幾乎毫無興趣——她當時叫瑪麗亞,克萊爾會從僑居的日本、巴西、莫斯科帶她前來探望他,一起相處幾個小時。戰後,帶著丈夫來巴黎見他的年輕女子,對他而言仍舊是陌生人。但在瑪夏一九六○年第二度到訪巴黎時,他和她之間起了變化。他並不明白她何以變得如此喜歡他;但他深受感動。妮可對他的愛情依然鮮活、熱切、令他喜悅;但他們太習慣彼此,以致安德烈絕對無法讓她開懷而笑,就像此刻瑪夏嚴肅臉龐上綻開的燦爛笑靨。
「行李到了嗎?」妮可問道。
「它們終究會到。」安德烈說。
何必焦急呢?他們在這裡有大把時間任憑揮霍。在巴黎,安德烈為時間飛快流逝所苦,在各個約會之間分身乏術,特別是從他退休以後:因為他過於高估自己所擁有的空閒時間。由於好奇心,由於不曾慎重考慮,他任由自己承接下許多責任義務,就此無法抽身。現在,他有整整一個月時間遠離那些職責,他可以過著熱愛的自由自在生活,他太愛這樣的生活,他的多數煩惱正是從中而生。
「我們的行李到了。」他說。
他們把行李搬上瑪夏的車,她坐進駕駛座。她開得很慢,就像這裡所有人一樣。沿路上,新鮮的草木氣息撲鼻而來,一段段原木順著莫斯科河漂流,安德烈感覺內心一陣激動,這是讓生活免於索然無味的必要成分。冒險即將展開,他既興奮又恐懼,這是一趟去發掘、去探索的冒險。他從來不關心自己是否功成名就,是否成為響叮噹的大人物。(要是他的母親不曾堅決監督他繼續學業,他會滿足於和父母一樣的職位:在陽光普照的普羅旺斯當小學教師)。他感覺到,自身生命與存在的真理似乎不屬於他:它神祕地散布在全世界各處。為了解這個真相,他得探查過去和世界各個角落;這是他何以熱愛歷史及旅行的理由。然而,儘管他能夠悠然從書本裡讀到某個面向的過往歷史,但只要親身接近一個陌生的國度——超越他所知任何事的豐富面——總是讓他暈眩。而這個國家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和他息息相關。他生長在崇拜列寧的家庭;他八十三歲的母親仍然積極投入共產黨活動。他沒有入黨,但在希望與絕望交織的動盪時代裡,他始終認為蘇聯握有未來之鑰,握有這個時代和他個人命運的鑰匙。然而,即使在史達林主義當道的黑暗歲月期間,他也從來不曾感覺對這個國度如此陌生。這次的停留將會讓他了解這個國家嗎?他們在一九六三年以觀光客之姿前來——到克里米亞、索契——東看西看,卻止於表面印象。這一次,他會提出問題,他會讓瑪夏讀報紙內容,他會融入當地人群。車子轉進高爾基街。街上有人群、有商店。他能在這裡感覺自在嗎?一想到自己萬一辦不到,他恐慌起來。他心想:「早知道應該更認真地學俄語!」又是一件他決心要做卻沒有實現的事:他只讀到愛絲米那(Assimil)俄語課本的第六課。難怪妮可要稱他為懶老頭。他對閱讀、聊天、散步總是興致高昂,但是受不了背單字或做筆記這類的苦差事。既然如此,他不該太在意這個世界。他太嚴肅,也太輕佻。他愉快地想:「這是我矛盾的地方。」(一位義大利籍同事對他的評語,那是一名欺壓妻子的堅貞馬克思主義信徒,所以他欣然當作恭維。)事實上,他覺得自己好得很。
她從書頁中抬起目光。這些關於缺乏溝通的陳腔爛調多煩人!如果一個人想溝通,他或多或少辦得到。好吧,當然不是和所有人,但起碼和兩三個人溝通不成問題。隔鄰的安德烈正在閱讀一本偵探小說。她把一些心情、懊悔、芝麻蒜皮的煩惱保留給自己,對他絕口不提,他無疑也有自己的小祕密,不過,大致來說,他們很了解彼此。她望向舷窗外頭:綿延無盡的黝暗森林和淺色草原。他們一同出遊了多少回,多少回在火車、飛機、船上捧書閱讀、比肩而坐?他們未來還會有許多次機會,這樣沉默地並肩而坐,穿行過海洋、大地和穹蒼。這一個瞬間帶有回憶的甜美...
作者序
前言
寫於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的中篇小說《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Malentendu a Moscou)原本預定被收錄於《破碎的女人》(La Femme rompue)小說選集(一九六八年出版)。儘管它的文字品質顯然無虞,波娃最後卻捨棄,改以另一部小說《懂事年齡》(L'Age de discretion)取代。《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在一九九二年才首次公開,刊登於《小說20─50》雜誌(Roman 20-50)。
《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講述一對老年退休教師伉儷妮可和安德烈於莫斯科旅行期間所經歷的婚姻與自我認同危機(在結尾順利克服),並有安德烈與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兒瑪夏在當地和他們聚首。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採用的敘事模式顯然極其適於本部小說的主題。透過妮可及安德烈兩人視角的不斷交替(總計細分為二十四則分量平均的段落),讀者處於有利位置,從而短暫地身歷其境,感受夫妻彼此的誤解、未曾言明的失望、越發深厚的積怨。藉由此一敘事技巧,波娃更得以平行呈現男、女視角(安德烈更關注政治,妮可側重感性面)的分歧及相似。波娃在更早期的作品裡即已運用過雙重視角手法(《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但在此部小說裡所展現的強度與互補性更勝以往。
誠如其標題所表明的,此部小說將個人歷史和集體歷史緊密扣連在一起:一趟旅行帶來的政治理想幻滅,以及所觸發的夫妻失和。它從而提供了一九六○年代蘇聯真實樣貌的動人(及批判性)見證。波娃與沙特於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間曾數度應蘇聯作家聯合會邀請前往該國訪問,她由屢次的停留經驗得到寫作靈感(沙特更得以和俄羅斯女友利娜.佐尼娜(Lena Zonina)重聚,小說角色瑪夏的某些特點即以她為藍本)。因此,讀者得以透過兩位主角對異地奇觀的真實體驗和感受來判斷該國的發展變化,並且目睹當地荒謬官僚制度帶來的眾多麻煩事。蘇聯的文化界狀況、彼時與中國交惡期間的外交政策,也引發瑪夏與父親安德烈之間的辯論,後者沒能在重訪的莫斯科親睹純粹、完美的社會主義制度,終而大失所望。波娃於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在一九七一年寫成的《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Tout compte fait),包含對蘇維埃政權更強烈的批判,且以更多的篇幅探討自由的課題。但本部小說對於蘇聯景況的詳實描繪,仍然讓它成為一份深具價值的文獻。
除了夫妻危機以外,波娃也觸及更廣泛的主題。各個女性角色闡明出女性處境的不同層面:妮可雖然渴望性別解放,年輕時曾挺身奮戰,卻為家庭生活所消磨,以致壯志未酬。她兒子的未婚妻伊雷娜代表新一代的女性,她們聲稱取得一切,斬獲卻止於表面。瑪夏享有的從容自在及獨立自主則是拜性別平等的蘇聯社會所賜。與他者溝通的問題貫穿整部小說,然而其核心主題是變老的苦澀:身體機能衰退,性慾消退,放棄計畫,喪失希望。對年齡的思索更引向對時光的詰問(最終是對普魯斯特致敬)。角色們的內心騷動往往賦予這些思索特別動人的抒情語
調。「誤解」的加劇使得角色越發沉緬於往昔時光,最終導向對於人類生命意義的探問:「她被焦慮擊倒:比起面對死亡的恐懼,活著的焦慮更令人難以承受。」這些疑問及主題無可避免地緊密纏繞。而整幅圖畫的核心是身為兩人導遊和翻譯的瑪夏,她觸發了他們的婚姻危機和覺醒。
在用來取代《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的另一篇小說《懂事年齡》(L'Age de discretion)裡,西蒙.波娃重拾老年夫婦失和的主題,並在合於上下文意的適切位置,原封不動照搬前者的許多段落。但她排除了蘇聯的故事背景,且只採用妻子單視角的敘事觀點:這些書寫上的選擇呈現,使得後者更順理成章被收錄於《破碎的女人》一書。然而,《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本身不言自明的豐富性,催化出此次以單行本問世。
艾蓮恩.勒坎蒙—塔伯恩(Eliane Lecarme-Tabone)
前言
寫於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的中篇小說《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Malentendu a Moscou)原本預定被收錄於《破碎的女人》(La Femme rompue)小說選集(一九六八年出版)。儘管它的文字品質顯然無虞,波娃最後卻捨棄,改以另一部小說《懂事年齡》(L'Age de discretion)取代。《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在一九九二年才首次公開,刊登於《小說20─50》雜誌(Roman 20-50)。
《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講述一對老年退休教師伉儷妮可和安德烈於莫斯科旅行期間所經歷的婚姻與自我認同危機(在結尾順利克服),並有安德烈與第一任妻子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