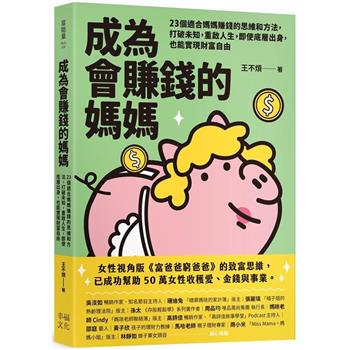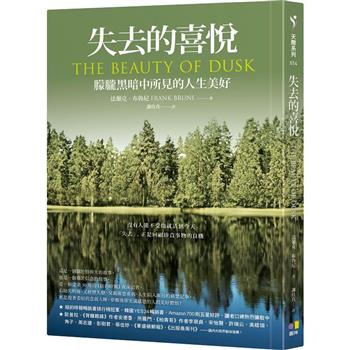導論
導論/莫比爾(Bill Moyers)
喬瑟夫.坎伯死後的幾個星期裡,我不論走到那兒都會想起他。
從時代廣場的地下鐵車站走出來,我不由得感到擁擠人潮散發出令人窒息的壓力。我自己在心底笑了笑,忽然想起坎伯曾在這裡經驗到的個意象:「最新輪迴轉世的伊底帕斯(Oedipus),是接續上演的美女與野獸羅曼史。他正站在四十二街與第五大道的街角,等待著交通號誌的變換。
在休斯頓(John Huston)依喬哀思(James Joyce)原著改編的最後一部電影「死者」(The Dead)的預演會上,我又想起坎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乃是了解《芬尼格.威克》(Finne gans Wake)一書的關鍵。喬哀思認為人類苦難中有所謂的「最大與恆常的苦難」,坎伯把這看成是古典神話學中的基本主題。他說:「造成所有苦難的原因,就是生命必然會死去這個事實。假如生命被肯定,死亡便無法被否定。」
有一次當我們正在討論苦難這個主題,他先後提到喬哀思與伊鳩札留客(Igjugarjuk)。「誰是伊鳩札留客?」我問。幾乎不可能正確發出這個名字的音來。坎伯回答說:「哦!他是加拿大北部一個愛斯基摩部落的巫師。他曾經告訴過歐洲的訪客:『生命遠非人智所及,它由偉大的孤寂中誕生,而只有從苦難中才能觸及。困厄與苦難才能使心眼打開,看到那不為他人所知的一切。』」
我說:「當然,伊鳩札留客。」
喬並不在意我對文化的無知。我們這時已不再步行。他的眼睛突然一亮的對我說:「你能想像一個與喬哀思、伊鳩札留客坐在火堆旁,談天說地的漫漫長夜會是怎樣的光景嗎?哇!我想要在一旁聆聽。」
坎伯正好在甘迺迪總統被暗殺二十四週年紀念日之前逝世。他曾經在我倆第一次會面之前的幾年,以神話的概念討論過這個悲劇。現在當這個令人哀傷的記憶再度到來,我坐著與我成年的孩子們談論到坎伯對這個悲劇的看法。他把肅穆的甘迺迪總統的喪禮描述成:「對一個社會作出最高宗教儀式的示範」,把深植在人類需要中的神話主題激發出來。「這是一個把社會最必要的精神,儀式化了的場合。」坎伯這樣寫下。總統被公然暗殺,「代表了我們這個活生生的有機社會,在精力最充沛的時刻,被奪走了生命。所以需要一個補償性的宗教儀式,以重新建立團結一致的感覺。美國是個大國,但在這四天國葬禮儀中,我們成為一個一致的社會;大家同時以相同的方式,共同參與一個具象徵意義的事件。」他說:「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承平時期而有一種身為整個國家社會一份子的歸屬感。這是藉由大家一致參與一項深具意義的宗教儀式而來的。」
我記得另一件事。是我們的一位同事被他朋友問到有關我們與坎伯合作的事。「為什麼你們需要神話?」她提出熟悉的現代論調,也就是「所有這些希臘的神與事」和人類今天的處境毫無關聯。她不知道,也是大多數人不知道的,那些「事物」的殘餘,就像考古現場的陶瓷器碎片一樣,填滿了我們內在信仰系統的圍牆。然而因為我們是一有機物,所以那些「事物」都以能量的形式存在。儀式則可以引發它。讓我們看看法官在我們社會的地位,坎伯是以神話而非社會學的概念來看待。假如法官只是個社會角色,那麼他可以只穿一套灰西裝而不是象徵權威的黑袍到法庭。因為支撐權威感的法律不僅僅只是一種強制,所以法官的權力必須儀式化、神話化。坎伯說:「所以今日生活的許多部份,從宗教、戰爭到愛與死亡,都必須如此。」
坎伯過世後,我在上班途中的某個清晨,停在附近一家錄影帶店門口,觀賞電視櫥窗中放映喬治.盧卡斯的「星際大戰」劇情片斷。我站在那兒想到我與坎伯在加州喬治.盧卡斯的「天行者山莊」中,共同觀賞此片的情景。盧卡斯與坎伯在該部電影製作後變成好朋友,因為盧卡斯知道該片的製作受到坎伯的影響極深,所以盧卡斯便邀請坎伯觀看「星際大戰」的三部曲。坎伯對古代神話中的主題、意旨,能以強而有力的當代意象展現在大螢幕上,而感到高興。在該次造訪中,由於對劇中人路克的歷盡危難與英雄事蹟感到欣悅,喬在談到盧卡斯如何「把最新而有力的變化放入」古典英雄故事中時,愈發興奮雀躍。
「那是什麼變化?」我問。
「那是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說的,而盧卡斯卻以現代語言來加以表示。也就是傳達科技將無法解救我們的訊息。我們的電腦、工具、機器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仰賴我們的直覺、我們真實的存在。」
「這是不是違反了理性呢?」我問。「我們難道不是已經從理性急急忙忙的撤出了嗎?」
「那不是英雄冒險的重點所在。它並不否定理性。相反的,藉由克服黑暗的感情,英雄象徵了我們對內在非理性破壞作用的控制。在其他幾個場合,坎伯也表示過,他對我們不能「承認人性本具的食色本能」而感到可悲。這裡他所描述的英雄冒險過程,並不是英勇的行為,而是一個自我發現的生活。「當路克發現形成他面對命運的內在性格淵源時,他變得再理性不過。」
諷刺的是,對坎伯而言,英雄冒險過程的終結,並不是誇大英雄這個角色的。他在一場演說中提到:「我們不應該把自己和所經驗的人物或力量劃上等號。」印度渴求解放的瑜珈大師,把自己化在光中而不再回到這個世界。但是意欲服務他人者,是不會如此逃避的。這個旅程的終極目標既非解放也非極樂,而是服務他人的智慧與力量。他說:「名人與英雄的眾多差別之一是,名人只為自己而活,但英雄是要解救社會。」
坎伯肯定人生是一場冒險。在他大學指導教授把他侷限在狹隘的學術課程中,他說:「去它的」。於是他放棄攻讀博士學位,而到森林中讀書。他一生持續不斷的閱讀有關世界的書,包括人類學、生物學、哲學、藝術、歷史與宗教。而且不斷提醒他人,了解世界的一條可靠之路,便在書本當中。在他死後幾天,我收到一封由現職一本重要雜誌編輯,是他以前一位學生所寫的信。在看過我與坎伯在公共電視上的一系列對談後,她寫信與我們分享坎伯是如何「以一陣旋風席捲所有知識的方式」,讓莎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學生「在課堂中毫無喘息的餘地。」她寫道:「雖然我們聽他的課聽得津津有味,但我們也對他每週指定閱讀作業份量之重,感到躊躇不安。最後有位同學站起來面對他(莎拉.勞倫斯學生的風格)說:『你知道,我還選了其他門課,每門課都有指定閱讀。你怎能期盼我在一週內念完所有的閱讀作業呢?』坎伯只是笑笑說:『我很驚訝你試著想在一週內讀完,你還有一輩子可以讀這些書。』」
她下結論說:「而我還未閱讀完他那永無完結的人生與智慧典範。」
我們可以從一項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為坎伯舉辦的紀念會上,看出他的影響力。當他還是個孩子時,被他人帶到博物館內。他為那些圖騰柱石與面具深深的震懾住了。到底是誰創造了它們?他感到好奇。它們代表什麼意義呢?他於是開始盡其所能的閱讀印第安人的神話與傳奇。在他進入這個領域不到十年的時間,他便成為世界研究神話的頂尖學者,同時也是我們當代最令人激奮的老師。據說,「他可以讓民俗學與人類學有如真實存在一般。」現在這個曾經在七十五年前激發他對神話興趣的博物館內,人們為他舉行紀念儀式並獻上崇高的敬意。其中有「歡樂死者」(the Grateful Dead)打擊樂團鼓手哈特(Mickey Hart)的演出,坎伯曾與這個樂團共享過打擊樂的美妙。布萊(Robert Bly)彈奏德西馬琴(dulcimer)並誦讀一首獻給坎伯的詩。以前的學生,他在退休後與舞者妻子珍.厄爾曼(Jean Erdman)搬到夏威夷去後結交的朋友,都前來致詞。紐約著名的出版公司都有代表出席。同時還包括年輕及資深的作家與學者,他們都曾在坎伯的書中找到人生的突破之路。
還有新聞記者。我早在八年前就為他所吸引,我自己設計製作了一系列節目,試圖把我們時代充滿活力的智者心靈帶到電視螢幕上。我們曾在這個博物館錄製了兩個節目,而透過他在螢幕上強有力的現身說法,共有一萬四千名觀眾來函索取對話的腳本。那時我便發誓還要再找他,作一個更有系統而完整探索他思想的節目。他寫作或主編了近二十本書,但是我們接觸到的他卻是為人師表的那一面。他是一個對世界傳說與語言意象有廣博知識的老師。我希望別人也能從這個角度去認識他。想要與大家分享此人智慧之寶的渴望,便促成了我與他公共電視對談節目以及這本書的問世。
大家認為新聞記者享有在公眾中不斷受教育的權利;我們是幸運的一群,可以繼續接受成人教育的課程。近年來坎伯是教我最多的人,而當我告訴他,不論我這個學生將來如何變化,他都得負起影響我的責任。他聽了哈哈大笑,並引用一句古羅馬諺語:「掌管命運的三個女神會引導有志者,隨波逐流的人則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就像偉大教師的教法一樣,他以實證教學。他的態度是不喜歡用言語說服別人,去相信某個事物(唯一的例外是當他向珍求婚時)。他告訴我演說者的錯誤在於,試圖「藉言語讓人產生信仰;他們最好能夠把自己發現的光芒展露給別人。」他對學習與生活的喜悅,正是如此活生生的展露給我們!馬修.阿諾(Matthew Arnold)認為最好的批評是「知道這個世界上已知的最好事物,然後再把這個已知事物轉化,創造出一股契合真理的嶄新思想潮流。」這就是坎伯的貢獻。只要你聽他所言——真正認真的聽,你就一定會發現到,在你的自性中有一股全新生命的湧現,以及自我想像力的提升。
他同意他研究的指導原則,是去發現「世界神話主題中的共通性,以指出人類心靈中,有將自己置身在一個具深刻意義核心的永恆渴求。」
「你是說尋找生命的意義?」我問。
「不,不,不,」他說:「是去尋找那種覺得真正活著的經驗。」
我曾經說過,神話學是一張內在經驗的地圖,它由曾經旅遊過的人所畫。我懷疑他認可這個來自新聞記者的無聊定義。對他而言,神話學是「宇宙之歌」,是「天籟」——即使我們不知曲調為何,我們依然隨之翩然起舞。「不論我們是以一種高高在上嘲諷的心,聽非洲剛果河畔巫醫,對著可笑偶像符咒唱誦的聲音,讀富含高度智慧的老子道德經譯文,咀嚼阿奎那像果核般堅硬的神學議論,還是突然間對愛斯基摩人神仙故事的意義有所了解。」我們所聽的都是天籟的重複樂章。
他猜測這個龐大而不協調的合唱團,大概是由我們原始社會祖先在殺動物為食,及觀察到動物死後似乎進入超自然世界,並講述這些關於動物故事的時候開始。超越可見的存在世界,「在那兒某處」有「動物首領」(animal master)存在,它是控制人類生死的力量。假如它不把動物送下來犧牲供人類獵食,則獵人與他的族裔將挨餓。早期社會學習了解到:「生命的本質是殺生與飲食;那就是神話所要處理的重大奧秘。」狩獵變成一種犧牲的儀式,獵人
反過來對動物的靈魂作出補償的動作,希望能夠誘使牠們再回來犧牲,供人類食用。野獸被看作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使節。坎伯臆測在獵人與獵物間逐漸滋生「一種神奇、美好的和諧」,彷彿他們被鎖在一個死亡、埋葬與再生「神秘的超時間」循環中。洞穴牆壁中的繪畫藝術以及口傳文學,便是我們今天稱作宗教衝動的表現形式。
當這些原始人從狩獵轉變到以栽種為生,他們詮釋生命奧秘的故事也改變了。種子成為無盡循環的神奇象徵。植物死亡,被埋葬,但它的種子會再生。對各大宗教談到永恆真實的顯現(亦即由死而生,或是他所謂的「從犧牲到極樂」)時,大多使用此一象徵的現象,坎伯感到極度有趣。
他說:「耶穌有慧眼」。「他在芥菜子中看到了偉大的真實。」他從約翰福音中引用耶穌的話:「真的真的,我告訴你,除非一粒麥子掉入土裡死去,它仍然是孤獨的;但是假如它死了,它可以長出許多果實來。」下一個引的則是可蘭經:「你認為你可以不經過那些,在你之前死亡人們的試鍊,就可以進入天堂嗎?」他漫遊於廣泛的心靈典籍中,甚至從梵文翻譯印度教經典,而且持續不斷收集最近的故事,以便附加詮釋古老的智慧。他特別喜歡有關一個困惑的女人去問印度聖哲拉馬克里希那(Ramakrishna)的故事。那個女人問說:「啊,大師,我不覺得我愛上帝。」他回問:「那麼你是不是不愛任何事物?」她回答說:「我的小姪女。」於是他對她說:「那是你的愛,也是對上帝的服務,因為你愛那小孩,也是在提供服務。」
坎伯說:「那裡便是宗教的崇高訊息:只要你們在這當中至少為一個人做了事……」
他在各宗教信仰的文獻中發現,人類精神層次的原則大同小異。但他們必須從部落優先的觀念中解放出來,否則世界宗教便會停留在今天中東和北愛蘭的狀態,那是鄙視與侵略的來源。他說,上帝的意象有許多,可以把它們稱作「永恆的面具」,因為它們同時掩蓋也揭露「光榮上帝的面貌」。他想知道上帝為什麼在不同的文化有如此不同的名字,也想知道在這些歧異的傳統裡,許多類似的故事如何被發現和比較。例如創世記、處女生子、輪迴、死亡與復活,二度降臨(second comings)和最後審判日等故事便是。他喜歡印度教經典中的一個見解:「真理只有一個:聖賢以許多不同的名字稱呼它。」他說:「我們所有的名相與意象,對上帝而言,都只是指涉永恆的面具而已。終極真實本身的字義已說明它是超越一切語言與藝術。神話也是上帝的面具,是表示藏在可見世界背後事物的一個隱喻。他說,不論神秘主義的傳統如何不同,他們都在呼喚我們對生命本身的行動有深層次的覺醒。在坎伯的書中,不能原諒的原罪乃是怠慢疏忽、不夠警覺、不夠清醒。
我從未見過比他更會說故事的人。聽他談原始社會,我有如置身在無際蒼穹下的廣大草原上,或是在群樹覆蓋的濃蔭森林中。我開始能了解,如何從風雷裡聽到神的聲音,從每條山中溪澗看到上帝之靈的流動,以及把地球看成是自神話想像聖地開出的果實。於是我不禁要問:既然我們現代人已經把大自然的神秘剝落殆盡,用梭爾.貝婁(Saul Bellow)的話說,已經把信仰完全清掃乾淨,我們的想像力要如何得到滋養呢?難道要靠好萊塢和為電視製作的電影嗎?
坎伯不是悲觀主義者。他相信「有個超越幻象衝突的智慧點,和一個能把生命重新放回原位的真理存在。」找到它「主要是時間的問題。」在人生最後的歲月裡,他試圖要找出科學與心靈間新的綜合。在太空人登陸月球後他寫道:「從地球中心說到太陽中心說之間,世界觀的改變似乎把人類從中心移開,而中心是很重要的。然而從精神層次來說,中心就是觀看的地方。站在高地便看到地平線,站在月亮上便看到整個地球的升起,即使你是從客廳的電視中看到,效果也是一樣。結果是史無前例的擴大了人類的視野。就好像古代神話對他們的時代所作的貢獻一樣,這個新宇宙觀也對我們的時代發生了相同功能。它把我們感覺之門清掃乾淨,「以迎接那一度被認為是可怕、迷惑的宇宙驚奇景象及自己的奧秘。」他認為並不是科學造成非人性化或使我們脫離神性。相反的,科學的新發現「使我們與古人重新結合」。
因為它使我們認識到整個宇宙不過是「我們內在心靈深處本性的放大反照而已;所以我們確實是它的耳朵、它的眼睛、它的思考、它的言語,或者以神學的語言來說,是上帝的耳朵、眼睛、思考與諭旨。」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問他是否仍然相信他曾寫過的信念:「此刻我們正參與個由人類心靈,對外在及我們內心深處奧秘知識,最大的一次跳躍。」
他想了一下然後回答:「從來沒有這樣堅信過。」
當我聽到他死亡的消息,我拿起他給我的《千面英雄》一書翻看了一會兒。我想起因此書第一次發現神話英雄世界的情況。我曾經漫步到孕育我成長的小鎮上,一家小圖書館內,隨便找找架上的書,抽出一本啟發我對宇宙人類驚奇的書:為了人類從神那兒盜火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勇搏巨龍獲得金羊毛的傑森王子;追求聖杯的圓桌武士等等,都記載於其中。但一直到認識坎伯之後,我才了解,在週六戲劇中所見的西方人,是如何自由的借用這些古代故事。而我們在教會主日學校學到的故事,與其他同樣體認到靈魂崇高追求,和以必朽生命追求上帝真實的不同文化間,有互相對照之處。他讓我看到了其間的關聯,了解各個片斷怎樣能彼此連接,並使我對他稱作「有活力的多文化未來」,不僅不再那麼懼怕,甚至歡迎它的到來。
當然,他也被批評為過度以心理學來詮釋神話,以及似乎把神話的當代角色,太過侷限在意識型態功能或治療的功能上。我沒有資格論斷這些評論,還是讓別人來衡量。他似乎從來不為爭議所困擾。他只是不斷教書,啟發別人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
畢竟,是他那種真實的生活給予我啟發。當他說神話是我們最深心靈潛能的線索,能使我們歡樂、明覺、甚至狂喜。他說得好像是自己曾經去過那些地方,而邀請我們前往造訪的人。
他的哪一點吸引了我呢?
智慧,是的;他非常聰明。
博學;他確實如此。「對那些少有人知道的素材,他卻能知道那千萬變化之過去的全貌。」
但還不止於此。
故事是要用講的。他是有成千故事的人。以下是他最喜歡的故事之一。在日本參加一項宗教國際會議時,坎伯聽到另一位從紐約來的美國社會哲學家,對一位日本神道教的神職人員說:「我們目前為止已參觀過許多典禮,也看了你們許多神廟。但我不了解你們的意識型態。我不了解你們的神學。」日本人停頓了一下,彷彿在深思,然後搖了搖頭。「我想我們沒有意識型態。」他說:「我們沒有神學,我們跳舞。」
坎伯也是一樣,在天籟伴奏下起舞。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神話的力量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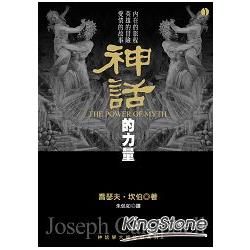 |
神話的力量 作者:喬瑟夫.坎伯 / 譯者:朱侃如 出版社: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1-1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6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283 |
Others |
二手書 |
$ 283 |
Others |
$ 308 |
中文書 |
$ 332 |
小說/文學 |
$ 351 |
宗教類 |
$ 390 |
神話/寓言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神話的力量
本書是當代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與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台記者莫比爾(Bill Moyers),在喬治.盧卡斯的天行者牧場、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三次對話編輯而成。
坎伯的學問遍及人類學、考古學、生物學、文學、哲學、文獻學、(超)心理學、比教宗較學、藝術史及流行文化等領域,由此融匯成其獨特的神話學見解,並因此奠定了他在神話學的歷史地位,成為一代宗師。
坎伯除了在學術及專業著作上享有聲譽外,也活躍於大眾文化及娛樂的領域中。喬治.盧卡斯的經典之作《星際大戰三部曲》,便是受到坎伯的神話概念「英雄的冒險旅程」影響而拍攝完成的。
閱讀本書,你會發現文中字字珠璣,給讀者無限啟發,例如「從腐爛中才有生命出來」、「每個人出生時都是個英雄」。坎伯以生動、平易而富於魅力的筆調,展現了他一生神話學研究的精髓,賦予現代人在平庸、貧血的生活中,另一種思維觀照和超越。
※本書原書名《神話》
作者簡介: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當代神話學大師。一九○四年生於美國紐約市,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去世於夏威夷家中,享年八十三歲。著有《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神話的智慧》(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神話》(The Power of Myth)等書(以上皆由立緒文化出版)
譯者簡介:
朱侃如
中興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天普大學新聞碩士(主要研究媒體所有權及新聞倫理問題),資深翻譯工作者。譯有《神話》、《坎伯生活美學》、《千面英雄》、《女性主義》、《榮格心靈地圖》、《哭喊神話》、《權力與無知》、《焦慮的意義》等書(以上皆由立緒文化出版)。
章節試閱
導論
導論/莫比爾(Bill Moyers)
喬瑟夫.坎伯死後的幾個星期裡,我不論走到那兒都會想起他。
從時代廣場的地下鐵車站走出來,我不由得感到擁擠人潮散發出令人窒息的壓力。我自己在心底笑了笑,忽然想起坎伯曾在這裡經驗到的個意象:「最新輪迴轉世的伊底帕斯(Oedipus),是接續上演的美女與野獸羅曼史。他正站在四十二街與第五大道的街角,等待著交通號誌的變換。
在休斯頓(John Huston)依喬哀思(James Joyce)原著改編的最後一部電影「死者」(The Dead)的預演會上,我又想起坎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乃是了解《芬尼格.威克...
導論/莫比爾(Bill Moyers)
喬瑟夫.坎伯死後的幾個星期裡,我不論走到那兒都會想起他。
從時代廣場的地下鐵車站走出來,我不由得感到擁擠人潮散發出令人窒息的壓力。我自己在心底笑了笑,忽然想起坎伯曾在這裡經驗到的個意象:「最新輪迴轉世的伊底帕斯(Oedipus),是接續上演的美女與野獸羅曼史。他正站在四十二街與第五大道的街角,等待著交通號誌的變換。
在休斯頓(John Huston)依喬哀思(James Joyce)原著改編的最後一部電影「死者」(The Dead)的預演會上,我又想起坎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乃是了解《芬尼格.威克...
»看全部
目錄
序 神話學探索的文化啟蒙意義 ◎傅偉勳
序 我們需要重興喚醒創造神話的活力 ◎李豐楙
喬瑟夫.坎伯簡介 ◎朱侃如
原著編輯說明 ◎Betty Sue Flowers
導論 ◎Bill Moyers
神話與現代世界
內在的旅程
第一個說故事的人
犧牲與喜悅
英雄的冒險
女神的贈禮
愛情與婚姻的故事
永恆的面具
序 我們需要重興喚醒創造神話的活力 ◎李豐楙
喬瑟夫.坎伯簡介 ◎朱侃如
原著編輯說明 ◎Betty Sue Flowers
導論 ◎Bill Moyers
神話與現代世界
內在的旅程
第一個說故事的人
犧牲與喜悅
英雄的冒險
女神的贈禮
愛情與婚姻的故事
永恆的面具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喬瑟夫.坎伯 譯者: 朱侃如
- 出版社: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1-14 ISBN/ISSN:978986360026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24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神話/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