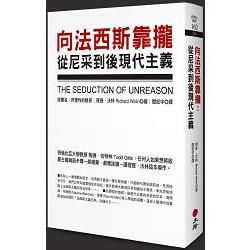序
「希特勒迫使人類接受一項新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好好引導你的思想與行為,不要再讓奧許維茲(Auschwitz)集中營重現人間,不要讓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
──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否定辯證法》(Negative Dialectics)
本書探討的主題令許多人諱莫如深,它重新檢視了一九三○年代知識分子與右派政治複雜斑駁的歷史,以及兩者關係對於當前政治的意涵。
有些人一廂情願地認定,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反智現象,只能吸引罪犯與惡徒。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已然知道實情並非如此。當年歐洲大陸有許多知識分子菁英,爭先恐後地跳上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列車。畢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之後,民主政治的信譽已經沉淪到史無前例的谷底。我們不妨列舉幾位法西斯主義在文學與哲學領域的支持者,但只是冰山一角:容格爾(Ernst Jünger)、班恩(Gottfried Benn)、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施米特(Carl Schmitt)、布拉席亞緒(Robert Brasillach)、拉羅舍爾(Pierre Drieu La Rochelle)、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德曼(Paul de Man)、龐德(Ezra Pond)、真蒂萊(Giovanni Gentile)、馬利內提(Filippo Marinetti)、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葉慈(W. B. Yeats)與劉易斯(Wyndham Lewis)。再者,馬克思主義學派著眼於法西斯主義經濟根源的詮釋,已經一蹶不振,因此我們對於極右派政治的思想淵源,實有必要嚴肅地重新探討。
知識分子與極右派的瓜葛關聯,在許多層面影響了當代的政治論述。歐洲的極右派政黨如海德(Jorg Haider)的奧地利自由黨(Austrian Freedom Party)與法國勒朋(Jean-Marie Le Pen)的國家陣線(Front National),在一九九○年代的選舉中大有斬獲。帶有種族中心與本土主義色彩的政黨,也在斯堪地納維亞半島、比利時與幾個剛解除桎梏的東歐國家趾高氣揚。因此評論家必然要一探究竟:法西斯主義的幽靈是不是已再度出現?
在學院的領域,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向來受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海德格、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德曼等人學說的滋養,這些人都預示或實際淪為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狂熱」知識分子。可想而知,一幅令人憂心的景象已經出現:一九三○年代的反民主風潮正在死灰復燃,只不過這一回它是託身在學院左派的羽翼之下。這種淵源傳承令人憂心忡忡,猶如再度印證了一句歷史悠久的政治格言:「物極必反」(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
勢力龐大的後現代主義在今日似乎已陷入困境,除了畫地自限的學術界之外,它的「揮別理性」(farewell to reason)計畫一直未能落地生根。後現代主義關於人類解放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s)已然結束的大膽宣示,迴響也稀稀落落。更有甚者,當年以言論和行動激發「一九八九年革命」的東歐國家異議人士,已經成功地運用「人權」的論述來搖撼極權統治。藉由這種方式,一度被文化界左派貶抑為美國霸權工具的西方人文主義(Western humanism),又再度整裝出發。
一九八○與一九九○年代,學院左派曾經嘗試以「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這個旗幟鮮明的反普世價值概念,來取代關於民主合法性的論述;然而這種作法充滿矛盾、困難重重。認同政治是一種文化自我肯定的反政治(anti-politics),在憲政與法治基礎穩固的政治實體中,看似理據充分而且引人入勝。憲政與法治的條件能夠創造出一個政治空間,一道免於政府干涉的「魔牆」(magic wall),讓人們在探討文化認同各項要素的時候,不至於鄙夷踐踏其他與之競逐的認同要素。但是在憲政法治保障付諸闕如的地方,例如波士尼亞(Bosnia)、盧安達(Rwanda)與阿爾及利亞(Algeria),認同政治卻會引發難以言辭形容的悲劇。這些前車之鑑應驗了政治現代化的一條金科玉律:要確保相互包容與共存共榮的價值,程序民主的正規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以當代政治理論的術語來說就是,這些地區的經驗印證了「作法正確」優先於「用意良善」。
事後回顧,後現代主義認定「理性」與「進步」的體制化只會導致宰制(domination)的強化而非解放,傅科(Michel Foucault)的作品在這方面最言之鑿鑿;但這種觀點實在過於犬儒,而且經不起實證。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橫掃東歐、南美洲以及(較具試探性)亞洲的「第三波」(Third Wave)民主化風潮,已經彰顯了民主人文主義的歷史貢獻,確實能夠之久遠。相反地,我檢視了一九三○年代以降的例子,發現從原則層面敵視民主價值的心態,很容易就會帶來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後果。
當代最大的諷刺之一就是,法國既是公認的後現代主義哲學發源地,也是後現代主義消沉最快、最徹底的國度。從一九七○年代到一九八○年代,人文主義形同一座堅強的堡壘,足以抵擋「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的倒行逆施,後者在東歐、毛澤東的中國、波布(Pol Pot,曾經留學巴黎)的柬埔寨,引發沒有人可以否認的災難。法國知識分子很快就體認到,後現代主義者軟弱的相對主義立場,欠缺道德上與觀念上的資源,無法抗衡暴政在國內與國外造成的不公不義。因此法國知識分子他們重新肯定人權,視之為當代政治不可逾越的一道地平線。
正因如此,後現代主義在今日的式微,與近年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人文主義的復興意謂著後現代主義的凋亡。極權政體是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經驗,它加諸予我們一項新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讓蘇聯的勞改營(Gulag)或納粹的奧許維茲(Auschwitz)集中營從此絕跡。如今我們已經知道,民主與極權這兩種政權有無可化解的差異。儘管民主政體在實務層面留下許多敗筆,但仍然具備極權社會望塵莫及的內部政治變革能力。像後現代主義這樣的論述,一方面大力宣揚文化相對主義,一方面對民主規範態度模稜,顯然已經無法滿足這個時代在道德與政治層面的要求。
儘管本書的主旨是要探討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糾葛,其中有幾位是後現代主義的大師;但是我並無意將他們連坐入罪(guilt by association)。在歷史上,法西斯主義一心鼓吹富國強兵的價值,然而後現代主義的政治思想傾向於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全面質疑包括民主在內的各種政治體制。從實務的觀點來看,這種態度意謂著後現代主義告別了現實世界的政治,轉而訴諸虛無飄渺、揣測紛紜的「政治」討論。
本書批判後現代主義另有一番目的。我關切的重點在於:就某個層面而言,後現代主義對於「理性」與「真理」的敵視,言之既難以成理,在政治上也是自廢武功。它對邏輯與論證的不信任已走上偏鋒,導致其信徒茫然無所適從,一遇上道德與政治問題就束手無策。為了實踐新尼采(neo-Nietzschean)學派「懷疑的詮釋學」(hermeneutic of suspicion),理性與民主被降格為無法信任的對象,從而導致政治上的無能為力:放棄在人世間採取有效行動的能力。專為一群門徒量身打造的深奧理論,恐怕會淪為虛有其表的作法,本身之外別無目的。
由是之故,後現代左派陣營正干冒風險,在民主最需要規範性資源的歷史時刻,將這些資源剝奪殆盡。每逢危機時刻,諸如當前全球對抗明目張膽危及人類基本權利與自由的恐怖主義,當務之急是維繫「最低限度民主」(democratic minimum)的要素。然而後現代政治思潮貶抑合縱連橫與尋求共識的重要性,轉而青睞認同政治與政治鬥爭,形同將這個傳統打入冷宮,也因此繼承了「左翼主義」(leftism)最有問題的特質:以犬儒心態認定,所謂民主規範不過是掩護既得利益階層的一道帷幕。不可諱言,民主規範有可能也的確會淪為一道帷幕,但是它們也提供了一股非常重要的倫理力量,足以揭露並轉化那些宰制社會的利益階層。過去三十年來,許多原先僻處邊緣的社會團體(女性、同性戀、少數族裔),在政治領域大有斬獲,驗證了一種海納百川的政治邏輯,顯示民主的準則與體制確實能夠讓政治與時俱進。將這些潛在價值完全揚棄,就等於是封殺了政治進步的可能性。
後現代主義界定(Note on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無疑是學術界用得最浮濫也最混淆的術語之一,因此基本的意涵釐清與界定有其必要。
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主要濫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築與藝術的演進。在這兩個領域,現代主義美學的核心觀念如形式主義、困難性、深度以及作為「天才」的藝術家,都已經日暮途窮。因此後現代藝術另闢蹊徑,強調通俗化、實用化與平民化的精神,沃荷(Andy Warhol)的普普藝術(pop art)畫像,范裘利(Robert Venturi)的重新發現美國建築語法(「向拉斯維加斯學習」),都是這種新精神的反映。在視覺藝術領域,後現代主義標誌著從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錯綜複雜,轉向一九六○年代藝術界的「新直接性」(new immediacy):歐普藝術(op art)、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表演藝術(performance art)與即興演出(happenings)。至於建築領域,後現代主義隱含著對「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排斥,撻伐千篇一律令人窒息的「玻璃與鋼鐵盒子」(包浩斯〔Bauhaus〕的功能主義),推行以隨機或特定的方式借用傳統手法。文學領域的後現代主義趨向,在於嘗試各種「後設小說」(metafiction)的可能性:探討或質疑文學自身存在理由(raison d’ête)的文學。
後來在「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或法國「理論」(theory)的衝擊之下,後現代主義擴大攻擊現代性的認識論與史料學(historiography)預設觀念:客觀真理與歷史進程。一九八○年前後,後現代主義(藝術領域)與後結構主義(哲學領域)的信條,在北美洲學院知識分子的思維想像中融合為一。
本書論及後現代主義時,主要是指涉前文所述最後一種現象:以「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尼采)、「主權」(sovereignty,巴岱伊)、「另一個開端」(other beginning,海德格)、「延異」(différance,德希達)或「另一種身體和愉悅的經濟學」(different economy of bodies and pleasures,傅科)之名,來否定現代性對於知識和文化的預設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