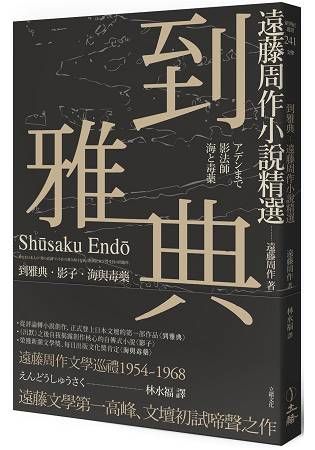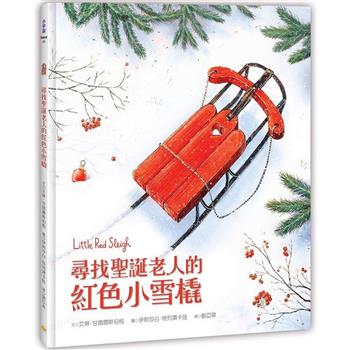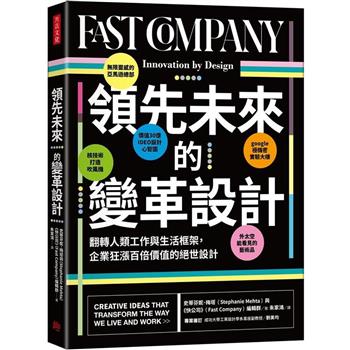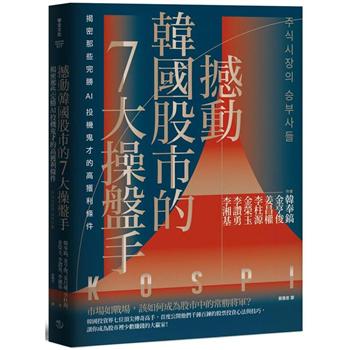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遠藤周作文學巡禮1954~1968】
遠藤文學第一高峰、文壇初試啼聲之作
‧從評論轉小說創作,正式登上日本文壇的第一部作品〈到雅典〉
‧《沉默》之後自我揭露創作核心的自傳式小說〈影子〉
‧榮獲新潮文學獎、每日出版文化獎肯定〈海與毒藥〉
本書所精選的三篇作品,在遠藤周作的創作生涯中皆具有獨特意義,各發異采。其中,〈到雅典〉之中譯版亦是首度在台發表,深具出版價值。
〈到雅典〉為遠藤從評論書寫轉至文學創作的小說處女作,本文作於一九五三年遠藤自法國留學三年歸國之後,發表後而受到文壇重視。小說某種程度記錄了他孤身異鄉期間的觀察、思考與心境轉折。遠藤曾表示,〈到雅典〉包含了後來他全部作品的方向與題目,即使日後發表過諸多類型的主題小說,此短篇仍是他所愛戀的原初之作。
〈影子〉乃近於自傳式的書寫,亦是遠藤自我揭露創作核心的作品。文中寫道:「長久以來,我的信仰在某種意義上與對母親的愛連結,也和對您(神父)的畏敬連結。」母親與宗教向來是遠藤不斷深掘、冶煉、打磨的文學命題,亦是其生命河流的源頭。除了透過書寫來釐清並深化對母親的依戀,作者更欲藉文中神父的際遇凸顯信仰與人性的掙扎,體現其所說過的:「宗教文學不是歌頌神或天使的,最重要的是描寫人性」此一寫作宗旨。
〈海與毒藥〉的寫作素材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發生在九州大學附屬醫院對美軍俘虜實施人體解剖的事件,主要是想藉此探討日本人欠缺「罪與罰」的意識,觀點深受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對東方人「無自我主張」的批評之影響。本文於一九五七年發表連載,不僅獲每日出版文化獎與新潮社文學獎肯定,更數度再版,引發廣大迴響,無奈卻受到事件當事人的指責,遠藤為此相當難過,澄清本文並非「事件小說」,他也無意譴責當事人,而是希望能透過角色的覺醒——產生罪的意識——到承認神的存在的這段過程,呈現出神與罪的意識兩者互為表裡的關係。
作者簡介:
遠藤周作
近代日本文學大家。一九二三年生於東京,慶應大學法文系畢業,別號狐狸庵山人。一生獲獎無數,曾先後獲芥川獎、新潮社文學獎、每日出版文學獎、每日藝術獎、谷崎潤一郎獎、野間文學獎等多項日本文學大獎,一九九五年獲日本文化勳章。遠藤承襲了自夏目漱石、經芥川龍之介至崛辰雄一脈相傳的傳統,在近代日本文學中居承先啟後的地位。
生於東京、在中國大連度過童年的遠藤周作,於一九三三年隨離婚的母親回到日本;由於身體虛弱,使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未被徵召入伍,而進入慶應大學攻讀法國文學,並在一九五○年成為日本戰後第一批留學生,前往法國里昂大學留學達二年之久。
回到日本之後,遠藤周作隨即展開了他的作家生涯。作品有以宗教信仰為主的,也有老少咸宜的通俗小說,著有《母親》、《影子》、《醜聞》、《海與毒藥》、《沉默》、《武士》、《深河》、《深河創作日記》等書。一九九六年九月辭世,享年七十三歲。
譯者簡介:
林水福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博士。曾任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副教授、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台灣文學協會理事長、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副校長與外語學院院長、文建會(現文化部)派駐東京台北文化中心首任主任;現任南台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授、國際芥川學會理事兼台灣分會會長、國際石川啄木學會理事兼台灣啄木學會理事長、日本文藝研究會理事。
著有《讚岐典侍日記之研究》(日文)、《他山之石》、《日本現代文學掃描》、《日本文學導讀》(聯合文學)、《源氏物語的女性》(三民書局)、《中外文學交流》(合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源氏物語是什麼》(合著);譯有遠藤周作《母親》、《影子》、《我.拋棄了的.女人》、《海與毒藥》、《醜聞》、《武士》、《沉默》、《深河》、《對我而言神是什麼》、《深河創作日記》、《遠藤周作怪奇小說集》、《遠藤周作短篇小說集》、《到雅典》;石川啄木《一握之砂》;井上靖《蒼狼》;新渡戶稻造《武士道》;谷崎潤一郎《細雪》(上下)、《痴人之愛》、《卍》、《鍵》、《夢浮橋》、《少將滋幹之母》《瘋癲老人日記》、《刺青》、《鑰匙》;大江健三郎《飼育》(合譯、聯文);《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合譯);與是永駿教授編《台灣現代詩集》(收錄二十六位詩人作品)、《シリーヅ台湾現代詩ⅠⅡⅢ》(國書刊行會出版,收錄十位詩人作品);與三木直大教授編《暗幕の形象―陳千武詩集》、《深淵―瘂弦詩集》、《越えられない歴史―林亨泰詩集》、《遙望の歌―張錯詩集》、《完全強壮レシぴ―焦桐詩集》、《鹿の哀しみ―許悔之詩集》、《契丹のバラ―席慕蓉詩集》、《乱―向陽詩集》;評論、散文、專欄散見各大報刊、雜誌。研究範疇以日本文學與日本文學翻譯為主,並將觸角延伸到台灣文學研究及散文創作。
章節試閱
到雅典
明天,是我離開歐洲的日子,女孩送我到馬賽。
兩人住宿碼頭前的小旅館。夕暮。額頭緊貼房間的窗戶往下看,夕陽照射下的岸邊,無數像中國帆船的茶褐色小舟群集,水手們以我不懂的話叫嚷著。
「那是什麼?」
「賣生蠔和海草的小船哪!」女孩回答,手掌按住太陽穴向床鋪倒下。從窗戶照射進來的夕陽,無情照在女孩臉上。
「去吃生蠔吧!」我說;但女孩像化石,動也不動。
夜晚來臨。黎明,含鹽的白色冷風從開著的窗戶進來,吹醒了我。碼頭還靜悄悄的。黎明微光中,只有帆船的帆尾形成細細的灰色影子,微微震顫。我看女孩,眼睛睜得大大的,空虛地望著天花板。臉頰有淚光。「天亮了,女孩也要走了。」我心想。
船,十時半出發。九時整理行李,結帳,沒事可做了。我們默默無語,相對著。聽到隔壁房間客人打開的收音機的歌曲。
天亮了
你,就要走了
太陽照著街道
在門口,我握她的手。那隻手白皙,乾淨。我在這個國家,握的最後的手掌。
「往後,有什麼打算?」
「什麼打算?」女孩的臉扭曲,劇烈震顫。「什麼打算?要活下去呀!」
十時半,稍早到D碼頭一看,船已經橫靠著。是三四千噸的老舊貨船。船身黑色油漆,處處剝落,像皮膚病,其他白色部分也生鏽,呈紅褐色。
繞到船尾,從寫著馬德烈努船名下的洞,不斷有像紅色的嘔吐物排入海中。
甲板上,頻頻使用鐵鍊堆積貨物。因汗水而發亮光的男人,邊工作邊叫喊著「安啪」或「阿列鐵」。我把自己的票給其中一人看,問四等船艙在哪裡?
「甲板下邊呀!」他說。「貨物取出後的船艙呀!」
登上甲板一看,已經堆在那裡的木箱子,佔滿了整個地方。每個木箱都用白漆寫著雅典。大概是試發動吧!微微的震動從腳下傳來。
寫著 4eme classe 的標示下,有鐵製梯子幾乎垂直下來。漆黑!那裡也跟剛才一樣,有木箱靠著船壁堆積著。
一個胖黑人女性,在那貨物箱下躺著,用右手腕遮著臉。
「四等,就是這裡吧?」我問;黑人女性沒回答。我儘可能遠離那像被日本的布袋包裹著的熱騰騰肉體,但還是跟她一樣把行李箱放在地板上,躺下來。
非常暗,不只是這樣,還有令人難耐的,熱。透過裝在一邊船壁的三個圓窗,天花板上波影搖晃不止。從那窗戶可以看到灰色倉庫。
取下船艙的鐵製天花板,兩個船員探出猴子般的臉。
「喂!你們、到前邊去。要卸貨了!」
「輕輕放下來,黑黑的阿桑生病呢!」另一個男人說。
「生病!既然生病,為什麼、搭船。咦~為什麼、搭船呢?」
「不知道哪!問問聖母吧!」
上貨非常慢,因此,船離開馬賽已是黃昏。夕暮,船員過來說,來拿吃的東西吧!到引擎室旁的煮飯處,拿了放在大桶子裡的白色液體,和兩三片乾麵包。我把它搬到船艙,放在躺在木箱下的黑女人面前。「吃嗎?」我問她;她臉靠著右手腕,只輕輕搖頭。她的身體很燙。
船開始移動時,我一個人到甲板。天空已經帶有藍色;但西方有金色邊緣的雲。大的光束從雲的裂縫灑向遠處黝黑的海。然而,夕靄中馬賽的街道浮現紅和藍色燈光。我最後看到的歐洲風景;而那個女孩,無疑地摻雜在這無數的燈裡、無數的生之中的某處。
隨著船向西南行,海逐漸帶暗黑色,波浪也喧囂著。我靠著木箱一直注視著上下或斜向圓窗玻璃的白色海面。海的顏色有時一直蒼白而冷。有時,變為綠色、亞麻色。波浪從旁邊過來時,船發出乾而單調的韻律咿呀著。
黑人女性一直躺著,似乎暈船而難過。暈船是沒人幫得了忙的,因此,我只幫她拿食物,沒說話。
上了船,我似乎喪失了思考力。斷斷續續,想起老舊的事、巴黎、巴黎後巷的一角、常在那兒休息的聖敘爾比斯(Saint Sulpice)公園的風景、夕暮地鐵中油漆的濕臭味等;但是我
沒有挽留它們的能力。(已經離開歐洲了)我心想。於是,想起長久住院的那間病房、放在病房窗戶的錢葵、滿是灰塵的盆子。
跟女孩的認識,是在病情較輕、出院之後。已無心到大學念書了。之前的住宿處,對我的病有所顧忌,要我搬出去。聽朋友說,接近森地方有蘇俄人寡婦出租房間。我認識女孩就是住在這宿舍時。
女孩住在我的隔壁,父親是住在鄉下的退役軍人,巴黎沒有親戚或寄居處。她白天上大學,晚上當家教或當保母賺錢。房客只有我和她,所以有空時會來聊天。
「日本漂亮嗎?我有錢之後想到印度和日本旅行。」
把玩散置房間的日本製花瓶和人偶,她喜歡拿富士山和櫻花想像這個國家。喜愛洛帝(譯註:Pierre Loti, 1850-1923,法國小說家)的年紀,不會浮現侵略國家或軍國主義日本的念頭。就我而言,女孩躲到日本的幻影之上是安全且輕鬆的。卑怯的我,星期日帶她到吉美美術館,詳細解說韓國和中國的陶器、佛像,避免打破她的幻影。
原本,並非沒有打破這幻影的事件。大學的朋友到她房間來,窸窸窣窣的交談聲,有時也傳到躺在隔壁的我耳中。「可是日本人很凶殘呀!雜誌上看過在南京殺死了幾千中國人的報導呀!」
男學生碰觸到我最疼痛的傷口時,女孩拚命辯解的神情舉止,隔著牆壁的我,一清二楚。
「那法國做過什麼呢?在北非,我們沒殺過人嗎?我們沒有裁判 Chiva 的權力呀。人,大家平等的。」
「總之,東洋人讓人感覺不好呀!」男學生被女孩的氣勢壓倒了,聲音無力。「不知道那些傢伙,在想什麼?」
「無論什麼人種都是一樣的呀!」女學生焦躁地大叫。「即使黑人、黃種人、白人,大家都一樣呀!」
是的!無論什麼人種都一樣。女孩很快喜歡我,我不拒絕她的愛,也是因為存在著人種相同的幻影。愛情裡,絲毫不會考慮到女孩的肉體是白的,我的皮膚是黃的。然而,我和女孩的第一次接吻,是到馬畢倫(Mabillon)跳舞回來的夜晚街道,那時,我對倒向牆壁閉上眼睛的她,不由得這樣叫出來。
「可以嗎?我真的可以嗎?」
「不要說話!抱我!」
如果無論什麼人種都一樣,為什麼,那時,我會發出這麼淒慘的呻吟聲呢?如果愛情超越人種和國界的話,即使短瞬間,也應該有信心才是。那時,我最後本能地面對隱藏在這呻吟聲內側的某種真實。因為害怕;然而,非面對不可的日子,那之後不到兩個月來了。那是兩人從巴黎到里昂旅行的今年冬天。我們第一次肌膚與肌膚相親的夜晚。
馬克羅尼索斯島(Makronisos,譯註:現已成無人島)的影子已經消失在水平線的前方。長久之間追著船尾的海鳥也改變方向飛回去了。歐洲終於結束了,此後,是非洲和東洋境界的開始。我記得剛剛的希臘島嶼群峰上殘留的白雪。
那天也下雪。從巴黎出發時開始,雪就下了。從里昂佩拉什(Perrache)站前寒磣的旅館窗戶,我們眺望著灰色陰霾的天空、在空中似乎冷得發抖的教會尖塔、融入夕靄的蒼白街道的屋頂、屋頂。
「我,小學時住過里昂呀!」
女孩臉頰貼上冰冷的玻璃窗,閉著眼睛想起從前,嗤嗤地笑著。我們在站前小而陰暗的店裡買了麵包和乳酪,在那房間裡分著吃。然後,讓雪濕了腳,在後巷冷冷的電影院看費南代爾(Fernand Joseph Désiré Contandin, 1903-1971)的舊喜劇片後回來。
除了睡覺,沒別的事了。彼此雖然避免碰觸那件事;但這一夜一定會來臨,是從巴黎出發前兩人已經知道的。
房間有鋪著花朵圖樣床單的大床和附了鏡子的大型衣櫥(Armoire)。我坐在床鋪邊緣,看著映在鏡中自己疲累的臉。女孩在屏風後邊,傳出褪下內衣的聲音。真像沙子溢出的乾燥聲音。
「轉向前方,把燈關掉哪!」女孩洩漏出嘶啞的小小嘆息聲。「討厭哪!不要看。」然而,她沒有關燈,雙手伸向沒有移開眼光的我,帶著似乎難受的表情靠過來。
屏息,兩人相擁,久久。沒有像那時覺得金髮那麼美。連一個斑點都沒有的白色裸體,金髮從肩窩往下滑。女孩在門那裡,我拉上窗簾,轉向窗戶方向。燈開著的,兩人的裸體完全映照在大型衣櫥的鏡子裡。
最初,我,不認為鏡中映像真的是我的身體。以日本人而言,生過病的我有著勻稱的裸體。身高也跟西洋人差不多,胸部、四肢都有肉,不以為恥。從肉體的型態來說,我抱白人的女性姿勢應該不會不協調。
然而,映在鏡中的自己,換成另一個人。在房間燈光照射下發出白色光輝的女人肩膀和乳房旁邊,我的肉體毫無生氣,帶暗黃色,死氣沉沉。從胸部到腹部,還不那麼明顯;但是,從脖子附近開始,這黃濁的顏色越富含灰暗光澤。而女孩的和我的身體糾纏的兩種顏色,無絲毫的美與協調。反而是醜陋的。讓我聯想到附著在潔白花瓣上的土黃色蠐螬。那種顏色本身會讓人想起膽汁或他人的分泌物。想用手遮掩臉和身體。卑怯的我那時,關掉房間的燈,黑暗中想讓自己的肉體消失……。
出發之後,黑人女性一直仰臥著。右手放在臉上一動也不動,有如死了。行動敏捷的蟑螂群,在船艙壁上跑,在她像棍子的雙腳和腳趾上穿梭。我每次幫她拿來的食物幾乎都沒碰,乾巴巴地留在碗底。
今天,我去拿食物時,告訴船員她生病了。
「我不知道呀!」他回答。「總之,似乎不關我的事呀!」
躺在船艙時,我注視著眼前這熱熱的、黑褐色的肉體。那肉體是一個物體。我真的認為那肌膚顏色是醜陋的。黑色是醜陋的,而黃濁色更可憐。我和這黑人女性永遠屬於那醜陋的人種。我為什麼只以白人的肌膚當美的標準呢?那經緯,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直至今日為止雕刻或繪畫裡畫的人,美的基本,一切都從希臘人的白色肉體產生,一直繼續維持下來?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再怎麼惋惜,我和黑人在白皮膚人的面前,於肉體這一點,忘不了可憐的劣等感。
下雪夜的翌日,晴天。女孩帶我到街上。陽光照射在厚厚的積雪上,感到目眩。開朗的笑聲,久違的藍空下欣喜的叫聲,在街上四處洋溢。年輕男女在路上玩弄滑雪道具,服務生拍落咖啡桌上的雪。
在雪的亮光中,我眼中彷彿看得到,知道從昨夜起女孩突然把心給了我。邊走邊高興地把金髮的頭靠過來,像綠色鸚鵡的眼睛瞄我的眼睛,像是確認愛情似地在互握著的手掌裡不時豎起尖銳的指甲。有如白種女人的愛情表現,今天的我為何無法呼應呢?心底有著什麼黑塊,那黑塊讓現在的我無法坦然接受女孩的愛撫。覺得那是囉嗦討厭的。愛慾是兩者的自尊心保持平衡呢?或者一方是主人,另一方非奴隸不可呢?了解我的肌膚比女孩的更醜陋的今天早上,到昨日為止無意識地,不!或許是因為無知而支撐我與女孩之間的平衡,昨夜之後陷入崩塌。無法拂拭我立於弱者的立場的心情。
到雅典
明天,是我離開歐洲的日子,女孩送我到馬賽。
兩人住宿碼頭前的小旅館。夕暮。額頭緊貼房間的窗戶往下看,夕陽照射下的岸邊,無數像中國帆船的茶褐色小舟群集,水手們以我不懂的話叫嚷著。
「那是什麼?」
「賣生蠔和海草的小船哪!」女孩回答,手掌按住太陽穴向床鋪倒下。從窗戶照射進來的夕陽,無情照在女孩臉上。
「去吃生蠔吧!」我說;但女孩像化石,動也不動。
夜晚來臨。黎明,含鹽的白色冷風從開著的窗戶進來,吹醒了我。碼頭還靜悄悄的。黎明微光中,只有帆船的帆尾形成細細的灰色影子,微微震顫。我看女孩,眼睛睜...
推薦序
探討日本人罪的意識╱林水福
遠藤周作在成瀨書房刊行的《到雅典》的〈後記〉寫道:
〈到雅典〉是我最初的小說。一九五三年從三年留學生活歸國,治病期間寫成的作品,發表於《三田文學》。恩師佐藤朔先生說以處女作而言,不錯;但是文壇前輩的批評,嚴厲。即使今日仍愛戀這篇作品,或許所有作家皆如此,因為覺得這短篇包含後來我全部作品的方向與題目。
〈到雅典〉的開頭,女孩從巴黎到馬賽送明天要離開歐洲的主角。去年(二○一六)已公開現實中這位女學生名叫富蘭索瓦茲,從巴黎經里昂到馬賽,在馬賽的飯店一起度過留法的最後一夜。遠藤《留法日記》(一九五二年九月~一九五三年一月)記載這日:「即使最後一夜,也沒有碰妳。」
開頭部分乍看會以為是戀愛小說;其實,不是。如上文「這短篇包含後來我全部作品的方向與題目。」具體而言,是什麼?有哪些作品?
一是人種問題。白人的優越感,其他人種如黑色人種,黃色人種的卑下,與被歧視感。這部份後來有《白色人種》《黃色人種》等作品。
二是神,或者說宗教信仰的問題。這是遠藤一輩子小說中追求的主題。如《海與毒藥》、《沉默》、《醜聞》、《武士》、《深河》等皆是。
三則是惡的問題。遠藤在《醜聞》中也觸及這個問題,本來有意再深入挖掘,後來又回到以宗教為主題的線上。結果,終其一生,對於惡,未有更深入的探討。
〈影子〉與〈母親〉是我最喜歡的遠藤的短篇小說。〈影子〉寫的是曾經是主角的「我」的母親的輔導神父,母親甚至希望自己的兒子能以神父為榜樣,將來也當神父。神父是主角追尋的模範,人生的標竿;然而,這樣的神父後來卻傳出與女信徒有不正常的交往,謠言四起……。有一天,主角的「我」帶著未婚妻,到神父那兒,準備跟神父報告婚事,請求祝福。不意,一打開門,看到神父摟著的就是傳言中的女性……。
遠藤曾說過,宗教文學不是歌頌神或天使的,最重要的是描寫人性。從〈影子〉我們可以看到信仰與人性的掙扎,神職人員可能遭遇到的「試煉」與「折磨」。
〈海與毒藥〉
1
〈海與毒藥〉先在《文學界》(一九五七年六、八、十月號)連載,翌年四月,由文藝春秋社發行單行本。全書以三章構成,第一章「海與毒藥」,第二章「受裁判的眾人」,第三章「到天亮為止」。同年(一九六○)十二月同時獲第十二屆每日出版文化獎與第五屆新潮社文學獎。十個月之內再版七次,兩年後同時被收入新潮文庫和角川文庫。
〈海與毒藥〉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發生在九州大學附屬醫院,以美軍俘虜實施人體解剖的事件為素材寫成的。作者在這部小說中,主要是想探討日本人欠缺「罪與罰」的意識,不是「事件小說」,作者也無意藉小說譴責當事人。可是,後來遠藤還收到事件當事者寄來的指責信件,為此,他感到十分難過。
作者在〈出世作之際〉(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十三日,《讀賣新聞》)中說:
那時候,《文學界》新總編輯上林氏剛上任不久,他是我獲芥川獎時《文藝春秋》的總編輯。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有事商量請我到出版社去一下。在文藝春秋地下室的俱樂部中,上林氏問我願不願意寫一部長篇小說看看……。
我心中早就有想寫的題目,素材方面也早已心中有數。我馬上搭火車前往九州、福岡蒐集資料,調查戰時發生在這所大學醫學部的美軍俘虜人體解剖事件。我腦中毫無想描寫那件事的念頭,我打算把那件事在內部加以改變、轉換到不同次元的世界。……靠著草場氏的幫忙,始得以取得當時的資料和訪問到事件的有關人士。
回東京後開始執筆,花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分成三部,登在『文學界』。可是,已轉移到不同次元世界的這部小說,卻被當成是事實的描寫;後來還收到事件當事者的抗議書,和自稱認識小說中登場的醫生的信件。我感到非常難過,因為我毫無藉著小說審判那些人的意思呀!
至於為何取名為海與毒藥?這是遠藤到福岡取材,準備回東京的前一天,下著毛毛細雨,他跑到小說舞臺的九大醫學院的屋頂上,斜倚著扶手,「注視著雨中朦朧的街道和大海。這時,腦中浮上〈海與毒藥〉這個題目。」
毒藥,象徵罪,而海呢?遠藤心儀的法國作家莫里亞克(Francois Mauriac)作品中,海「象徵孤獨、永恆,同時也意味著恩寵」(〈作家與讀書〉)。〈海與毒藥〉中,遠藤也以象徵性手法描寫海,除了上田信聽到的陰鬱的海鳴,宛如自己不祥的命運之預兆外,皆與勝呂有關。第一章的「楔子」,說話者的「我」的前面「海,湛藍的海,彷彿要滲入我眼中」。此外,勝呂看到的海大多是黑色的,黝黑的;夢中看到自己在黑色的海中如碎片般被海浪衝擊。海,有時是湛藍如粼粼波光,有時是黝黑而陰鬱的;小說的結尾,勝呂在黑暗中「注視著波光粼粼的大海,似乎想從那兒尋找出什麼?」的時候,「每當綿羊般的雲朵走過時……」的詩句不禁衝口而出,事實上這部分詩句取自近代早夭詩人立原道造〈雲之祭日〉詩篇。「天空喲!你撒落的是,白的、純白的、棉花的行列!」中的「棉花的行列」暗示著「神的羔羊」;而「他嘴裡好乾燥」是象徵著對神的渴望、企盼。
2
第一章可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搬到東京新興住宅區的「我」的視點,描寫到知道當地開業醫生勝呂的過去的經緯;第二部分是描寫戰爭末期勝呂和同事戶田到參加人體解剖的過程。其實,第一章的第一部分,遠藤曾單獨以短篇小說,題名為〈人面獅身的微笑〉投給「中央公論」,結果被封殺。
第一部分的梗概是:八月盛夏中,「我」搬到從新宿搭電車需要一小時車程的新住宅區來,在那兒認識了加油站和西服店的老闆以及勝呂醫師。加油站老闆在公共澡堂裡,頭上抹著肥皂邊得意洋洋地對「我」說以前在中國大陸的暴行和殺人的經驗,最後還告訴「我」服役時當憲兵的西服店老闆殺過更多的人。「我」到九州參加小姨子的婚禮,無意中知道勝呂醫師是F醫大人體解剖事件的關係者之一,因此詳細調查該事件。回到東京之後,「我」再訪勝呂醫院,告知去過九州。勝呂知道自己的過去為人所知時,自言自語地說:「那是沒辦法的事!在那種情況下真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以後也一樣,我自己也沒有信心,將來如果還遭遇到同樣的情況,我或許還會那麼做……」回家途中,路過西服店,「我」注視著櫥窗中「白人男模特兒」的「謎樣的微笑」,想起「早上四條腿,中午兩條腿,晚上三條腿的動物是什麼……」的「人面獅身像的謎題」。
遠藤對這部分的解釋(見《現實與文學》一九六三年七月與窪田精對談)是:
我有意從日常時間寫起,我們讀戰爭小說時會注意到有這樣的人;可是,那跟我毫無關係,會有我的手仍然是乾淨的感覺。我很討厭這樣子,因此,我有必要寫普通人,連加油站老闆都殺過人,同時,無論如何非把日常看到的櫥窗模特兒轉變為人面獅身的影像不可。基於此,勝呂必須和大家站在同一條線上。
在這裡,遠藤混合了話者「我」的觀點與作家的觀點,目的是希望讀者腦海中能將現在與過去的影像重疊在一起。同時,體認到這「故事」就發生在你我身旁,而非少數特定且與自己無關的人物身上。日本名評論家佐伯彰一說這部分是「印象鮮明的楔子」;作者也認為在這部分「埋下很精采的伏筆」,而且肯定是〈海與毒藥〉中,以小說而言是「最好的部分之一」。
從第二章起小說的舞臺轉移到F大醫學院。主角勝呂和戶田服務的大學醫院裡,為了爭奪下一任醫學院院長的職位,教授之間展開了一場權力鬥爭的醜劇。戶田和勝呂所屬的第一外科主任橋本教授,為了要奪取院長寶座,對田部夫人——大杉醫學院院長的親戚——提前動手術,希望藉手術的成功能獲得大杉門下內科系醫生們的支持,結果卻把患者醫死了。另一方面,為了要討好當時最高權力者的軍部,於是答應對俘虜做人體解剖。小說中,作者所要描寫的重點並非動手術和人體解剖本身,而是透過手術和人體解剖烘托出日本人缺乏罪的意識。這裡所謂的罪,並不是法律上的罪,而是承認神的存在,從而產生的宗教上的罪。神與罪兩者互為表裡。
〈海與毒藥〉中,作者把勝呂塑造成:滿臉倦容,對一切事物均不感興趣,即使犯了罪也產生不了倫理上的苛責,常自言自語道:「不管什麼事怎麼樣都無所謂」的人物。以遠藤而言,這種人物的造形並非從〈海與毒藥〉開始,在〈我的小說〉(《朝日新聞》,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中,他說:
有一條大直線把從〈到雅典〉經〈黃色人種〉到〈海與毒藥〉連接起來。〈到雅典〉的主角在〈黃色人種〉中成為「我」;而〈黃色人種〉的我,在〈海與毒藥〉中,不用說就是主角的勝呂醫師和戶田醫師了。
勝呂參加人體解剖時的部分對話,很明顯地刻劃出勝呂的個性,例如:
「你啊!也真是阿呆一個。」
戶田小聲地說。
「哦!」
「想拒絕的話還有機會呀!」
「嗯!」
「不想拒絕嗎?」
「嗯!」
「到底有沒有神?」
「神?」
「是呀!說來荒誕;人,無論如何是逃脫不了命運——那推著自己的東西——的擺弄;而能讓自己從命運中獲得自由的就是神吧!」
「這我就不懂了!」勝呂把火已熄滅的香菸放到桌上回答著。
「對我來說,有沒有神都無所謂。」(一五三~一五四頁)
怎麼樣都無所謂。我答應參加解剖,或許是因為那藍白色的炭火在作祟;或許是由於戶田的香菸在作怪;隨便怎麼樣都無所謂,不再想它了。睡覺吧!多想也沒用,這世界光靠我一個人是起不了作用的!(一五○頁)
「來一下!」戶田突然低聲催促他。「過來這邊幫忙!」
「我——不行呀!」勝呂低聲說:「我還是應該拒絕的。」
「阿呆!你在說什麼?」戶田回過頭來瞪著勝呂。「想拒絕的話,昨天晚上,還有今天早上,不是有的是時間嗎?現在,到了這地步,你已經走過了一半呀!」
「一半?我走過什麼的一半?」
「跟我們同樣的命運!」戶田冷靜地說。「現在—已經不能退出了!」(二○七頁)
從以上的對話,充分表現出勝呂毫無自我意志的個性。遠藤筆下,常有「弱者」出現,對什麼事都不做決定,不表示意見;遠藤個人認為,這種不表示自己的意見,無行為表現者,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行為」,所以也是一種「罪」。這種觀點受莫里亞克對東方人「無自我主張」的批評之影響。
勝呂在應該有所行動時卻「什麼都不做」,更嚴重的是他「在那兒卻什麼都沒做」。「什麼都沒做」對勝呂而言,也是一種「責任」的迴避。勝呂的行為經常表現出這種責任的迴避,在這種藉口下,勝呂對自己的行為毫無「責備」之意,這也是勝呂無「罪」之意識的特徵。
3
小說中另一個主角戶田,形象與勝呂迥然不同。勝呂在任何情況下皆選擇不採取行動;可是,戶田卻處處表現出積極的自由意志。即以參加人體解剖而言,勝呂是出自無奈而參加的,戶田卻表現出積極參加的態勢。在戶田手記中,有著欺瞞、偷竊、與表姊通姦、對女傭始亂終棄等等的告白;可是對他做那些壞事時的心理反應,我們無法不為他欠缺犯罪意識而感到顫慄。
所謂良心的苛責……從孩提時代起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他人的眼光、社會的制裁罷了。當然,我也從不認為自己是好人;我相信無論是誰,只要剝掉外面的一層皮,就都和我一樣。或許這是偶然的結果,我幹過的事從沒受到懲罰,也從未受過社會的制裁。
戶田所擔心的只是他人的眼光,或社會的制裁,此外,毫無良心上的自責。他還說:「我對別的事似乎也無感覺。……坦白說我對他人的痛苦和死亡毫不在意。」以下是病房中戶田與患者家屬的一段對話:
「醫生啊!求求您幫他打一下麻醉針。」
肺部手術後,患者不停地呻吟,不忍聽下去的家屬即使哭喪著臉哀求我,我也只是冷冷地搖搖頭。「再打麻醉藥,反而危險呀!」事實上我心裡只覺得這樣的患者和任性的家屬好囉嗦!
病房裡要是有人死了,父母親或姊妹慟哭著。我雖然在他們面前表示同情,可是,當我一腳踏出病房時,剛才的那一幕就忘得一乾二淨了。人體解剖完後,戶田看到淺井助教的臉上,絲毫找不到剛才殺過人的痕跡。那表情就跟平常吹著口哨在研究室出現的臉完全一樣,也和平常看檢查表時的表情沒有什麼不同,接下來他說:
「我的臉大概也一樣吧!」戶田痛苦地思考著。「沒有什麼變化嗎?為什麼我的心是這麼平靜?而且絲毫感受不到良心上的痛苦和犯了罪的苛責呢?我甚至感受不到奪取一條人命的恐怖。為什麼呢?為什麼我的心是如此無所感呢?」
戶田「確信」對他人的死、他人的痛苦無所感的並不只是自己,他周遭的人每一個都一
樣,這種「自信」使他的罪惡感完全麻痺了。
4
〈海與毒藥〉中有兩個與勝呂二郎和戶田剛相比,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卑微人物,即阿部蜜和佐野蜜。阿部蜜是大病房的患者之一,是「老太婆」的朋友,因而與勝呂認識,而佐野蜜是和戶田發生過關係的女僕。從整部小說的結構上來看,她們兩人不過是毫不惹眼的配角罷了;可是,作者所賦予她們的「任務」並非僅僅是微不足道的卑微人物而已!勝呂到大病房診療時,阿部蜜讀親鸞的「和讚」給老太婆聽。從她那兒勝呂知道了老太婆的身世,使得勝呂對不久之後死去的老太婆產生些許的憐憫之情。換句話說,是阿部蜜的言行促使勝呂對他人的命運和痛苦產生同情心。
當戶田決定參加人體解剖時,想起和佐野蜜的昔日往事。他想起:臉色蒼白靠在牆壁上,咬著牙強忍著痛楚的蜜的表情;想起把她打發回故鄉,當火車開動時,蜜把臉靠在窗戶上的痛苦表情;戶田因此認為「有一天自己會受罰吧!有一天自己會因過去的半輩子受到報應吧!」良心上感到痛苦,也有那麼一絲絲的犯罪意識的產生。雖然那只是一剎那之間的事,可是對毫無良心、無罪之意識的戶田剛而言,即已顯示出佐野蜜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痕跡是多麼深呀!從這角度來看,作者的確在她們身上埋下很深的意圖。
這部作品之外,作者的其他作品中,以蜜為名的女性,大抵皆有共同的特性:弱者的女性,透過她們的生活,促使毫無良心、無罪之意識的人們,良心萌芽和罪之意識的覺醒。換句話說,作者企圖透過她們的生活,告訴讀者神的存在,從而產生罪的意識。以日文原文而言,阿部蜜、佐野蜜的蜜是「ミツ」,倒過來唸即為「ツミ」(「罪」之意),而「ミツ」本身也可解釋為「光」(ミツ),即神的恩寵。因此,如前所述,神與罪的意識是互為表裡的關係。
與阿部蜜、佐野蜜相對的,上田信所扮演的是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他人的角色。遠藤在〈海與毒藥〉中本來有意將上田信塑造成惡女的主角形象(見〈創作手記〉,昭和四十年《批評》春季號,後收錄於《石之聲》)終未成功,要等到〈醜聞〉的成瀨夫人出現,作者始得以塑造出完整的「惡女」主角形象。名為「信」其實「不信」,名為「ツミ」(罪〉其實幾近於神,是遠藤的諷刺手法之一,也可見作者苦心經營之一斑。
5
前面說過本書的主題是——探討日本人罪的意識。儘管作品中出現的人物,他們的生活形態是那麼無奈、無力、無理想、無信仰,對所犯的過錯,既無良心上的痛責,也無犯罪之意識,宛如已經無可救藥;可是,作者並不讓他(她)們一直墜入罪惡的深淵,安排了「蜜」的角色促使他們覺醒,產生罪的意識,同時承認神的存在。而本書中,海的象徵之一——神的恩寵,也告訴我們神並未拋棄他們。
探討日本人罪的意識╱林水福
遠藤周作在成瀨書房刊行的《到雅典》的〈後記〉寫道:
〈到雅典〉是我最初的小說。一九五三年從三年留學生活歸國,治病期間寫成的作品,發表於《三田文學》。恩師佐藤朔先生說以處女作而言,不錯;但是文壇前輩的批評,嚴厲。即使今日仍愛戀這篇作品,或許所有作家皆如此,因為覺得這短篇包含後來我全部作品的方向與題目。
〈到雅典〉的開頭,女孩從巴黎到馬賽送明天要離開歐洲的主角。去年(二○一六)已公開現實中這位女學生名叫富蘭索瓦茲,從巴黎經里昂到馬賽,在馬賽的飯店一起度過留法的最後一夜。遠...
目錄
導讀 探討日本人罪的意識∕林水福
1 到雅典
2 影子
3 海與毒藥
遠藤周作年表
導讀 探討日本人罪的意識∕林水福
1 到雅典
2 影子
3 海與毒藥
遠藤周作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