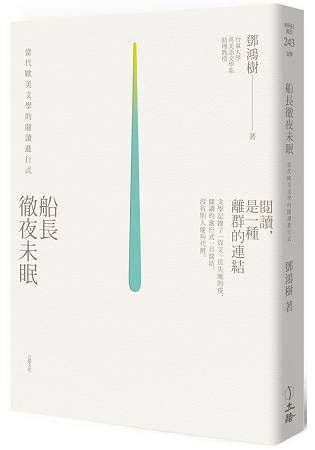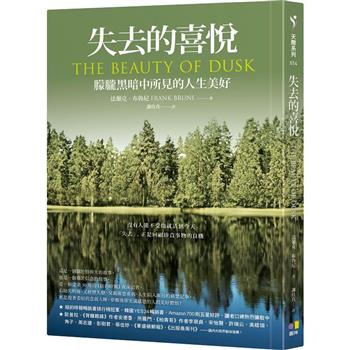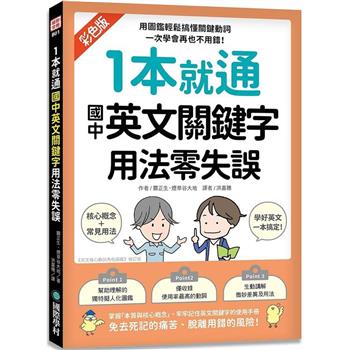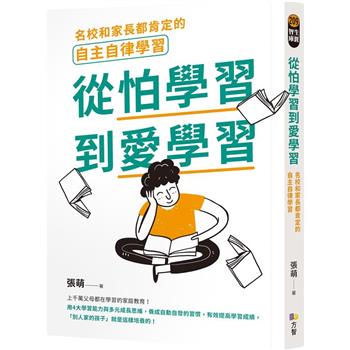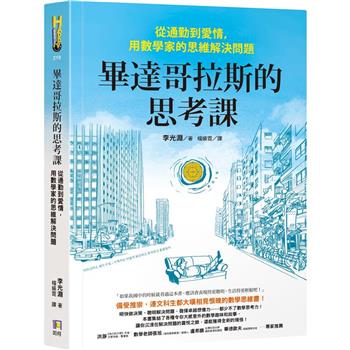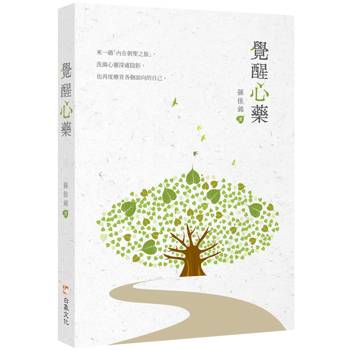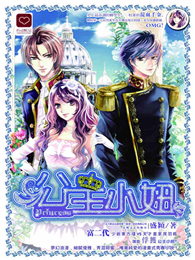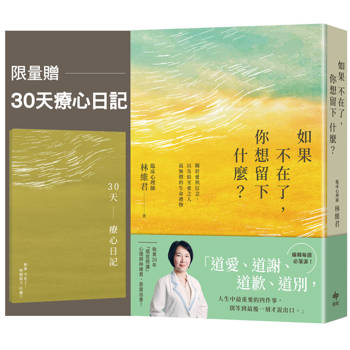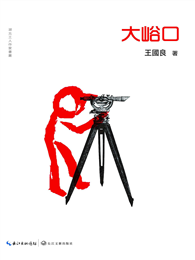閱讀,是一種離群的連結
文學記錄了一頁又一頁失眠的夜,
閱讀的進行式一旦開啟,沒有別人能夠代班。
文學記錄了一頁又一頁失眠的夜,
閱讀的進行式一旦開啟,沒有別人能夠代班。
對立與偏見,是雋永的文學題材;情感的侷限與悲劇,正是永恆的文學母題:經典文學是如此,當代文學也不例外。
「經典」曾為過去的「當代」作品。當代讀者需要當代文學,才能探究當代難題,樹立新的經典以為傳世。
在出版量急遽膨脹、電子載具可輕易大量存取的年代,「讀書」這件事反而日益艱難。畢竟書海茫茫,讀者又何嘗不茫茫然。就像旅遊需要指南,在書海中迷失的讀者也需要一位優秀的領航員。本書作者書評家鄧鴻樹先生,就是一位絕佳的伴讀者。
《船長徹夜未眠》乃針對一般讀者所寫的主題式文學評論,避開艱深的文學論述,文字精簡而不失深度,為讀者引介當代歐美文學新作與相關中文譯作,包含當代作家介紹、作品點評,以及當代文學與出版議題討論――讀書,讀人,也解讀文壇局勢。其評遒勁有力卻又溫柔敦厚,實為台灣難能可貴的精采書評作品。
吳爾芙所稱頌的「普通讀者」,也許並不在意經典或通俗,不在乎理論或流派,只是想遇見一本好看的書,就這麼簡單。閱讀,本來就該這麼簡單。盼讀者能藉本書體驗當代文學的樂趣,讓閱讀融入生活:拾起書本,維持生活裡的閱讀進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