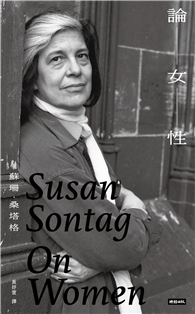法國文學泰斗、法蘭西學院巨星讓.端木松(Jean d'Ormesson),法國總統馬克宏禮讚其為「文字的王子」。
台灣重磅出版系列作品:《宛如希望之歌》、《無盡的讚歌》
本系列為讓.端木松人生最後力作,對於人生、信仰、時間和宇宙的不斷叩問,無比清晰凝煉的傑作。
「就和所有的死亡一樣,所有的出生都是個謎,而此謎的難度也許比死亡更甚。」
一部無比清晰凝煉的傑作。本書開宗明義即強調,人生充滿不確定性的眾多事物當中,唯有生與死毋庸置疑。然而,就和所有的死亡一樣,所有的出生都是個謎,而此謎的難度也許比死亡更甚。
作者認為,活著是每時每刻的事務。是最扣人心弦的體驗。是獨一無二的冒險。是最出色的一部小說。很多時候是麻煩。更多時候是苦難。有時何嘗不是幸運,有時又是恩典。它始終是驚喜、驚奇,偶爾會變成驚愕。
繼首部曲《宛如希望之歌》之後,讓.端木松以九十二歲高齡寫下這本《無盡的讚歌》。這位形而上學的偵探,始終努力不懈地追查探問,企圖為一個永不得解的問題找出答案——那個問題是:「我來這世上究竟是為了什麼?」
本書亦是作者人生的終章。在這部最後力作中,他興致昂揚地追索著問題的謎底,透過對人生、信仰、時間和宇宙的不斷叩問,思緒或輕巧或凝重,然字字句句都促使著我們去夢想、去期望、去相信:生命是我們唯一擁有的寶物。
作者簡介:
讓.端木松 Jean d'Ormesson
法國知名暢銷文學作家。一九二五年出生於巴黎,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並取得哲學教師資格。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理事會祕書長、《費加洛報》社長、部長顧問等,在外交、文化、政治等領域皆具有卓越影響力。
著作等身,一九七一年憑藉《帝國的輝煌》獲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其他代表作品包括有《宛如希望之歌》(立緒出版)、《悉聽上帝尊便》、《永世流浪的猶太人史》、《海關》、《觀看如跳舞》、《這世界終究不可思議》、《有一天我離去時還沒說夠》等。
一九七三年獲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二○一○年獲頒羅馬尼亞奧維德文學獎。法國總統馬克宏曾向其致敬,稱其「代表著法國最優秀的精神,擁有智慧與優雅,是文字的王子」。端木松於二○一七年十二月五日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譯者簡介:
張穎綺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法國巴黎第二大學法蘭西新聞傳播學院碩士。譯有《女巫》、《藍色加薩》、《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柳橙園》、《重返革命現場:1917年的聖彼得堡》(以上立緒出版)、《謝利》、《觀鳥大年》等書。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絕美之書。簡而言之,是對生命的熱愛。
——《Côté雜誌》
令人激動地揭開了作家逝世前夕所完結的故事:精緻而細密的文字,形而上學,我們短暫而美好的存在。
——《La Vie雜誌》
這部偉大的著作,關於信仰(或缺乏信仰)的聲明與表白,是對我們形而上的痛苦的回應(……),毫無疑問,這是對取之不盡的富有的反思。
——《Lion雜誌》
優雅和智慧的瑰寶,罕見而微妙的思想書。……美麗的文學作品,熱情友好,充滿智慧和瘋狂、溫柔和常識,就像一顆心,儘管受到時間的侮辱,仍然跳動著偉大詩人的永恆韻律。
——francenetinfos.com
這位學者的最後作品,憂鬱而發光,謙虛而又明亮,自相矛盾和黑暗,完美地與作家的目光炯炯、知識份子象徵、精神光芒滲透出的最後貴族氣息一致。
——Brigit Bontour
他代表著法國最優秀的精神,擁有智慧與優雅,他是文字的王子。
他散發的優雅具有傳染性,在生活的灰霾下,人們在他身上找到了解藥。
請允許我在棺槨上放一支筆,簡單的一支筆,卻具有魔法。今日,我們對他的魔法心存感激,永遠銘記。
——法國總統馬克宏,2017年12月8日於讓.端木松國葬儀式致詞
媒體推薦:絕美之書。簡而言之,是對生命的熱愛。
——《Côté雜誌》
令人激動地揭開了作家逝世前夕所完結的故事:精緻而細密的文字,形而上學,我們短暫而美好的存在。
——《La Vie雜誌》
這部偉大的著作,關於信仰(或缺乏信仰)的聲明與表白,是對我們形而上的痛苦的回應(……),毫無疑問,這是對取之不盡的富有的反思。
——《Lion雜誌》
優雅和智慧的瑰寶,罕見而微妙的思想書。……美麗的文學作品,熱情友好,充滿智慧和瘋狂、溫柔和常識,就像一顆心,儘管受到時間的侮辱,仍然跳動著偉大詩人的永恆韻律。
——fra...
章節試閱
1
感謝上蒼,我會死。就和所有人一樣。就和你們一樣。很可能先你們一步:畢竟我已經活了很久,我的人生道路已接近盡頭。儘管死亡必定會到來,但也沒有任何事比它更隨性而至了。任何一位小我許多歲、身強體健的讀者也可能比我先死。世事難料。這本小書開宗明義必須強調的是:沒有任何一件事是確定的。
在這世上可能會發生、充滿不確定性的眾多事物當中,只有兩件事是確鑿無疑的。第一:我們已經出生。第二:我們會死。只要活著,誰都別想逃脫死亡的命運。我們活著,所以我們都會死。波舒哀寫道:「從出生起,我就受到有生就必死的法則支配。」
2
我們會死,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活過。那麼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出生?我們來到世上真的有必要嗎?甚而對這個世界非常有益嗎?每個人的出生都是預定好的嗎?或者純粹屬於偶然?是否有一條律法規定我們在生命終結時死去?最初是否有一條律法規定我們要活?
就和所有的死亡一樣,所有的出生都是個謎,而此謎的難度也許比死亡更甚。
3
沒有人問過我們的意見,沒問過你們,沒問過我,沒問過任何一個活著的人:我們是否願意到圍繞著太陽運轉的八大行星裡的其中一顆,就像度個長週末一樣,在那裡待上一陣子。你們都會承認,這實在太過分了。我們的生命不屬於我們自己。它不是我們要求來的,並非我們選擇的,甚至不是我們同意接受的。它是我們被迫收下的一個餽贈—或者更恰當地說,一個出借物。我們無償就取得其使用權。或者說,我們非運用它不可。
一切的拍板定案毫無我們置喙的餘地。了不得。我們在生命舞台粉墨登場這件事,與我們自己完全不相干。起碼到現今為止,人的出生只涉及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之間展開的那些私密(總之在我們不知情下) 互動——我們每個人都毫不陌生、但是從不願想像自己的父母有過的那類交流。接著,我們就蹦出來了,多奇妙啊,我們就擁有了生命。就這樣。
我們對自己的生命或許負有一部分責任。我們有時候可能還得為自己的死亡負責,即使不是死亡本身,起碼是死亡的日期。但我們的出生絕非自己的責任。古哲先賢對此抒發的感慨不勝枚舉,例如流傳三千年的《傳道書》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索福克勒斯(Sophocle)在《伊底帕斯王》寫道:「不生在世上則尤為萬幸,若不然,出生後則求盡快返回源頭……」;蕭沆(Cioran)直言:「我未曾生養的那些孩子並不知道他們欠我多大的恩情」;三位作者都怨嘆自己的出生,三人都把生視為苦,都厭惡為世上創造增添新生命。活著的我們,首先都是受害者。承受活著然後死去——一個並非我們選擇而是強加於我們身上的命運。
1
感謝上蒼,我會死。就和所有人一樣。就和你們一樣。很可能先你們一步:畢竟我已經活了很久,我的人生道路已接近盡頭。儘管死亡必定會到來,但也沒有任何事比它更隨性而至了。任何一位小我許多歲、身強體健的讀者也可能比我先死。世事難料。這本小書開宗明義必須強調的是:沒有任何一件事是確定的。
在這世上可能會發生、充滿不確定性的眾多事物當中,只有兩件事是確鑿無疑的。第一:我們已經出生。第二:我們會死。只要活著,誰都別想逃脫死亡的命運。我們活著,所以我們都會死。波舒哀寫道:「從出生起,我就受到有生就必死的法則支配...
作者序
致讀者╱愛洛伊絲.端木松
二〇一七年六月那時候,我父親很幸福。夏季將至—一個可以大啖新鮮覆盆子(灑上滿滿糖粉)、到海水浴場曬日光浴、赤腳走在莫泰拉角(pointe de la Mortella)古代海關小徑的季節。他剛寫完《我,始終活著》(Et noi, je vis toujours,二〇一八年初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已開始動筆寫他的第三十八本書。在九十二歲之齡還有精力重拾寫作樂趣,對他來說簡直是奇蹟。儘管身體有恙,但以《宛如希望之歌》打頭陣、由《迷途者指南》(Guide des égarés)接續的三部曲計畫可望有始有終,這讓他開心不已。
接下來的六個月,從六月到十二月,他欣喜滿足看著手稿一頁頁累積,雖然從秋末開始,原本工整的藍筆字跡變得抖動。
父親始終維持著老派的手寫習慣。他沒有電腦,不用打字機。他每週把完成的幾頁手稿送去打字。隔週拿回繕打好的稿子後,會對照原稿仔細重讀一遍,確認有無誤讀錯打之處,接著重新修改、潤飾原來的內容。修過的稿子會再送去繕打。每次拿到打字稿,他總是從第一行再讀一遍。如此這般,一部作品起碼經過上百遍的精梳細理。就像一個緩慢的「熟成」或是層層上釉的過程,他月復一月精煉自己寫出的字句。他謹慎檢查每個標點符號、文字排版、日期數字、引用的作品書名,一絲不苟地斟酌度量每一個用字,同時繼續書寫後續內容。等到最後一字落筆完成,他會先將全稿暫時擱置,接著花數個月時間繼續修潤打字稿,糾正任何不連貫處,進行最後的去蕪存菁。即便已寫下作品的最後一個字,意味著還有數個月之長的後續工作要做。
十二月三日星期日那天,父親將《無盡的讚歌》結尾手稿交到一直以來幫他繕打的年輕女打字員手中。他在十二月五日離世,沒能夠像慣常一樣重讀最後那幾頁的內容。不僅僅是最後幾頁沒能經過他的校閱,《無盡的讚歌》跟他過去三十七部作品毫不相同的是,這是唯一一本未經他本人鉅細靡遺反覆審訂過的書。
這本書,我父親是寫完了,但並未真正完成。或可以說他完成了,但並未真正地定稿。
本書行文明晰簡潔,但在他眼中肯定仍然有需要修正或刪減的贅詞冗語以及欠精準的用詞。而我選擇以此原貌將它付梓。不以某個句子還未完成的理由就擅自刪去它,沒為了說明某個初具雛形的概念就任意添字加句。我禁止自己去介入、去做出任何更動。那會剝奪它的原汁原味。是以假代真。我需要做的只有說明這部遺作的編輯方式。
依我之見,家父的這部最後作品風味分毫未減,縱有寥寥幾個不盡完美處,它仍是一部無比清晰凝練的傑作。
致讀者╱愛洛伊絲.端木松
二〇一七年六月那時候,我父親很幸福。夏季將至—一個可以大啖新鮮覆盆子(灑上滿滿糖粉)、到海水浴場曬日光浴、赤腳走在莫泰拉角(pointe de la Mortella)古代海關小徑的季節。他剛寫完《我,始終活著》(Et noi, je vis toujours,二〇一八年初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已開始動筆寫他的第三十八本書。在九十二歲之齡還有精力重拾寫作樂趣,對他來說簡直是奇蹟。儘管身體有恙,但以《宛如希望之歌》打頭陣、由《迷途者指南》(Guide des égarés)接續的三部曲計畫可望有始有終,這讓他開心不已。
接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