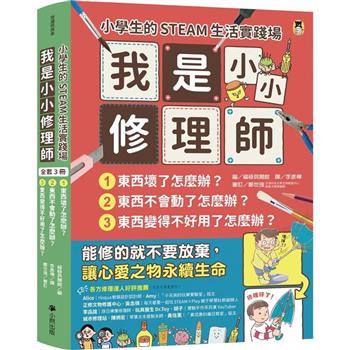良心的培養
良心的呈現——人性的發端
現代人喜歡說,做什麼要像什麼,代表一分成就感;不過不能僅停留在職責分工的盡職負責上說,還要回到「人」的身分,做普遍性的根本反省。生而為人,就要做人,且像個人,可不能人模人樣,而言行卻失去了人的品格跟味道。
這就是儒學傳統的第一要義,問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本質在哪裡?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儘管人跟禽獸不同的地方,就是那麼一點,而那麼一點卻是人之成為萬物之靈的所在。
所謂的「人禽之辨」,就在於人有仁心,人有善端良知,人性在「仁者愛人」的生命流行間,凸顯它的尊貴與莊嚴。人之所以為人在人有仁心,而仁心就在人會有不安感的當下呈現,論語有段孔子與宰我的師生對話: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曰:「安。」
「女安則安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爲之。」
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質疑父母過世,子女要服喪三年之傳統禮俗的合理性。他的論證有二:
一是人文價值的評量,倘若人人服喪三年,等同三年間,不能承擔禮樂的責任,那豈不是適得其反,導致禮壞樂崩的後果了嗎?
一是自然現象的運轉,正好一年一週期,四季用的木材,一年輪換一回,稻穀收成也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間完成。
依前者來看,三年太長了;依後者來看,一年就夠了。一破一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未料,孔子根本不從人文價值與自然現象的兩大論點,做出回應,反而直指本心的逼問:在父母離開人間的悲痛時刻,吃美味、穿錦繡,你會心安嗎?
原來,服喪三年的約定俗成,與人文評量、自然週期不相干,它發自人心的自我要求:你會心安嗎?這一逼問將人逼向存在的邊緣,你不能閃躲逃避,你要面對真實的自己,有如千鈞重錘,直敲在你的心靈深處。
「你會心安嗎?」這是儒家學說的根基。孔子只有這一問,再無其他,沒有神話,沒有啟示:只有人心的自問自答,人間道德的最後依據,就在「你會心安嗎?」的自問自答。
更出人意表的是,宰我竟做出「安」的回答。
孔子對此,也不能再說什麽,只能訴諸人性自身,你安那你就去做好了;不過一個有德行的君子,在守喪期間,美食當前不以為美味,聆聽音樂不會感受快樂,家居生活也不會覺得安適,你會心安那你就去做吧!
這樣的對答,看似委婉,實則跡近棄絕的罵人,話已說盡,宰我再無立足的空間,等同決裂般的離去。
可惜的是,在宰我離去之後,孔子才點出了三年之喪的理論依據,一邊詮解宰我何以說安的心理因素,一邊解答服喪三年的理由,就在兒時父母懷抱三年。
孔子不是罵宰予沒有仁德,而是說宰予的安,不是從仁心發出來的真心話,而是意氣的回應。所謂的父母過世,要有存在的實感,宰我的應對,卻只當做假設的情境,加上在被逼急的自我防衛之下,衝口而出的硬撐氣話。
何以要服喪三年,理由在,我們剛來人間,處在生命最稚弱無依的階段,父母懷抱我們三年,那麼在他們離開人間,處於最孤獨寂寞的時候,我們要不要陪伴他們三年,回報他們三年的愛呢?守喪三年的禮俗,是發自人性根處的內在呼聲,因為只有如此,才會心安。不是權威的教條,也就沒有議論的空間。
孔子從心會有不安感,說人有仁心,孟子繼起,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說人性本善。試看一段關鍵性的論述: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幼兒稚弱,即將掉落井中,生命已臨生死關頭,此時在我們心中呈現的內涵,一定是真切的傷痛感,不忍生命即將終結。不忍天下人受苦受難的心,正是良知善端的顯發。而這樣的心,是與生俱來,天生本有的心,所以用三個「非」,來排除後起人為的可能因素,不是為了要跟孺子的父母建立交情,不是為了想得到鄉里的讚譽,也不是受不了人家的批判才如此的。這樣的「非」,在經驗現象中可以一直增列,反正,不忍人受苦受難的善端良知,不是後起人為而有,而是直從先天本心發出,此一良知善端的本心源頭。統稱為良心。
所謂的「良」有二義:一為天生本有,二為善良,此所以台灣鄉土責罵品行不端的人,就拋出一句重話:「還有天良嗎?」天生本有的善良,從本來說,就是天理良心,良心從天理而來,天理是超越在人之上,天理也內在於心之中。
孔子說:「天生德於予。」孟子說:「此天之所與我者。」天生給我的就是德性良心,道德的理想在此確立,道德的源頭也在此奠基。人人當該做好人,人人皆能做好人,是因為天理就在人心中,因為人性本身就是善的。
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又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仁義禮智,不是由外來的權威強加在我的身上,而是人心本身所發動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善端良知;且一個有德行的君子,他所認取的性,是仁義禮智的價值心靈,而不是耳目官能的形氣物欲,心發出的是善端良知,所以心是善的。儒者的存在抉擇,就是以心為性,當然性也就是善。
良心的自覺——人性的朗現
道德人格的可能依據,在人有仁心善端,且仁心會在生命流行的每一當下呈現。問題是,良知會隨時呈現,也隨時隱沒,所以道德也就沒有必然性。只有在仁心呈現,生命處在覺醒的狀態,仁心良知呼喚自己,讓自己永遠保持清醒,而不會再沉墮而為昏昧狀態,這叫仁心的自覺。仁心不僅呈現,且在呈現時自覺,如此良心才能永遠挺立在生命的每一現場,道德才有必然的保證。
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我欲仁的「我」,就是仁心,仁心自我呼喚,仁心呼喚仁心的自己,也就是思則得之的意思,思是自我反思,自我照明,讓仁心自己永保清明。
試舉一例,我在師大就學時,擔任家教。學生白天上課,夜晚又要補習,疲累不堪,眼皮老是不爭氣的往下垂,他幾經掙扎,就在瞌睡片刻後的一念清醒,但見他奮力的挖出一小塊萬金油,悲壯的往雙眼一抹,靈魂之窗不僅豁然開朗,且自己感動得淚水直流。這時,再想睡也已不能,那個晚上,兩個鐘頭間不僅不再昏睡,反見神采飛揚。
仁心會呈現,仁心也會隱沒,呈現時會有不安感,知道自己不對,但隨即隱沒,又習以為常,轉成習氣。如期末考到了,老打電動或上網路,一兩個鐘頭過去,仁心呈現頓覺不安,不過下一秒鐘,仁心隱沒,又陷溺其中,等同昏睡。這形成弔詭的現象,逐漸安於不安。自知錯了,卻超拔無力,關鍵就在,清醒時未讓自己永遠清醒。
孟子說:「不為也,非不能也。」既然良知隨時呈現,何以會「不為」,原因就在不做自覺的工夫,而聽任仁心良知在呈現與隱沒間上下浮沉,迫使自己掉落在明知不對,卻依舊犯錯的境遇中,反而藉「不能」來自我說解,實則,人既有「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良能,怎能說我不知我不能,當然是我不為了。扭轉之道,就在良心的自覺,在清明間朗現人性。
良心的自做主宰——人性的光輝
仁心良知在心的不安與不忍中呈現,而呈現瞬間流逝,所以良知本心要在清醒的那一當下,自我呼喚讓自己永遠清醒,這是由呈現升進一層的自覺工夫。
呈現是仁心良知在形氣欲的拖累中,突圍而出,心從形氣物欲的包圍中超離出來;自覺是心對心的自己,發出邀請呼喚,把心留住,永遠自覺挺立;自作主宰,是心站出來,做自己的主人,自己當家做主,主導形氣物欲。孔子有一段與顏回的對話,十分完整的說出修養工夫的三層次:
顏淵問仁。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克己是就自然物的層次說,復禮是就社會人的層次說,為仁是就人文心的層次說。人同時兼有自然物、社會人與人文心的三重身分。
人是自然物,有形氣物欲,會蠢動會膨脹,所以要有克制的工夫;人是社會人,處在人際關係網中,要有情意感應,理想會通的管道。克己是主體的修持,復禮是客觀的實踐,而源頭卻在仁心的自做主宰。
為仁是仁心的自做主宰,與自我實現。由己是從自身來,是自己決定方向,自己約束自己,既是規範又是自由,這就是道德的自律。
由己與克己,分屬人文心與自然物的不同層次,故不構成矛盾,人文心自做主宰,自然物有待克制。倘若未有仁心的自由(由己)僅為了克己而安排的禮教或禮制,就成了外在的規範或權威,不是由己,而是由人,如此道德規範對人性而言,形成壓迫或傷害,禮制是權威的教條,禮教就難逃「吃人的禮教」的罵名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激越,重點在打倒吃人的禮教,所謂吃人,是失去了仁心的自做主宰,僅是「克己」,而不是「由己」,禮既是「由人」,有如外在牽引,甚至是外力逼壓,那當然成為人人要反抗的權威教條了。
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為學之道,首在把失落的良心找回來,而良心會流放自己,是因為物欲的牽引,心不做主宰,不能主導物欲,反而隨物欲而去,成為生命最大的顛倒。台灣社會,當前亂象的根由,就在失落了五十年來一步一腳印的台灣良心,只看黑金官商混流的局面,名利心權力欲淹沒一切,對症下藥,惟有「求其放心」,把台灣良心找回來;不過存養良心,得破解過度膨脹的貪欲。良心與物欲,有如天秤的兩端,物欲消減,則良心增長。
比諸孔子的「克己復禮」,孟子的重大突破在「知言養氣」。孟子的「知言」,就社會人的層次說,近於「復禮」,而「養氣」,就自然物的層次說,近於「克己」。不過知言是以心知言,以良心去評斷天下的是非,養氣是以心養氣,從孔子自我克制的消極義,轉向生命力存養擴充的積極義,「以直養而無害」,把良心的正直當養分,灌注在形氣上,就會長成生命的大樹,「至大至剛」,什麼都不怕,因為我永遠是對的,不僅心安理得,且理直氣壯,當氣壯山河的時候,就是瀰漫天地間的浩然正氣了。
以心知言,以心養氣,所以一定要「先立其大」,孟子的論述,有大體、小體的二分:「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此中大小的區分,不是數量上的多寡,而是指品質的貴賤。且不是界域的平面區別,而是層次的超越區分。它是價值的意涵,在重要感之下的二分,「從」意味人生的定向,「養」則指向人生的涵養,有定向有涵養,那麼耳目官能,形氣物欲的小體,就不能篡奪大體的主導地位了。
從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到孟子的「先立其大」,且以心知言,以心養氣,仁心的光輝通貫到社會人、自然物的層次,人文心化成了社會人與自然物,統體是人性的光輝,孟子說:「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說:「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是把自己的身體當做道場,而良心是修道人,自然生命轉化成道德生命,煥發人格的光輝,這叫生色。此有如我們有良心,有理想性,有責任感,好好讀書,這個社會就是書香社會,而每一個人身上都涵有書卷氣。
存在的抉擇——人性的莊嚴
良心的呈現、自覺與自做主宰,是道德實踐的三部曲,可能在呈現,保證在自覺,而完成在自做主宰。
孟子有一段千古傳誦的話: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嗅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此言耳目官能的小體,與仁義禮智的大體,都是天生而有的,都是性;而二者都有它不得不然的限制,也都是命。耳目官能的欲求,會疲累會厭倦,且有時而窮,譬如老是吃山珍海味,會倒胃口,還不如清粥小菜,來得清淡可口;反之,仁義禮智的良知,是仁心的自我流露,父子親情,你總是愛他,偶爾生他的氣,你還是念他疼他,似乎永遠有不得盡的遺憾,這就是所謂的「命」感,看起來有限,實則愛有無窮伸展的空間,愛不會厭倦,愛可以不斷的付出,不會有枯竭的危機。所以人生最重大的抉擇,端在你要認取哪一部分做為人性的內涵,是有時而窮的耳目官能呢?還是無限伸展的價值心靈呢?孟子說一個有德行的君子,是不以耳目官能為性,而是以仁義禮智為性,這叫做存在的抉擇。抉擇的是存在的本質,人性的莊嚴就在兩可間,你做了價值的超越決定。君子把耳目官能看做命一般的限制,而把仁義禮智當做自家的性分。
孟子說大舜「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這就是仁心良知的自我感動,與自我完足。孔子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愛當然要有智慧,不過智慧僅是有助於仁德的實現,它不是目的,人會在不安中求安,這就是道德的動力,而且仁心會安於仁心的自己,因為它是最高的理想,也是最後的真情,它是終極原理,當仁心呈現,自覺與自做主宰時,人就可以安心了。
性命對揚,性是德行的必然依據,而命則是福報的偶然遇合。孟子有一段極精到的解析: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德行所求在我,求則得之是良心的自覺,舍則失之是良心在呈現與隱沒間游離,求有益於得,意味道德有其必然性;福報所求在外,求之有道是以德行去求取,得之有命是要看人間的機緣遇合,求無益於得,代表福報有其偶然性。有如孔子所說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意思,均不是人的德行所能決定的。
所以孟子說:「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是求之有道,而人爵從之,僅是吾人心中的願望,理當如此,而事實上卻得之有命。
天爵是天生的高貴,是「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爵是人間的高貴,是「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人生存在的抉擇,就在你選擇的是道德人格的高貴,還是人間權位名利的高貴,前者是「雖無文王猶興」的豪傑,後者是「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的無奈,價值的實現是自己良心可以做主的,權勢的角逐則是外在情勢所決定的,人的一生是以何等的面貌姿態出現,人生百年到底繳出怎麼樣的成績單,端在吾心一念的抉擇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生命的學問十二講(2021年版)的圖書 |
 |
生命的學問十二講(2021年版) 作者:王邦雄 出版社: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0-0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中國哲學 |
$ 282 |
Books |
$ 288 |
中國哲學總論 |
$ 288 |
哲學 |
$ 288 |
社會人文 |
$ 320 |
靈性療癒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生命的學問十二講(2021年版)
國內老莊研究第一人,
說世道、說圓融、說生死、說信仰與人生、說良心的培養。
將古老智慧在現代社會中賦予新的生命力,
以真我洞析真相做為生命學問的依歸。
生命的學問.人間的智慧
本書是王邦雄教授對生命的學問深度觀照的集結。
生命的課題既深奧而又命題廣泛,王邦雄教授在書中談生死、談婚姻,也說故鄉、聊世道,用充滿機趣的言談把生命的嚴肅本質編織進他的論述之中。
全書內容包括兩個層面,首先是人間智慧,作者談世道說圓融,探討宗教信仰與生死大關,並論及生命情緣、良心的培養;其次則為老莊智慧現代詮釋,是儒、釋、道三家的會通,對於人文與自然、生命本相等亦有深刻、生動的剖析。
透過簡單卻充滿力道的指引,照見生命的深刻意義。
(本書為《行走人間》增訂新版)
作者簡介:
王邦雄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文化大學哲學碩士及博士,榮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曾任鵝湖月刊社社長、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所教授、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所教授暨哲研所教授、所長,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著作等身,包括:《韓非子的哲學》、《老子的哲學》、《儒道之間》、《中國哲學論集》、《緣與命》、《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老子十二講》、《莊子內七篇.外秋水.雜天下的現代解讀》、《莊子寓言說解》等書,其中《道家思想經典文論:當代新道家的生命進路》、《走過人生關卡:生命的大智慧》於立緒文化出版。
章節試閱
良心的培養
良心的呈現——人性的發端
現代人喜歡說,做什麼要像什麼,代表一分成就感;不過不能僅停留在職責分工的盡職負責上說,還要回到「人」的身分,做普遍性的根本反省。生而為人,就要做人,且像個人,可不能人模人樣,而言行卻失去了人的品格跟味道。
這就是儒學傳統的第一要義,問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本質在哪裡?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儘管人跟禽獸不同的地方,就是那麼一點,而那麼一點卻是人之成為萬物之靈的所在。
所謂的「人禽之辨」,就在於人有仁心,人有善端良知,人性在「仁者愛人」的生...
良心的呈現——人性的發端
現代人喜歡說,做什麼要像什麼,代表一分成就感;不過不能僅停留在職責分工的盡職負責上說,還要回到「人」的身分,做普遍性的根本反省。生而為人,就要做人,且像個人,可不能人模人樣,而言行卻失去了人的品格跟味道。
這就是儒學傳統的第一要義,問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本質在哪裡?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儘管人跟禽獸不同的地方,就是那麼一點,而那麼一點卻是人之成為萬物之靈的所在。
所謂的「人禽之辨」,就在於人有仁心,人有善端良知,人性在「仁者愛人」的生...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增訂新版自序╱二○一七年
這一本解讀人生的書,二十年前首度以《世道》為名刊行;十年之後再以《行走人間》之更貼近生活的姿態重新出發;而今又過了十年,轉以《生命的學問十二講》之增訂新版推出,加進了〈信仰與人生〉與〈良心的培養〉兩篇專為青年學生之通識素養而寫的篇章。
對人文學者而言,講課與寫書乃是理想追尋與責任擔當的分內事,它的本身就是目的,暢銷與否那可是廣大讀者的事了。這二十年來,出版社對本書未得到應有的迴響,引以為憾,難得主編有此信心與堅持,身為作者深感榮幸,哪敢輕言從講堂與書房中退休呢!
說...
這一本解讀人生的書,二十年前首度以《世道》為名刊行;十年之後再以《行走人間》之更貼近生活的姿態重新出發;而今又過了十年,轉以《生命的學問十二講》之增訂新版推出,加進了〈信仰與人生〉與〈良心的培養〉兩篇專為青年學生之通識素養而寫的篇章。
對人文學者而言,講課與寫書乃是理想追尋與責任擔當的分內事,它的本身就是目的,暢銷與否那可是廣大讀者的事了。這二十年來,出版社對本書未得到應有的迴響,引以為憾,難得主編有此信心與堅持,身為作者深感榮幸,哪敢輕言從講堂與書房中退休呢!
說...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增訂新版自序〉╱二○一七年
〈序〉世道在人心的開拓╱一九九七年
1 說世道
2 說圓融
3 說生死
4 說宗教
5 說生命情緣
6 說父母經
7 說第二故鄉
8 說人文與自然
「道法自然」的空靈智慧
9 說生命本相
「用心若鏡」的現代詮釋
10 說示相與識相
展現真相與真我
11信仰與人生
12良心的培養
〈序〉世道在人心的開拓╱一九九七年
1 說世道
2 說圓融
3 說生死
4 說宗教
5 說生命情緣
6 說父母經
7 說第二故鄉
8 說人文與自然
「道法自然」的空靈智慧
9 說生命本相
「用心若鏡」的現代詮釋
10 說示相與識相
展現真相與真我
11信仰與人生
12良心的培養
生命的學問十二講(2021年版) 相關搜尋
水晶寶石應用全書:收錄多種寶石介紹及應用技巧,解讀礦石中的占星知識與療癒能量財富豐盛吸引力(牌卡書盒珍藏版)【附28張指引牌卡+6張燙金招財貼紙+專書+精美書盒】
財富豐盛吸引力:28個豐盛指引,開發內心能量,扭轉未來人生
煉金術新手指南:物質、心智、性靈煉金實作導引,靠煉金術原則轉變性靈自我
能量水晶療癒全書:身心靈的自然平衡開運指南
格局的力量:提升人生境界的365條黃金法則
真正的你,和你想的不一樣:揭開「我」獨一無二的專屬人生,觸發生命改變的108個神奇問答
零極限.第五真言:荷歐波諾波諾的進階清理與釋放
請問覺醒:無極瑤池金母密傳靈魂覺醒啟示錄
探尋神聖知識的旅程-從未失落的光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