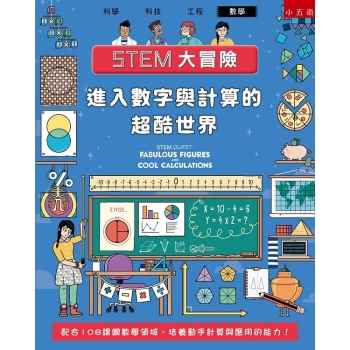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THE REAL AWAKENING世界覺醒03夜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54 |
懸疑推理 |
$ 174 |
神怪/推理 |
$ 174 |
Literature & Fiction |
$ 194 |
中文書 |
$ 198 |
文學作品 |
$ 323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THE REAL AWAKENING世界覺醒03夜行
啜飲鮮血,與虛假的自我告別。
《闇獵者》作者
四隻腳
經典代表作
妖物×懸疑×帥哥滿滿的不思議奇想
--
唯有死亡,與真實相依。
人生比小說更離奇這句話,葉逍深有體會。
為了追捕犯人而搭上的火車,在隧道之中車廂分離,
葉逍與蘇沐偕同落難的數名乘客,躲進了一間燈火通明的空屋。
然而,當一具具屍體出現,眾人等待救援的希望亦隨之幻滅。
待在屋內成為乾屍,或者離開鬼屋化為一灘血水,
進退兩難的局面,又該如何選擇?
而在危難中,葉逍再次發現了蘇沐的祕密!
同樣身懷祕密的刑警搭檔,是否有互相坦承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