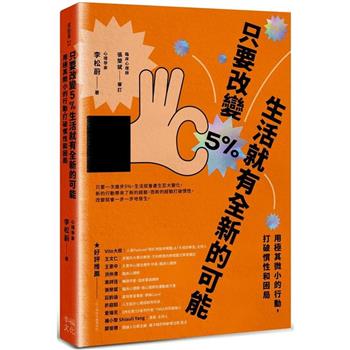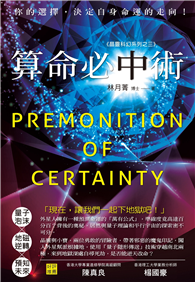★星雲獎得獎作品《遺落南境三部曲》最終章
★紐約時報暢銷小說 ★授權超過二十個國家
★星雲獎、軌跡獎、世界奇幻獎、英倫奇幻獎獲獎作家
★納塔莉.波曼主演,亞力克斯.嘉蘭導演改編電影將於2017年上映
★我愛傑夫‧凡德米爾的《遺落南境》三部曲,詭譎又引人入勝。──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我們像供品一樣獻身,成了迷途羔羊。
我們穿越了鬼魅之門,進入幽靈之地。
X禁區以超越人類想像的智慧與耐心布下陷阱,利用返回的探險隊隊員感染外在世界,以及負責阻止它的政府組織「南境」。
邊境隨著感染擴大而得以瘋狂擴展,甚至吞噬了南境。絕望的南境員工決定聽從前任主任的命令,前往燈塔尋求答案。幽靈鳥為了探求自己的真實面貌,決意回到X禁區,深受她吸引的指揮官也跟隨了她的腳步。紛雜的線索糾纏交會,是否會導向真相?
究竟是什麼引發了這種超自然的動盪?南境過去曾有著什麼樣的內幕?X禁區會迎向什麼樣的結局?在許多探險者中,有誰真正接近了真相?誰又被同化了?
當所有的謎題都被解開,將會帶來什麼樣殘酷的後果與影響?
名人推薦
我愛傑夫‧凡德米爾的《遺落南境》三部曲,詭譎又引人入勝。──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迷人三部曲的完美結局。──《書單》雜誌(Booklist)
凡德米爾傑出的劇情安排、角色魅力與日益加深的絕望情況,將會讓讀者瘋狂渴望讀到這三部曲的最後一集。──《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一部講述解謎探險以及我們內在生疏的心理驚悚片,緊張且令人發寒。有些「庫柏力克」,非常「洛夫克拉夫特」,小說建立在讓人無法承受的緊張與幽閉恐懼上。我很喜歡!──羅倫•布克斯Lauren Beukes,《我會回來找妳》作者
很久沒有書帶給我這種真實且奇妙的不安感了。有種從第一頁就出現,而我卻沒有及時意識到的震撼感。──Matt Bell,《In the House Upon the Dirt Between the Lake and the Woods》作者
一本燦爛奪目的書……在腦海中縈繞不去。──凱麗‧林克Kelly Link,《Magic for Beginners》作者
這部小說最恐怖的便是在於它對人性的探索,而那份恐怖更因我們對他人或自己的不信任而萌生滋長。──Jared Bland,《環球郵報》
●但唐謨(知名作家)、馬欣(知名作家)、膝關節(知名影評人)聯合推薦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遺落南境Ⅲ:接納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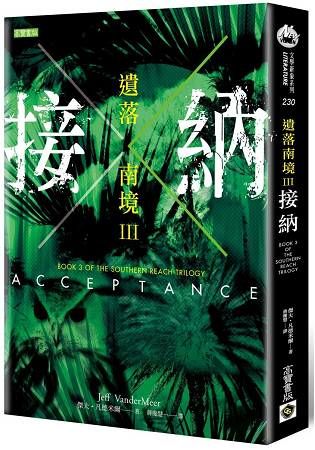 |
遺落南境(Ⅲ):接納 作者:傑夫‧凡德米爾 / 譯者:蔣慶慧 出版社: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17-02-1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遺落南境Ⅲ:接納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傑夫‧凡德米爾 Jeff VanderMeer
身兼作家、編輯、出版人以及教師等多重身份,同時也是「新怪譚」(New Weird)流派的代表作家。他以華麗且實驗性的筆法為長,在文壇獲獎無數。
他以《遺落南境Ⅰ:滅絕》獲得星雲獎。過去曾獲三次世界奇幻獎(World Fantasy Awards)、軌跡獎(Locus Award)、雷斯靈獎(Rhysling Award)、英倫奇幻獎(British Fantasy Award)、英倫科幻協會獎(BSFA Award),也曾入圍雨果獎,作品更被收入美國圖書館科幻故事集與數本年度最佳科幻小說選集。
此外他創立的「異想部」出版社也致力於發掘大膽創新的年輕作家。凡德米爾的小說已在全球被翻譯成二十二種語言,《遺落南境》系列也已授權超過二十國。他於斐濟長大,現與妻子居於佛羅里達州塔拉赫西。
作者官方網站:www.jeffvandermeer.com/
星雲獎(Nebula Award)為美國科幻及奇幻作家協會(Science Fiction & Fantasy Writers of America Inc.)所頒發的科幻與奇幻藝術年度大獎。歷屆著名獲獎作品:《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美國眾神》、《戰爭遊戲》……。
獲獎作家:《冰與火之歌》喬治•R•R•馬丁、《地海六部曲》娥蘇拉.勒瑰恩……
譯者簡介
蔣慶慧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畢,曾任無線及有線電視台節目、文學小說及商管書籍翻譯。現居紐約,任職廣告行銷專業。
傑夫‧凡德米爾 Jeff VanderMeer
身兼作家、編輯、出版人以及教師等多重身份,同時也是「新怪譚」(New Weird)流派的代表作家。他以華麗且實驗性的筆法為長,在文壇獲獎無數。
他以《遺落南境Ⅰ:滅絕》獲得星雲獎。過去曾獲三次世界奇幻獎(World Fantasy Awards)、軌跡獎(Locus Award)、雷斯靈獎(Rhysling Award)、英倫奇幻獎(British Fantasy Award)、英倫科幻協會獎(BSFA Award),也曾入圍雨果獎,作品更被收入美國圖書館科幻故事集與數本年度最佳科幻小說選集。
此外他創立的「異想部」出版社也致力於發掘大膽創新的年輕作家。凡德米爾的小說已在全球被翻譯成二十二種語言,《遺落南境》系列也已授權超過二十國。他於斐濟長大,現與妻子居於佛羅里達州塔拉赫西。
作者官方網站:www.jeffvandermeer.com/
星雲獎(Nebula Award)為美國科幻及奇幻作家協會(Science Fiction & Fantasy Writers of America Inc.)所頒發的科幻與奇幻藝術年度大獎。歷屆著名獲獎作品:《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美國眾神》、《戰爭遊戲》……。
獲獎作家:《冰與火之歌》喬治•R•R•馬丁、《地海六部曲》娥蘇拉.勒瑰恩……
譯者簡介
蔣慶慧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畢,曾任無線及有線電視台節目、文學小說及商管書籍翻譯。現居紐約,任職廣告行銷專業。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