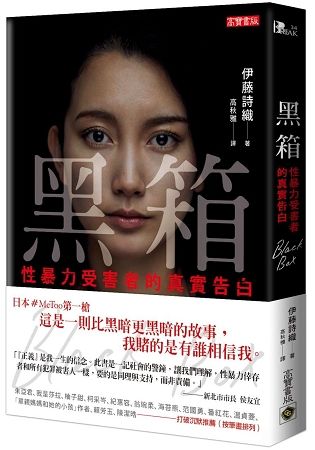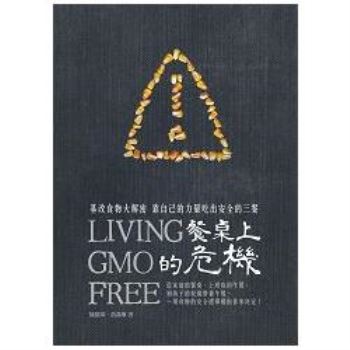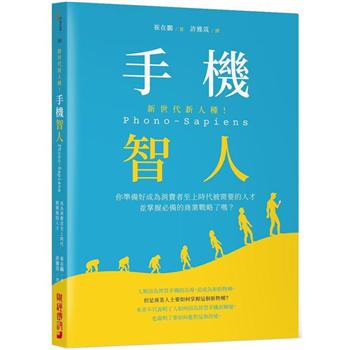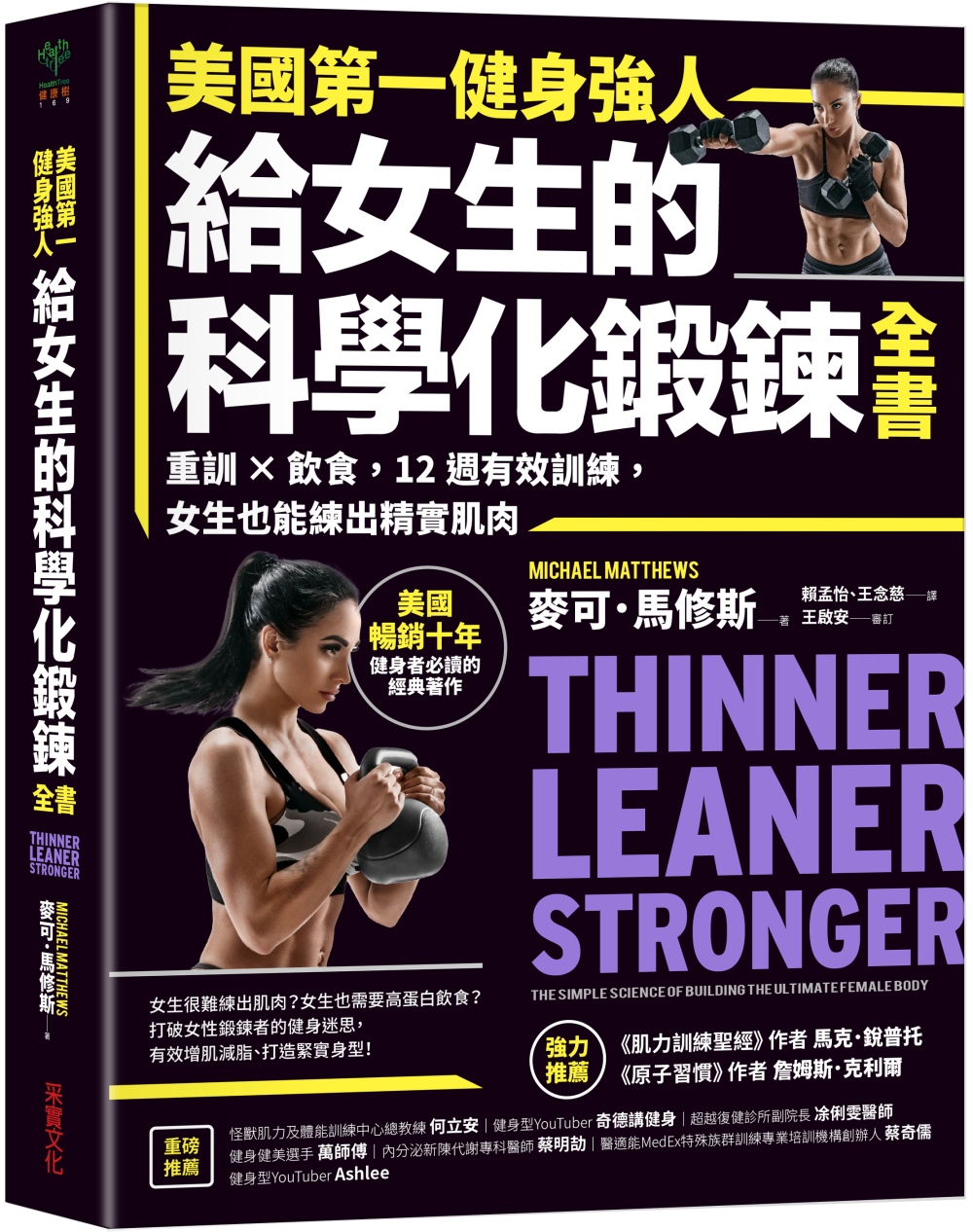圖書名稱:黑箱
日本#MeToo第一槍
這是一則比黑暗更黑暗的故事。
★鼓勵無數受害者,給予強而有力的勇氣!★
即使是小蝦米對上大鯨魚,也要奮力一搏,尋求真實與正義。
受害者不可恥,該撻伐的是傷害的加諸者,性暴力,必須被終結。
受同業前輩性侵,身為記者的受害者伊藤詩織,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同時,仍直搗問題核心;意圖向大眾傳達強暴受害者在權力傲慢的壓迫下,還得面對法律及社會體制的不足──也就是黑箱──的殘酷真相。
一起不可饒恕的性侵案,就此變成了密室事件,尋求正義的過程,面對的是一個個開啟不了的黑箱,真相就此被封閉。
以權職作為惡行的藉口,有多少加害人仍在大眾的默許下逍遙法外?又有多少受害者發聲捍衛自己,換來的卻是大眾的控訴?
2013年,伊藤詩織遠赴紐約攻讀學位,期間結識了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局長山口敬之,並在對方的承諾下期待能得到新聞業的工作機會。
恰逢雙方都回到日本時,兩人相約居酒屋,原以為主要是討論提供工作機會,沒想到山口只是不斷吹噓自己與總理等政商界有權人士的人脈。席間伊藤開始察覺身體的不適感,意識也逐漸模糊,平日酒量相當好的她幾乎可以確定自己被下藥了。
兩人一同搭上計程車後,雖然伊藤要求在車站下車,山口卻以工作機會的名義為由強留下她。從車上到飯店的這個過程,伊藤近乎沒有記憶,等到她再次恢復意識,她已是全裸的躺在飯店床上,山口正跨坐在她身上。
飯店的攝影機證實,當晚伊藤是被抱進房間的,然而山口的證詞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惡行:「妳從廁所出來之後,還很正常地說喝太多了,就自己爬上我的床。」
2015年伊藤向警視廳諮詢,高輪警察署在月底以準強姦嫌疑受理了告訴狀,開始搜查。6月初雖然發行了逮捕狀,但當時的警視廳刑事部長卻在準備於成田機場逮捕山口前際,下達了停止命令。之後再經過1年4個月左右的調查之後,東京地檢署以嫌疑不充足為由判決不起訴。
2017伊藤向審查會提出了再審要求,並以「詩織」這名字出席召開了記者會。而山口則於自己的臉書社群上反駁「自己從未觸法」。
即便再次審理,檢查審查會仍決議不起訴。
兩次刑事訴訟皆不起訴,2017年9月,以非自願性行為而承受精神上的壓力與痛苦,伊藤向山口提起民事訴訟,求償1100萬。同年12月,舉行第一次民事訴訟第一次口頭辯論。
為喚醒社會大眾對於性暴力的意識,更為控訴日本社會在處理性暴力的冷漠應對,伊藤以本名出版了這本事件紀錄。
身為記者,她有著強烈找出真相的決心,回首痛苦記憶將只有當事人知曉的密室對話,及她在提出強姦被害與起訴狀後所遇到的司法及媒體高牆,全都記述在本書中。
每個地方都有Black Box,強暴受害者勇敢道出自己的經歷,只為停止這種最沉默的傷害。
各界推薦(按筆畫排列)
寶瓶文化社長兼總編輯 朱亞君
空姐 我是莎拉
作家/心靈工作者 柚子甜
吾思傳媒 女人迷總編輯 柯采岑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紀惠容
國際新聞記者 翁琬柔
科普心理作家 / 愛情心理學家 海苔熊
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 范國勇
作家 番紅花
演員 温貞菱
東華大學通識中心講師╱粉絲頁「單親媽媽和她的小孩」作者
律師 賴芳玉
《不再沈默》作者 陳潔晧
作者簡介
伊藤詩織(いとう しおり)
1989年出生,獨立記者。目前主要在《經濟學人》、半島電視台以及路透社等外國媒體發佈影像新聞和紀錄片。
譯者簡介
高秋雅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畢業。
現從事翻譯工作,譯有《整理瘦身收納法》等書。
信箱:choyakao@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