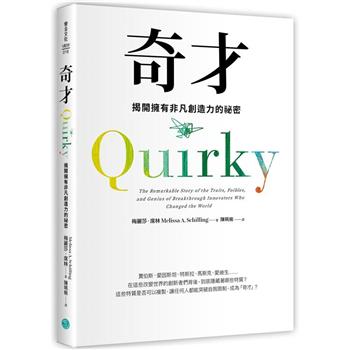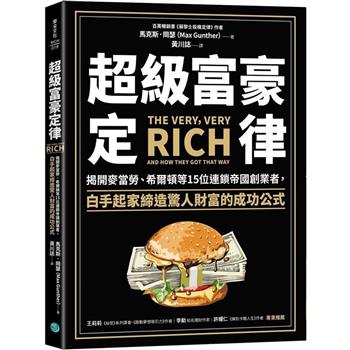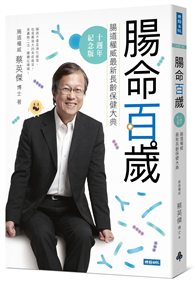入墨方者,應銘記墨方之道。
墨黑不染,方正不阿。才為墨方。
墨黑不染,方正不阿。才為墨方。
雷雨滂沱……
預定成為下任鑄門掌門的少女鑄宓,
攜著一柄青銅古劍──鑄之刃「春江」,來到了王都「晶畿」,
為的是刺殺暴戾無道、喜怒無常的諸侯,歐泉君。
卻在行刺之際
與同樣擁有鑄之刃「花月夜」的新任天子,岐桂交鋒。
刀劍相向,召出一幅象徵盛世的「春江花月夜」之圖,
也喚醒了千年前的統治者渴求天下太平的幻夢。
為了實現那場夢,直屬於天子的組織「墨方」應運而生,
然而夢想與現實的落差,讓「墨方」在屢經挫折後,
淪為助紂為虐的殘酷組織……夢終究成了泡影。
千年後,「春江花月夜」之夢選擇了鑄宓與岐桂,
懷著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心思,
變革的使命,以及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愫,
在青年與少女的胸中,開始萌芽──
本書特色
★《罌籠葬》《兩守》人氣小說家久遠×《北城百畫帖》知名插畫家AKRU,聯手獻上瑰麗絢爛的古裝奇幻系列!
★春江花月夜。太平之世。太平之夢。即便那只是場夢,他與她終究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