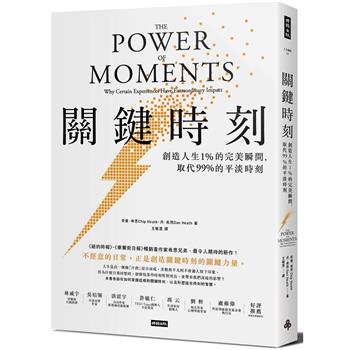老師,又有事件了!
熱愛推理小說的高二女生花本雲雀,和舊書店老闆枯島一同造訪位於山谷間、收藏著大量珍奇舊書的日式大宅。為了收購這些書,枯島和雲雀與舊書商展開了古書鑑定戰,更因此而遇上有如推理小說般的殺人事件……
自詡為女高中生偵探的花本雲雀,有辦法解決這起事件嗎!?
而正牌的神探-古怪作家久堂蓮真,又身在何方呢?
本書特色
★niconicio動畫已突破75萬人次點閱的傳奇樂曲,小說正式登場!
★離奇出現的屍體、抄寫著豐收之歌的血書,宛如推理小說再現眼前,花本雲雀能否順利破案?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舊書大宅殺人事件 女學生偵探系列 02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09 |
懸疑推理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 288 |
中文書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舊書大宅殺人事件 女學生偵探系列 02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TENIWOHA
廣島人,虛擬人聲歌曲製作人(VOCALOID P)。從首度投稿歌曲創作以來,在兩年半之內發表了三十首類型豐富的歌曲,特色是歌詞中有豐富的文字遊戲及押韻。曾發行專輯《女□生探偵□□□》(暫譯,女學生偵探搖滾樂)。
繪者簡介
NANORI
最愛黑框眼鏡男的B型插畫家。主要替虛擬人聲歌曲繪製插畫,近年來在乙女遊戲(以少女為對象之戀愛遊戲)與原創作品之領域亦相當活躍。
譯者簡介
黃薇嬪
熱愛英國、三件式西裝和馬甲背心的日文譯者。這或許就是我一看到這套小說封面就決定接下的原因。我生活中也有一位推理作家朋友寵物先生,不過他不古怪就是。譯有《火目的巫女》、《古書堂事件手帖》系列等書。
TENIWOHA
廣島人,虛擬人聲歌曲製作人(VOCALOID P)。從首度投稿歌曲創作以來,在兩年半之內發表了三十首類型豐富的歌曲,特色是歌詞中有豐富的文字遊戲及押韻。曾發行專輯《女□生探偵□□□》(暫譯,女學生偵探搖滾樂)。
繪者簡介
NANORI
最愛黑框眼鏡男的B型插畫家。主要替虛擬人聲歌曲繪製插畫,近年來在乙女遊戲(以少女為對象之戀愛遊戲)與原創作品之領域亦相當活躍。
譯者簡介
黃薇嬪
熱愛英國、三件式西裝和馬甲背心的日文譯者。這或許就是我一看到這套小說封面就決定接下的原因。我生活中也有一位推理作家朋友寵物先生,不過他不古怪就是。譯有《火目的巫女》、《古書堂事件手帖》系列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