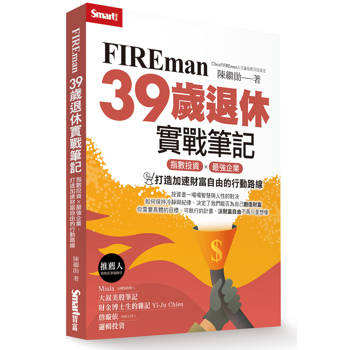!!警告!!
如果,在閱讀中感受到窺視的眼神,請先暫時闔上本書。
「不要看! 因為它會來……」
昭和末年,某個夏天。
來到偏僻出租別墅打工的成留一行人,
在謎樣女性的引領下,來到被視為禁忌之地的廢棄村莊,
遭遇既可怕又詭異的經歷。
昭和初期,民俗學家‧四十澤寫下的筆記本中,
記載了這座名叫「弔喪村」之村,
曾流傳一則怪談,
在鞘落這一戶人家,盤踞著附身惡靈「窺目女」,
自那時開始,便不斷有人離奇死亡……
最凶惡的附靈「窺目女」,流傳於「弔喪村」的顫慄怪談。
* * * * * * *
本書特色
★板野友美 主演 2016/4/2電影日本上映!
★挑動人們對恐懼最敏感的神經,體驗如噩夢般的極致恐怖世界───
★三津田信三:「這是身為作家的『我』所知的兩個恐怖體驗。而這兩個故事,源自於同一個遭受詛咒的村莊……」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窺伺之眼的圖書 |
 |
窺伺之眼 作者:三津田信三 / 譯者:王靜怡 出版社: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3-2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0 |
二手中文書 |
$ 306 |
小說/文學 |
$ 324 |
中文書 |
$ 324 |
驚悚/懸疑小說 |
$ 32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窺伺之眼
|